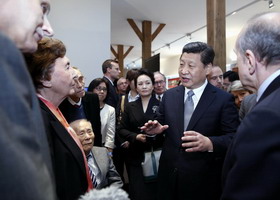8月6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纳维•皮莱发表声明,敦促日本政府全面而永久地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皮莱在声明中强调,日本政府在6月20日发布的《“河野谈话”调查报告》中否认日军征用“慰安妇”的强制性,这对“慰安妇”受害者带去了极大的痛苦。
在此两周前,针对二战期间日军强征“慰安妇”问题,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7月24日公布结论性意见,要求日本政府作为“国家责任”予以承认,并追究加害者的刑事责任,并指出日本在教科书中充分记载该问题的重要性。
为什么说强征“慰安妇”是日本的“国家责任”?中国为什么要将“慰安妇”档案申报联合国记忆遗产名录?围绕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苏教授同时还是今年6月中国将“慰安妇”史料申报世界记忆工程的发起人。
寻访幸存者
研究“慰安妇”问题,对苏智良来说源于一个偶然的机会。1992年,苏智良正在东京大学做访问学者,主要研究中国毒品史。
在和日本同行的一次闲谈中,他得知日本第一个慰安所设在上海。之前,日本政府一直在刻意隐瞒“慰安妇”问题,到了1992年,“慰安妇”问题开始成为普受关注的世界性问题。
回国后,苏智良立即试着调查。由于日军投降前销毁了大量的档案,过去很长时间又没人关注,加上大多数受害者已经离开人世,一些仍然健在的慰安妇及其后代出于种种原因不肯说出当年的痛苦经历,所以“慰安妇”的研究面临重重困难。但苏智良还是找到了100多个愿意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
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南林乡万如村谭亚洞阿婆说,当时慰安所里有一个叫阿诗的女孩,被日军强暴后怀孕了,于是日军士兵把她绑在树上,用刺刀破开她的肚子,并命令所有的慰安妇在路边排队现场观看。谭亚洞告诉调查员,几十年来晚上经常梦到这件事。
杨时珍,16岁那年的7天被掠到慰安所的经历改变了她的一生,留下了精神失常、大小便失禁的毛病;张仙兔,17岁那年被强征为慰安妇,见日本人进来吓得浑身发抖,从此落了病根,双手抖了一辈子;陈亚扁,因不甘在慰安所受辱,反抗时一只眼睛被日本士兵打坏,60多年来流泪不止……
这些都是苏智良和调查员走访调查幸存者时亲眼所见,并记录在《慰安妇研究》、《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两本书里的。
通过这些幸存者讲述,苏智良了解到,被掠为“慰安妇”毫无人身自由,经常一天要被日本士兵强暴数次、甚至数十次,除了部分性情刚烈的女性自杀外,反抗强暴、逃跑被抓回来、染上严重性病、甚至怀孕了的都会被日军杀掉,到战争结束时幸存者不过四分之一。
苏智良在调查中了解到一个案例,1942年夏天,日军第56师团的军队冲进了芒市的一个街口,当众抓去50多名傣族妇女充当“慰安妇”,没有一人生还。
即使幸存下来的少数人境遇也大多凄凉,有的受到周围人的歧视,有的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有的痛恨男人终生不嫁。
被强迫的性奴隶
苏智良说,日本把强征来的这些女性称为“慰安妇”,顾名思义就是“慰安”日军官兵的女性,这就明显带有掩饰战时日本国家及其军队建立性奴隶制度战争犯罪的色彩,以致外界有意无意将“慰安妇”与“军妓”完全混为一谈,给受害人带来第二次伤害。很多受害者战后遭人歧视和侮辱,因为人们认为她们“陪日本兵睡过觉”,甚至直称她们为“日本妓女”。
“‘慰安妇’的实质就是日军强征的性奴隶!大量中国、朝鲜、东南亚甚至部分欧美国家的妇女惨遭日军的蹂躏。”苏志良对记者说,“日军的‘慰安妇’制度是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上找不到第二例的男性对女性、尤其是对敌国及殖民地女性集体奴役、摧残的现象;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阀违反人道主义、违反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了的政府犯罪行为,也是世界妇女史上最为惨痛的记录。”
事实上,早在1993年维也纳人权大会上通过的《关于废除对女性暴力的宣言》就将日军“慰安妇”问题界定为“战争中对女性的奴隶制”。
2012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指示美国所有文件和声明禁用按日语直译的“慰安妇”一词,将其改为“被强迫的性奴”,以此要求日本正视二战期间的性暴行。此后,韩国政府也表示考虑将“慰安妇”的官方英文译名改为“性奴隶”(sex slaves)。
尽管还活着的“慰安妇”已经寥寥无几,尽管也曾有一些昔日的“慰安妇”到日本申诉并要求赔偿,但至今这些昔日的“慰安妇”甚至连日本政府的一个道歉也没有得到。她们发起的赔偿要求也被日本政府以过了追诉期、不是国家行为等借口而加以拒绝。
日本的国家行为
面对日本安倍政府矢口否认二战期间强征占领国的“慰安妇”问题,苏智良指出:不仅自己、世界各国学者都拿出大量证据来证明这是日本国家、军队主导实施的。
苏智良经过20多年的研究调查,尤其是日本国内资料、旧的报刊资料,以及侵华日军没有来得及销毁的部分资料,他对日本在中国实施行奴隶制度的概况、特点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日军在亚洲最早设立的慰安所位于上海,可以追溯到1932年初。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在中国各占领地都设立了慰安所,由军队自己管理。根据苏智良的调查,慰安所遍布日军占领的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20多个省市,仅上海一地就有160多个。苏智良推测,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先后被逼迫为日军的性奴隶。
“最初我没想到日军‘慰安妇’制度会这么完善,日本从外务省、法务省到海军省、陆军省、朝鲜总督府、台湾总督府、侵华日军,都卷进去;从师团到联队、甚至于一些中队、小队都有慰安所。具体到如何提解、如何运输、如何开支都有完备的制度。” 苏智良说。
苏智良从吉林省档案馆近期公布的一批10万多件日本侵华档案中,仅用一个星期时间就查到有40多件有关“慰安妇”的档案,其中一件是日军以公款建立慰安所的档案。
“从伪满中央银行的档案可以发现,日军的7990部队在4个月内,花费53.2万日元建立慰安所。”苏智良分析,当时日军少尉军官每月的工资只有几十日元,53.2万的资金算得上是巨款。“吉林省档案馆公布的这份日本军队使用大量的经费用于建立慰安所档案,表明日本政府在‘慰安妇’上投入巨大;同时这些档案都是抄送相关日军部队司令部和宪兵队司令部,表明这是合法的、得到上层批准的。”
苏智良还表示说,“这次公布的档案和在日本发现的陆军省、海军省、法务省和外务省的档案,构成了一个很严密的体系”。
作为将“慰安妇”相关史料提交联合国世界记忆工程的倡议人,苏智良表示,这次中国申报给联合国世界记忆工程的《“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共五大类29组档案,主要包括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侵华日军关东宪兵队档案、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档案、伪政权档案、“满洲中央银行”档案以及日本战犯的笔录供词等。申报单位的档案中,有关于日占区各地“慰安所”设施状况的材料,日军利用“慰安所”的人数统计材料,日军兵员数及“慰安妇”配置比例的统计材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侵华日军强征、奴役“慰安妇”的暴行。
申报资料中还有苏智良提供的24张照片,也全部来源于日本,是他1992年开始研究“慰安妇”问题以来,走遍日本的书店、遍读公开出版的侵华日军老兵各种回忆录搜集得来的。
一位署名“华公平”的日本作者在日本出版的《从军慰安所海乃家的故事》一书,公开揭露其父在上海经营的海乃家海军慰安所1939年至1945年从建立到关闭的整个过程。苏智良提交给世界记忆工程的24张照片中的6张,出自这本书。
苏智良认为,“从各个角度都能够证明,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队和国家推行的制度,是日本政府和军部直接策划、各地日军具体执行实施的有组织、有计划的行为。”
日本必须正视
当记者问起为什么把“慰安妇”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时,苏智良回答说,把这些资料申请进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永久保存下来,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反日”问题,而是希望后人能汲取这个惨痛的不人道的教训。
苏智良表示, 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时,中国政府和人民非常真诚地希望中日合作、友好,在战争问题上是希望日本自己反省,所以没有对日本的战争罪行反复强调,相反还主动放弃了战争的国家赔偿。在“慰安妇”问题上同样如此,由于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调查“慰安妇”问题,随着这些老人的离去,现在很多人证都没了。
直到上世纪90年代苏智良开始研究“慰安妇”问题时,还曾经被有关部门告知,“为了中日友好,这东西(‘慰安妇’问题)最好不要研究;研究了也最好不要公开。”但苏智良个人觉得,为了中日真正的友好,必须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而且事实上,日本后来不断地否认历史,否认强征“慰安妇”的日本国家行为,尤其是拒绝向亚洲幸存的慰安妇道歉和赔偿,让40万“慰安妇”们冤屈得不到伸张。
韩国第一本有关“慰安妇”问题的教科书《不要忘了我》今年正式投入中小学课堂,就是为了提醒人们不要忘了“慰安妇”受害者!
今年7月25日,日本再次拒绝美国、联合国等要求日本承担慰安妇责任。对此苏智良非常愤慨:“实际上,日本有点像鸵鸟政策,以为把头埋起来,别人就看不到这种暴行,这不是一个政府应该采取的态度。”
“我希望日本国民和政府,尤其是日本政府能够向德国学习,要消除日本和亚洲的对立,日本对战争作深刻反省是一个前提、甚至说是一种政治基础。如果没有这种基础,日本就不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做了这些战争犯罪就应该反省。”
谈到在目前的中日关系背景下,慰安妇的研究有哪些意义时,苏智良表示,这是一个二战本应该解决但没有解决的遗留问题,至今影响着日本和中国、韩国的关系、日本和其它国家的关系,而且受害者都没有得到所谓的昭雪,更没有赔偿。为了不让那些死去的人们死不瞑目,为了人类不再犯这样的战争罪行,我们要和日本做斗争。尤其是现在日本安倍内阁越来越危险,如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宪法,千方百计要日本能够成为一个战争国家,这个很危险。
“日本要真正地要和亚洲各国和平相处的话,历史这道关是一定要过的。”苏智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