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7年,27岁的萨布瑞亚即将大学毕业,心怀梦想,她只身来到拉萨。
在拉萨一家名叫八朗学的旅馆里,她结识了之前在非洲救助儿童的荷兰人保罗。她告诉他,自己要在这里办一所盲童学校。之前,她也遇见过很多“老外”,他们对萨布瑞亚想在西藏开设盲童学校的想法都很排斥:你以为你是谁?
让她感动的是,保罗倾听了萨布瑞亚的计划,十分激动,甚至提出要帮助她。
后来,萨布瑞亚筹集到了资金,并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邀请。她打电话给保罗,说自己准备前往拉萨,并有可能在那里住上几年。开始对方没有回应,萨布瑞亚有点难过。突然那边笑起来:“我要辞掉工作去找你。”
5天后,保罗辞去了在荷兰的工作飞到了拉萨。从那时起,直到萨布瑞亚的事业受到瞩目之前,家人一直觉得保罗是一个“拎不清”的人。他们认为他的想法不切实际,不要说前途,就是生活也失去了保障。
萨布瑞亚有着强烈的意志。“一般人有了目标会计较成败,萨布瑞亚不,在她那里,目标和出发点之间是一条直线。她是一个沿着直线径直奔向目标的人,不管中途有多少困难,都会想尽办法一一干掉。”保罗说,“她从来没有惧怕。”
其实,第一次游历中国时,很少有人知道萨布瑞亚手中那根白色杆子——也就是盲杖——是用来干什么的。有人问她是不是放羊的,还有人以为这只是一根普通的拐杖。
在她的畅销书《我的道路通往西藏》中,萨布瑞亚笔下的拉萨是一个又热闹又空旷的城市。这本书的英文版发行了20万册,在德国也卖出了10万册,她的故事打动了很多人。
旅途中,有人向她借手中的盲杖,然后闭上眼睛,体验做盲人的感觉。萨布瑞亚很享受这份融洽,旅途中结交了很多朋友。
激发孩子的梦想
西藏拥有260万人口,和萨布瑞亚一样的视力障碍患者约有3.5万人。
1998年,萨布瑞亚的盲校落成。这是西藏第一所盲童学校,也是拉萨唯一的盲童学校,盲童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免费接受寄宿教育。
盲校的组织工作主要由萨布瑞亚和保罗所在的“盲文无国界”组织负责,资金来自包括德国政府在内的各种机构和个人,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也在其中。
 萨布瑞亚在教学生打字
萨布瑞亚在教学生打字
开始,学校只有6个孩子。萨布瑞亚租了一匹马,骑上它走向170公里外的孜贡,寻找那些有视力障碍的孩子。
“她骑马找孩子的经历真是神奇,她说自己看不见,但是马可以看见,她非常相信那匹马,一直跟着它走。”吉拉说。
如今,慕名而来的盲童远远超出了这所学校的床位。学生中,最远的孩子来自阿里。学校上课不分年龄,根据接受能力分为“老鼠班”、“老虎班”和“兔子班”,开设的课程有英文、藏文、汉语、计算机、美术和音乐等。
其实,帮助孩子克服自己心里的怯弱和自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萨布瑞亚夫妇想出了一个主意:让孩子描摹自己的梦想。8岁的诺布想了一周之后告诉萨布瑞亚,他希望做一个出租车司机。
“太棒了!”萨布瑞亚鼓励说。两年后,她问诺布:“你的梦想咋样了?”诺布回答:“我清楚自己是一个盲人,不可能真的去开出租,但是,我可以开一家出租车公司,雇别人开!”
为了激发孩子的潜能,2004年,萨布利亚邀请第一个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盲人埃里克·威亨梅尔和他的登山团队来西藏指导盲校孩子攀登喜马拉雅山脉一座海拔7000余米的高峰。经过精心准备,6名盲童成功攀登至海拔6500米的高度,刷新了此前盲人团队登山的海拔纪录。这段经历被拍成了纪录片《盲视》(Blindsight),拿了很多国际大奖。
授人以渔
慕名而来的造访者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原本认为残疾人什么都做不了,结果常常大开眼界:孩子们在课堂上敲着打字机大声朗读字母和单词,还可以操着流利的英语和外国人聊天。
学校慢慢有了口碑,又因为全部免费,大家争相把盲童带过来。萨布瑞亚夫妇又在日喀则的一个农场开设了一所盲校,稍大些的孩子可以在那里学习技术性课程。“比如织毛衣、做奶酪、种菜、放牧、制陶等等,那边的学校比这边还大。”吉拉自豪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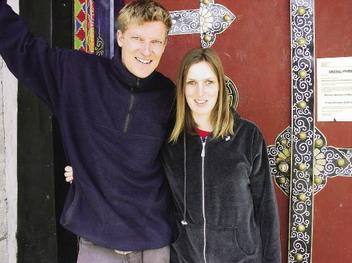 保罗和萨布瑞亚
保罗和萨布瑞亚
拉萨和日喀则的盲童学校仅仅是萨布瑞亚夫妇事业的开始,他们觉得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2009年,他们又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创办了一个国际盲人培训机构。盲人在接受培训后,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独立经营学校。两年的时间,来自24个国家的盲人在那里接受了培训,吉拉就是其中的一个。
“其实,盲人的世界充满了想象,绝不像我们健全人认为的那样漆黑一片。”保罗说。
保罗的家人通过电视、报纸了解到了保罗所从事的事业。2000年,他们看到德国第一电视台拍摄的有关拉萨盲童学校的纪录片,对别人说:“那个在西藏帮助盲童的人就是保罗。”2004年,保罗的弟弟来到拉萨盲校,他告诉哥哥,他也想留在这里帮助孩子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