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照马海德的研究,19世纪西方的那种建麻风村落和聚居地的隔离的方法已经不适合中国。他提出四个原则:不实行住院隔离,而是在社会上预防、治疗;各种药物配合使用而不是一种药,他尤其提倡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与康复并重;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不能光靠医生。
这些治疗方法大大加快了战胜麻风病的进程。1949年诊断出50万个麻风病例,到80年代初期,其中的80%已痊愈,发病率及复发率都大幅度下降。许多市县基本上消灭或是控制了麻风病。
但是,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依然不富足,防治麻风病所需要的治疗药物和资金依然缺乏。马海德向他的国外同行提供详细的报告和分析,并请求给予经济和技术的援助。1979年访问美国的时候,马海德就发动了为中国的麻风病者募捐的活动。从1981年起,他每年都出国,每次总要谈到麻风病,谈到在全世界只要互相理解与合作,麻风病是真正能够消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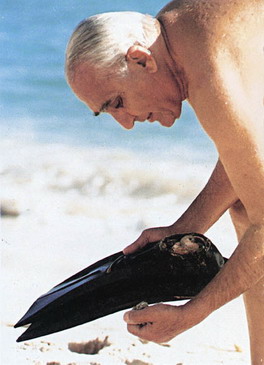 海滨拾贝也是一种爱好
海滨拾贝也是一种爱好
到了1983年,马海德在麻风病防治中的成就已闻名于世界。1983年11月,他被提升为全国政协常委,同月,他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对外友好协会、宋庆龄基金会、国务院外国专家局联合颁发的荣誉证书,褒奖他五十年来对医务工作的贡献,并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举行庆祝宴会。他的老朋友邓颖超、邓小平都发表了讲话,对他赞扬备至。邓小平说:“五十年,不容易!”马海德自己并不在乎,真正使他愉快的是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知道他、爱戴他。
马海德参与的国际活动越来越多,虽然身体不好,他依然旋风般地为麻风病而奔走。1985年,他又去了日本。他与日本的造船大亨笹河,以及笹河卫生基金会的其他人员进行了讨论。笹河曾是日本战犯,他向马海德承诺为中国麻风病治疗捐款,但是前提条件是见到邓小平。很为难的马海德把此话告诉了邓小平,邓小平问:“老马,这件事对你的麻风病有好处吗?有好处,我就见。”马海德点点头,于是笹河见到了邓小平。
 邓小平向马海德祝酒
邓小平向马海德祝酒
1986年,他依然积极地为麻风病而奔走。其中11月,他去纽约接受声誉极高的艾伯特·拉斯克的公众服务奖,这是该奖第一次授予中国公民。褒奖文上说:“马大夫贡献之重要性,能与消灭黄热病和鼠疫相比,而作为公共卫生控制性病的模范,是独一无二的。”
在他去世的那一年夏天的时候,他已经吃不进去任何东西了,但他还要去北戴河参加麻风防治外援计划座谈会,他说:“哪怕要爬着去,我也要参加。”
8月到北戴河时,他连水都喝不进了。许多参会的医生都记得,马老显得从未有过的消瘦与衰弱,拖着缓慢的步伐来到了会场,以微弱的声音坚持作了近一个小时的发言。会议结束后的那天晚上,他还坚持约见各地来参会的人员,很多人记得当时他已无力坐着,只能躺着。
当他从北戴河回到北京,他的儿子周幼马将他抱下火车时,幼马发现“他轻得很”。
9月,他对朋友沙波理说:“再有两年时间,我就能打败麻风病了。”
一直到最后,他还想着麻风病。儿子周幼马把他侄子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寄来的一笔捐款递给他,他轻声说:“捐给麻风病基金的,一定要交到基金会去。”
1988年10月3日,他去世了。唁电、唁函从世界各地如潮水般涌来。
如今,马海德基金会依旧为麻风病的治疗提供扶持和帮助,他的妻子苏菲和儿子周幼马一直延续着他的奋斗目标——消灭麻风病。
本文为纪念马海德诞辰100周年而做,以纪念他为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所做出的贡献。本文由马海德之子周幼马的口述,参考了苏平、苏菲的《马海德传》、沙波理的《马海德传》以及曾经跟随马海德一起工作过的医生们所撰写的回忆文章,编辑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