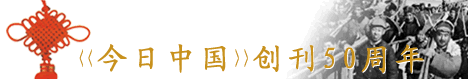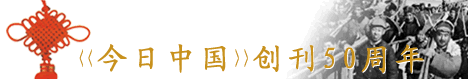作为对中国的前途抱有乐观态度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无疑是很温情的,这一点不难从他充满智慧的经济学随笔中感觉得到。但作为改革进程中所出现的社会腐败与社会不公现象的见证者,吴敬琏无疑又是很忧愤的,这一点在他众多抨击时弊的谈吐中显得特别鲜明,充分体现了一个经济学家的社会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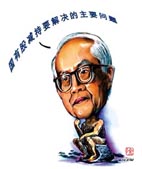 用智慧与良知拨开迷雾
用智慧与良知拨开迷雾
--解析经济学巨擘吴敬琏
吴志菲 余 玮
吴敬琏,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市场经济理论之父。1930年1月生于江苏南京,195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历任中国科学院(后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等职。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是唯一连续五年荣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芳经济科学奖的学者。
在2001CCTV中国年度经济人物颁奖典礼上,当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经叔平开启2001CCTV中国年度经济人物大奖的信封,读到:“他敢于铁肩担道义,他是一位无私的、具有深刻忧患意识的社会贤达,一个纯粹的人、一个特立独行的智者,一个睿智和良知兼备的中国学者,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优秀代表,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高贵品格,年过七旬仍然能够保持童真和率直的经济学家”的时候,台下500名观众自发地全体起立、鼓掌。这无疑是对2001CCTV中国年度经济人物大奖获得者吴敬琏的最高褒扬。
“小时候,母亲及家庭对我的影响很深刻。”
 吴敬琏出生在江苏省南京市一个有着几代民族资本家传统的书香门第。母亲邓季惺是律师、报业家、社会活动家,是当时有名的“报业大王”。30年代与其父创办上海《新民报》(现《新民晚报》),后到北京创办《新民报》(现《北京日报》)。《新民报》后来扩展为旧中国最大的一家民营报业集团,一度创下五社八报的业绩。
母亲对他的影响很深刻,母亲邓季惺是一个喜欢依法办事的人,用吴敬琏的话来说是“我母亲比我父亲更现代化。”吴敬琏所说的“现代化”,是指在办报中,父亲更多的是靠他的个人关系,而母亲更多的是靠规章制度。参加《新民报》的经营管理之后,她最先做的事情就是建立健全了财务会计、广告、发行、印刷等方面的制度,使新民报馆逐步走上企业化经营的道路。所以有这样一种说法:邓季惺精明到报馆里用了几根大头针她都有数。吴敬琏说,他至今不喝酒、不抽烟,就是源于早年母亲对他的教诲。温实敦厚的家教,使吴敬琏的身上总透着一种学者气质和大家风范。
“因为父母都是新闻记者出身的,记者有一种很好的素质,就是对新的事物的敏感性;我的一些阿姨、叔叔他们也都是大记者,也许是记者的敏感性对我的影响,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点东西,80年代初便开始使用电脑。其实,经济学家一定要对新的事物具有敏感性,因为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活动,特别是我们处在现在这样一个改革的时代,如果老是拘束在旧东西里面,就很难做好经济学家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吴敬琏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巨大高潮即将到来,下决心选学经济学。“革命救国已经实现了,要做点什么事呢,那就是做经济建设,所以我就选学经济。”1950年,吴敬琏接着读书,学的是经济专业,当记者问他:“假如时光倒流50年,您会挑选什么专业?”老人毫不迟疑地回答:“经济学。经济学太有意思了!”
吴敬琏出生在江苏省南京市一个有着几代民族资本家传统的书香门第。母亲邓季惺是律师、报业家、社会活动家,是当时有名的“报业大王”。30年代与其父创办上海《新民报》(现《新民晚报》),后到北京创办《新民报》(现《北京日报》)。《新民报》后来扩展为旧中国最大的一家民营报业集团,一度创下五社八报的业绩。
母亲对他的影响很深刻,母亲邓季惺是一个喜欢依法办事的人,用吴敬琏的话来说是“我母亲比我父亲更现代化。”吴敬琏所说的“现代化”,是指在办报中,父亲更多的是靠他的个人关系,而母亲更多的是靠规章制度。参加《新民报》的经营管理之后,她最先做的事情就是建立健全了财务会计、广告、发行、印刷等方面的制度,使新民报馆逐步走上企业化经营的道路。所以有这样一种说法:邓季惺精明到报馆里用了几根大头针她都有数。吴敬琏说,他至今不喝酒、不抽烟,就是源于早年母亲对他的教诲。温实敦厚的家教,使吴敬琏的身上总透着一种学者气质和大家风范。
“因为父母都是新闻记者出身的,记者有一种很好的素质,就是对新的事物的敏感性;我的一些阿姨、叔叔他们也都是大记者,也许是记者的敏感性对我的影响,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点东西,80年代初便开始使用电脑。其实,经济学家一定要对新的事物具有敏感性,因为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活动,特别是我们处在现在这样一个改革的时代,如果老是拘束在旧东西里面,就很难做好经济学家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吴敬琏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巨大高潮即将到来,下决心选学经济学。“革命救国已经实现了,要做点什么事呢,那就是做经济建设,所以我就选学经济。”1950年,吴敬琏接着读书,学的是经济专业,当记者问他:“假如时光倒流50年,您会挑选什么专业?”老人毫不迟疑地回答:“经济学。经济学太有意思了!”
大学毕业后,吴敬琏被分配到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研究实习员,从事财政、企业财务、价格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问题的研究。
“顾准,是我一个可遇不可求的老师和朋友。”
初出茅庐的吴敬琏尚未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便接踵而至,无情地封杀了他的独立研究和自由声音。“文革”中,吴敬琏先是被定为“帽子拿在人民手中的反革命分子”,后因被军宣队抓住吴敬琏所谓“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证据,而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在饱受精神摧折的同时,他得到了一个可遇不可求的老师和朋友——顾准。
其实,一开始吴敬琏对顾准的思想理论并不完全理解,他也曾经真心地迷信“左”的思想和潮流,甚至在运动中对顾准进行过口诛笔伐,这是他终生的愧疚。没想到吴敬琏与顾准在“牛棚”里结成了忘年之交,相濡以沫,并一起冷眼观察极“左”派的疯狂表演。吴敬琏说,“顾准是一个卓越的思想家。在那场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1956年,顾准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也可以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的观点,这在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是非常超前的。吴敬琏之所以能够改革开放后,率先提出市场经济理论的观点,是受顾准影响的。
在顾准的帮助和启发下,吴敬琏开始恢复和提高英语阅读能力,从希腊史入手学习了世界文化史、经济史与政治史,并回过头来同顾准一起分析中国的问题、探索人类历史的未来发展。虽然二人对其中的某些问题看法不一,互不相让,常常争论得脸红脖子粗,但在思想上受到了启迪和补充。吴敬琏说“当时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参与这种能够启发人的思想的自由讨论了,这种机会居然在被打成反革命的情况下得到,真是一种奇缘。”
1974年12月3日,弥留之际的顾准把自己所有的手稿分别托付了吴敬琏与胞弟保管,并用尽气力对吴敬琏说了最后一句话:打开行军床,睡觉去吧。这句平平淡淡的临终遗言,给吴敬琏以后漫长的治学生涯以巨大的鼓舞与激励。
1976年,绕了一个大弯儿的吴敬琏重返经济学界,从此忙得不亦乐乎。这期间,他参与策划和组织了“按劳分配讨论会”。受孙冶方、薛暮桥等人的启发,吴敬琏意识到改革不能零敲碎打,而要建立一个能有效运行的经济管理体制。但它的核心机制是什么?如何建立?都还没有答案。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使我成为政府经济学家。”
1983年1月,53岁的吴敬琏只身远赴美国耶鲁大学从事客座研究。他发现,要发展现代经济,不懂得现代经济学就寸步难行。于是,他“放下架子,从头学起”,对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进行了系统的“大补”,从经济学原理学起,一直到博士生的讨论课。“这时,只觉得与国际经济学界的距离太远了,已是个正教授的我似乎是个小学生,挤在一群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中去听课。”这段学习、研究与思考,使他对现代市场经济概念有了全新的认识,使他获得了一种信念:任何真正的改革,都应当是市场取向的,即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形成“整体协调”的改革。
1984年7月,吴敬琏一回国,当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就约他到东北去出差,起草一份关系改革大局、为在1982年遭到批判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翻案的论文。期间,马洪多次跟吴敬琏讲,你干脆到我们这边来算了,何必又回到社科院。吴敬琏自己也觉得他们的工作挺有味道的,能更好地实现个人的价值,就答应了。于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日后有了一位推动市场经济的“大力士”,他的著作也被称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蓝本”。
有人曾对吴敬琏转入政府咨询机构——国务院发展中心工作颇有微词。吴敬琏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一个人在哪里工作,而在于他秉持什么样的主张。“并不因为你当了政府经济学家,就变得道德低下了。要那么清高干什么呢?你不是要改变这个社会吗?不是要为人民造福吗?在政府机构里面,不是完全可以和在民间机构里做得同样好么!”
“把我叫做‘吴市场’,其实当时是一种贬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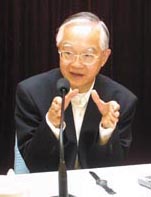 吴敬琏有个大名鼎鼎的外号叫“吴市场”,可有几人知道,当初这“吴市场”可并非美誉。“我在1990年7月的一次会上跟人们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有位中央领导同志还在我的报告上批示——‘市场就那么灵吗?’会后,人们把我叫做‘吴市场’,其实当时是一种贬义。”后来,市场经济在中国越来越得到官方和民间的认可,“吴市场”才变成人们对他当初具有先见之明的赞扬。
吴敬琏有个大名鼎鼎的外号叫“吴市场”,可有几人知道,当初这“吴市场”可并非美誉。“我在1990年7月的一次会上跟人们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有位中央领导同志还在我的报告上批示——‘市场就那么灵吗?’会后,人们把我叫做‘吴市场’,其实当时是一种贬义。”后来,市场经济在中国越来越得到官方和民间的认可,“吴市场”才变成人们对他当初具有先见之明的赞扬。
经济发展了,要归功于市场经济,但也有人把社会中的一些不尽人意的现象归罪于市场经济。对此,吴敬琏说:“不可否认,市场经济是一种存在很多缺点的体制,但较之人类迄今试用过的其他体制而言,它是最佳的。在中国,除了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别无他途。现在社会中出现了一些消极乃至丑恶的东西,并不是由于市场趋向与改革造成的,而是由于我们的改革还不够快、不够彻底造成的。”
吴敬琏1989年写成《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许多家出版社不敢出版。直到1991年下半年,中国财经出版社的社长和总编辑在一份出版批文上提心吊胆地一起签上了各自的姓名,这样“一旦有事,共同承担”。此书出版恰逢小平南巡讲话,一席话澄清了经济理论界长期的争论,第一版的7000册不到一个月便被抢购一空,不得不加印。后来,该书获得了“中国图书奖”,1998年被评为“影响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之一。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最终被写进党的“十四大”文件,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基本目标,目前已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中占主导地位的思路。这不仅是我国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包括吴敬琏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长期探索、积极倡导的结果。
有人曾这样描绘吴敬琏:“他大半辈子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度过的,但满脑子是市场经济的思想。”他说,“我说的那些东西,是经受了实践反复检验的,是经过自己深思熟虑的。因此,我觉得心里有数,这个东西一定是对的。在拿不出有力论据加以否定的情况下,我不会轻易地放弃。”
透过吴敬琏新近出版的《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一书,我们便不难看到改革之路的艰难与一个经济学家跳动着的一颗火热的心。很显然,就经济研究工作而言,吴敬琏的众多经济理念是符合国情的。他有满腹的东西方现代经济学知识,但他从不在书斋中实行形而上学的本本主义,而是不畏年岁已高和身体虚弱,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发达国家做深入的市场经济研究,到国内沿海一带广泛考察民营企业,到大中型国营企业探讨战略性改组方案;然后不断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式拓展自己的研究空间,敢于打破思想禁锢与突破理论禁区,及时诊断出中国经济改革的症结所在,准确开出有效的“药方”,并努力使其成为决策者或决策部门指导经济工作的重要依据。
“我难得忙里偷闲,听听音乐。”
吴敬琏总是有做不完的工作与探讨不完的理论,吴老的夫人周南解释说:“这些年他越来越忙,每周的日程都排得满满。要是以前,想忙也忙不了。”
因为忙,吴敬琏没法顾家。温文尔雅的周南原是北师大教授、儿童教育专家,为了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15年前她牺牲自己的事业,退为家庭主妇,兼作“秘书”,现在书房的所有书柜中,摆放的都是吴敬琏的藏书,她的书则挪放到角落里。
每天晚上12点过后,时间才真正属于吴敬琏,没有电话的干扰,也没有客人的拜访,他可以安安静静地读书、做笔记。政府决策需要经济学家,企业经营、老百姓的生活需要经济学家。吴敬琏谦虚地说,“在这么一种被多方面强烈需求的状态下,我总觉得有很强烈的紧迫感,总觉得力不胜任。这个力不胜任,首先还不是体力上的不胜任,而是思维能力、研究能力的不能胜任。”他认为经济学发展很快,过去东方国家中实行的都是计划经济。如要迎头赶上经济学的发展就要从西方去汲取营养。
有人讲,做学者,搞研究,最好是清心寡欲,不问俗事,否则很难在学术领域有所作为。而吴敬琏偏偏又是一个爱好广泛的人。年轻时,他喜欢运动,后来又迷上了集邮,集古钱币,更喜欢听音乐。听古典音乐,是吴敬琏在大学时代培养起来的爱好。在复旦大学,他是音乐欣赏社团的“铁杆”成员。“文革”后期,卡式磁带刚上市,吴敬琏便不惜“巨资”买了一个现在看来像个砖头样的录音机。当收音机有了调频广播、播放古典音乐时,他就认真地听和录,积攒了大量的音乐磁带。有了CD,他便转向去听CD,而那些磁带还是舍不得丢弃。因为职业紧张的原因,如常常处于激烈的辩论,所以吴敬琏爱听舒缓一些的音乐,最喜欢的是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经济学家在工作的时候,不要有太多的激情。太多的激情,就容易不冷静。”这是他的生活态度。但是他实在太忙了,尤其是近几年,学术会议、专题分析、政策研究……他的时间总是排得满满的,很少有时间呆在家里静心欣赏音乐,连集藏了几十年的邮票也无心再坚持了,不得不把几本大邮册送给女儿。
待人和蔼可亲的吴敬琏,知识丰富,见解独到又十分健谈。他的品质修养、脾气秉性和执着的人生追求,确同自己的母亲如出一辙。不管是言过其实的盛誉,还是无端贬低的嘲讽,吴敬琏都能泰然地一笑了之。这种对生活宠辱不惊的恬淡心态,颇有点仙风道骨之状。他从不抬高自己,也不无缘故地轻视别人,与之交谈很愉快而且受益匪浅。
“社会良知,是我作为经济学人的立身之本。”
真正的经济学家,应该有“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浩然正气,应该有忍受孤独、寂寞,能在纷至沓来的干扰与形形色色的诱惑中坚守自己清白的毅力和勇气。吴敬琏不是一个沉湎书斋、孤芳自赏的名士,更不是一个愤世嫉俗、清高自傲的腐儒。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时时以民生国运为已任。他的建言,既不唯上,也不唯书,更不媚俗,常常显示出特立独行的风格。吴敬琏始终以一个学者的良知站在经济改革的前沿,以巨大的热情关注着改革的每一步发展,并提出真知灼见。
在生活中,吴敬琏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但在学术领域,他却以敢于直言而著称。他信奉:对科学对真理的追求,只能采取科学的态度。因此,在任何场合他都不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不管是与高官、大贾,还是与中国最高领导人直接的对话与交谈,吴敬琏都能直接地说出自己的所思所想。他只想着如何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得清楚明晰,其他的就顾不得许多了。当然,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吴敬琏是不可能这么做的,他甚至也不会想到要这样做。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都没有真正的经济学,有的,只是对‘最高指示’、现行政策的诠释和辩护”。鹤发松姿的吴敬琏,不愧是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的脊梁。率先向僵化的计划体制挑战,首先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批判,最早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是吴敬琏。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于祖尧所言,其贡献与“两弹一星”升天相比,毫不逊色。
2001年吴敬琏对于股市中违规违法活动提出了批评,站在中小投资者的立场上呼吁加强股市监管,并使这种呼吁成为2001年中国资本市场最主流的声音。作为中国经济界一言九鼎的人物,关键时刻的这番讲话,不啻于在证券界与经济理论界引爆了一枚重磅炸弹。“吴敬琏一言毁市”的攻击,颇让他感到很大的压力。“中国的经济问题很多,该说的还是要说的,但我不一定是对传媒说。”吴敬琏进一步指出,股市泡沫要挤掉,基金黑幕要曝光,否则有序的市场经济就无法实现,改革的预期成果就要大打折扣。
入世后各种政策性“壁垒”逐步放开,中国的经济弱点会明显暴露出来。吴敬琏认为,“入世后,机遇是潜在的,挑战是现实的。入世不是天上下金雨,但更不会前景黯淡一片。”他认为,加入WTO将给中国带来非常大的推动力。目前,吴敬琏主要是研究我国经济改革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他说,“经济改革中的所有问题都在我的视野之中,但是,哪个问题最突出,哪个便是我研究的重点问题。”如果说1949年中国在政治上站了起来,那么世纪之交的改革,将使我们在经济上站起来。
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始终充满活力,与政府职能部门中的一大批有经济改革“马前卒”之称的经济专家的参与决策无不关系。他们视野开阔,观察敏锐,而且有深重的历史使命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及学者良知。吴敬琏,便是其中之一,坚持用自己的思想智慧与社会良知,不断拨开前进中的迷雾,从而赢得了时代的认可与社会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