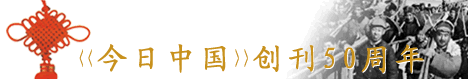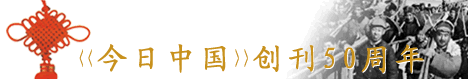溯江而上,朝拜母亲河源头
张力
长江上游,从通天河以下至宜宾约2200公里湍急曲折的干流河道,称为金沙江。她是一条传奇优美的江,又是一条狂放不羁的江。其年平均水量1450亿立方米,相当于黄河的三倍;水能总蕴藏量1亿千瓦,占整个长江的43%。据水利部门介绍,长江的泥沙70%来自金沙江,治理金沙江流域的水土流失,对于保护长江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元谋人新的传奇
北出昆明174公里的元谋县,因出土了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化石而闻名于世。它地处金沙江流域的干热河谷,最高海拔2800多米,年均降雨量600毫米,年蒸发量却高达3900毫米;尽管植被茂密,总体上仍然干旱缺水。到达元谋县的当天,昆明日最高气温摄氏22度,元谋则达到摄氏35度。
元谋,这块云贵高原上不算大的山间盆地,在遥远的往昔曾经相当富庶,而千百年的灾害累积至今,全县水土流失面积已在长江上游高居第一。1989年,国家将元谋县列为“长江上游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机。12年过去了,元谋的植被覆盖率由25.5%提高到72%,农民人均纯收入由341元增加到1775元,县财政收入由680万元增加到2381万元。
元谋县采取的恢复生态环境的办法之一,就是对全县的荒山、荒坡、荒滩、荒地公开拍卖、自愿承包。打破所有制界限、行政区域界限、承包期界限和投资经营规模与范围的界限,充分发挥国家、集体、民营企业与个人的力量。目前,全县累计购买“四荒”地7.3万亩,扶持发展了户均购买“四荒”地50亩以上的专业户、重点户157家。
在一处生长着成片香蕉林和其他作物的高岗上,我们见到了全国治理开发“四荒”示范户郑子琼,一位出身于元谋热坝的彝族妇女。她告诉我们,历史悠久却生态恶化的家乡,曾经痛苦地折磨着她。1990年,她打定主意用多年在外经商赚的钱回报家乡,回报大地。如今,环顾郁郁葱葱的绿色植被,人们很难想象这里十年前的模样。一个女性,12个难以细述的春秋,400万元血汗投资,6000亩得到综合治理的荒山——在发现元谋人的地方,这是一个新的传奇。
洱海没有步滇池的后尘
到大理之前,我们曾担心洱海会不会像昆明的滇池那样,随着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发展,出现水质的严重恶化。当我们来到洱海岸边的时候,看到的是青山白云映衬下,碧波荡漾,水体透明。乘船横渡整个湖面,很少看到在一些风景区常见的漂浮物。这条满载数百名游客的大船上,厕所是免冲水的,垃圾实行分类收集,对发动机产生的废油也进行了专门处理。尽管在湖上航行了四个多小时,但游船上并没有设餐厅,以免污水排入江中。
同船的云南省人大环资委副主任薛惠新女士欣慰地告诉我们,洱海目前的水质,从全国范围来看,也是不错的。她说洱海周边人口和企业密度较低,洱海的蓄积量约24亿立方米,比滇池大一倍多,并且有两个排水途径,每年又有2亿吨新水进入。加之,洱海的综合治理比较及时、得力,有相应的立法保证,对整个风景区实施统一管理,因而蓝藻危害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记者在大理街头采访了几位市民,他们说他们的生活用水都是取自洱海,水质比前些年好多了。
目前,洱海水质总体上达到二类,水环境质量保持相对稳定,成为中国保护得最好的内陆湖泊之一,开创了一种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相结合的成功模式。
二滩库区最后的漂木

二滩库区最后的漂木 |
我们翻过滇西北的高山,行进至四川南部攀枝花市。中国已建成的装机容量最大的二滩水电站就坐落在流经这里的雅砻江上,今年计划发电量127亿度。在距大坝两公里的盐边县红果码头,只见辽阔的库区水面上漂浮着大量原木。一些工人正忙着将漂木捞起,用传送装置送上去,再用卡尺量过,装车运往60公里外的金江火车站。一位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原属于以经营漂木为主业的雅砻江木材水运局,自1998年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以后改为长江造林局攀枝花分局红果林场,他们由砍林人变成了护林人。
他介绍,1997年二滩大坝合拢,漂木便聚集在库区,然后再由陆路转运,多的时候水面上漂浮着足有20万立方米木材,都是上好的冷杉。到1998年禁伐以后,便形成了这一大片蔚为壮观的最后的漂木。红果林场的140多名职工除护林外,夜以继日地打捞漂木,每天从早7点忙到天黑,周末无休。这位负责人估计,用不了多久这片最后的漂木就将永久地消失了,这也将意味着一段沉重历史的终结。
走近青藏铁路

铁路将从格尔木向西藏延伸 |
我们从青海西宁启程,踏上通往雪域高原的青藏公路,向着长江源头的沱沱河进发。青藏公路是世界上环境最恶劣的公路之一。当年为修筑这条路,平均每一公里就牺牲一名战士,那都是些能征善战的精兵。即使是现在,我们坐在面包车里,仍然会感到不适。渐渐地接近了雪山,海拔也在从2000多米升至3000米、4000米,直至风火山的5010米;沿途经过了雄浑的昆仑山口和令人生畏的五道梁,气温已从零上十几度陡降到零度以下。这时就是坐着不动,也会有头疼、乏力的高原反应。
一路基本上与正在加紧建设的青藏铁路平行,看到了一个接一个整齐铺开的施工现场、大段大段垒好的路基和一处处正在开挖的隧道,青藏公路旁的戈壁滩上还立起了一个个保护生态环境的大幅宣传牌。青藏铁路在建设中对沿线的生态环境保护有严格的规定,包括不允许从当地取石取土(打隧道挖出的土石除外),翻动的草皮要移植回去,以保护植被;工作面尽可能缩小,以降低对野生动物的影响;专门设置高架桥和路轨下的通道,以便野生动物通过;尽量租用当地已有房屋,集中构筑活动板房等非永久性建筑,等等。
在青藏公路的艰难行程中,我们幸运地在广袤的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边缘先后遇见大约七八十只藏羚羊,它们在离公路很近的地方安静地吃草;但都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一发现有人注意并企图接近它们,便会立即向远方飞奔,姿态优美轻盈,难怪它们被称为“高原精灵”。而且,它们都是一只公羊带领几只或十几只母羊,组成一个小家庭。目前正值交配季节,如果不出意外,到来年6月就可望产崽了。
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自从1997年12月国务院批准建立这片面积广阔的保护区以来,已经设立了4个保护站,成立了拥有50多人的巡山队。他说,保护区刚建立时,青藏公路边上根本看不到野生动物,只有电线杆上偶尔落着乌鸦。前些年在可可西里北部地区的河流附近,也是珍稀野生动物最喜欢栖息的地方,从去年开始,政府禁止采金;加之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反盗猎措施,使生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登上中华水塔
行进了8个多小时之后,我们在9月3日下午3点40分看到了沱沱河大桥,看到了沱沱河兵站楼顶上的红旗,更看到了长江源头——沱沱河的一股股河水。我们差不多都忘记了身在海拔4600多米,忘记了原本严重的高原反应,直奔“长江源纪念碑”,或直奔陡坡下清澈的河水。
位于海拔4600米的沱沱河水文站是万里长江第一个水文站,是观测长江源头区降雨量、来水量、来沙量唯一的水文站。建站45年来,该站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克服种种困难,积累了珍贵的水文资料。记者团来到沱沱河水文站时,见到站房破损无法使用,只能借用河畔的铁路系统一个简陋的平房招待所。几个房间都是工作室兼寝室,设施陈旧,生活用具简单,没有电视机、计算机。但整齐地摆放着测量工具和仪器,水文记录本规范地记载着每日工作情况,墙上贴着规章制度和管理条例。全站有6名职工,在此工作最长的已15年,长期不能与家人团聚。去年,因建成了兰西拉光缆工程,站里才通上电话。
长江由格拉丹冬雪山的姜古迪如冰川孕育而成,干流在青海省境内有1206公里,海拔多在4000米以上。长江水量的25%来自青海省,源头的生态环境状况直接影响到全流域。
一位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的工作人员说,如果失去了草原,藏羚羊和其它的珍稀动物就会消失。有关专家建议,要保护长江源区,就应该禁牧封育,把长江源区的牧民迁移出来,恢复自然生态。这一点并不难做到,因为在源区生活的人口不多,像沱沱河沿的唐古拉乡面积5.1万平方公里,只有1180人。随着青藏铁路的建设和青藏高原的旅游开发,完全可以吸纳这些人。记者从长江源区返回格尔木的途中,看到了一个封育的草场,全部用铁丝围起来,水草丰美,草有一尺多高,地表湿润,这说明中度退化的草场通过封育是可以恢复生态的。
在沱沱河畔,记者凝望着夕阳辉映下静静流淌的河水,不禁在想,我们的生命是谁给的?既是生身父母,也是大自然母亲。长江千百年来孕育了我们这个民族,我们怎么能不对她顶礼膜拜?怎么能不对她倍加爱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