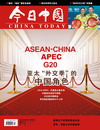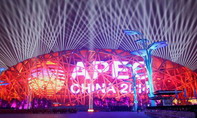60岁时,我出了一本书画集《墨缘》,同时写了一篇文字《六十自述》。我与书画笔墨结缘,出自天性,始于童年。及长,爱好成了我的职业,持之于花甲,“不忘初心”,我似乎做到了。
光阴荏苒,不期然间,我已经70岁了。孔夫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杜子美诗云:“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70岁,在今天已不稀奇了,但作为人生偏后的一个阶段,“从心所欲”则是理想的选择,而我心底的欲,实在离不开艺术,那是我的精神家园、快乐所在。因之,我又想到《论语·述而》篇的句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游于艺,何其自由自在,得于心而应乎手,赏于心而悦乎目。“游于艺”,自然成了我70岁书画及珍藏集子的名称,也就是此文的题目了。

60年代初,我考入了江苏省国画院专修班,受到傅抱石、钱松嵒、林散之、亚明、宋文治、魏紫熙等名师的指导。其时,画院在旧总统府内西花园的桐音馆中,举办过“扬州八怪”艺术研讨会,陈之佛、俞剑华、傅抱石、罗叔子等大师的高论,引起我对画史的兴味和对传统的思考;“新长安画派”的交流会上,又认识了石鲁和他走着的新路,那是一条开掘生活、开掘心灵的路;作为中国现代舞先驱者的吴晓邦,也曾为我们作过舞蹈语言的演示,又让我知道,画外的天地如何宽阔。1962年夏,我有幸随江苏画家代表团(成员有钱松嵒、俞剑华、亚明、张文俊、陈大羽和我)访问山东。在青岛海滨,与北京、上海、山东的一批画坛名流(吴镜汀、李苦禅、王雪涛、郭味蕖、田世光、颜地、王个簃、江寒汀、孙雪泥、朱复戡、关有声、黑伯龙、于希宁等)雅集,谈艺作画,观摩切磋。其间,我第一次登上了东岳泰山,在山巅不仅观览了日出的壮丽,还领略了佛光的神奇;又曾访曲阜,下榻幽深的孔府,仿佛穿越了千载时空,感受古代文明的丰厚。那时我年方20,襟怀为之大开。
1963年画院毕业,进入南京博物院,在那座梁思成设计的辽式大屋顶建筑中,我埋头于数以千万计的古代书画中,从事鉴真辨伪的艰苦研究。那时,沉浸在求得新知的热情中,如饥如渴,从没有过午睡(竟延续到今天),自靠近的“金陵八家”到吴门画派、浙派、四僧、清六家与“扬州八怪”,又上溯元人和宋人……导师是姑苏老人徐沄秋。70年代中,又拜师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徐邦达,并随其鉴阅了故宫及苏、浙、皖、沪数省市的馆藏书画作品。自70年代开始,负责全省书画鉴定工作十余年,经眼书画过万。“文革”后期及改革开放初始阶段,为国家抢救、保护了一批批珍贵的书画文物。

1981年,我调回江苏省国画院工作,成了职业书画家。然而,多年养成的研究习惯是不易改变的。我坚持着书法、绘画、鉴定和史论写作四项并举的方针。在绘画创作上,也兼顾着山水、花鸟和人物三个方面,不拘一格,有感而发。对于书籍和艺术真品的博览,对于大自然的体察和感悟,年复一年,从未懈怠。我相信,建筑一个广阔、深厚的基础,才有塑造成功大厦的可能。在我步入“不惑”之年的时候,将画室名“朝华馆”改为“爱莲居”。“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莲花,成了我的“偶像”。淡于名利,不倚不傍,唯真、善、美是求。
1983年,作为江苏文化艺术界第一位访问学者,我应邀去到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举行演讲会和讲座,把悠久而优秀的中国艺术及我的研究心得,介绍给异国同行和爱好者。同时举办我个人的第一次画展,并考察了旧金山、洛杉矶、堪萨斯、克利弗兰、纽约、波士顿、华盛顿等近十家博物馆,鉴赏了几乎所有美国存藏的中国书画珍品。
1984年,我应邀访问日本,鉴阅了东京国立博物馆和京都国立博物馆收藏的中国书画珍品,与日本著名南画家大山鲁牛及美术评论家远藤光一会晤交流。同年,又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方艺术史系的邀请,被聘为“卢斯基金”研究员。
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中国书画鉴赏”系列讲座,历时一月。
1996年春,在美国圣玛丽学院和明德大学,分别作了“中国书画艺术”的系列讲座和演示,历时两月。其间,两赴纽约在大都会博物馆观摩中华瑰宝——台北故宫所藏书画精品。
1996年秋,在新加坡艺雅鉴赏社,作“中国画的本质和中国画的鉴赏”系列讲座,历时一月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