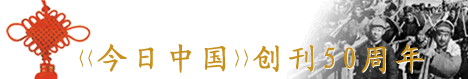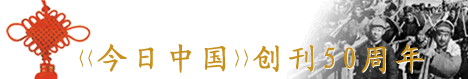眼之缘
——记洛杉矶华人眼科大夫王森林
鲍文清
一个极偶然的机缘让我结识了远在美国的眼科大夫王森林。说起来,这段机缘,实际是“眼缘”。因为一切是从我的眼病开始的。那是去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的一个好友谢天成从美国洛杉矶打电话给我。他总是这样,往往搞不清美国的白天恰好是北京的夜晚,总是选择在晚上给我打电话报告他的新消息。这天他打来电话,我正在害眼病,左眼痛得死去活来,我一手捂住左眼,一边有气无力地接电话,我说:“天成啊,我的眼睛痛得厉害,没法跟你说话,有什么事明天再来电话吧!”谢天成听了也很焦急,向旁边的人嘀咕了一阵,马上又有另一个人接过电话对我说:“你的眼睛怎么了?”我说:“原来诊断是青光眼,现在很痛!”他说:“啊,青光眼,那一定是眼压太高,你得马上去医院。”我说:“算啦,现在是深夜,明天再去吧!”他说:“我要告诉你,我就是个眼科医生,眼压高可不能小视,严重时能导致失明,你听我的劝告,明天就到医院去吧,快去,一定不能耽误了!”匆忙中,我甚至来不及询问这位热心的眼科大夫的姓名,电话就挂上了。过了两个小时,大概是深夜两点多钟,电话又响了。此时,我的眼痛已经略有减轻,但是没有入睡,电话里传来另一个陌生的声音,她自报家门说:“我是301医院的眼科主任李星星,是美国的王森林大夫告诉我你的病情的,请你明天一定来找我!”这一夜,我为这两位未见面的朋友所感动,整夜未合眼。
我做完了眼科手术后,那位从未谋面的王森林大夫差不多隔三五天便来一次越洋电话,不时提醒我有关术后眼睛保养的事宜。我则一直渴望能亲眼见见这位远在异邦的大夫。
转过年来,也就是2002年1月,计划中的访美之行终于成行了。我去看望在美国的儿子和孙女,当然也趁此机会拜访渴望一见的王森林大夫。王大夫住在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我儿子在华盛顿,一个在西部,一个在东部,相距几千公里,乘飞机也需六七个小时,途中经过新泽西州,还要倒一次飞机,但我还是横下一条心,千难万难也要去见一见这位王大夫。我们在美国已经通了电话,他十分欢迎我能到洛杉矶来,他说他一定要到机场接我,吃住都在他家,并且招待我畅游洛杉矶。我知道王大夫诊所的事情很忙,让他不要到机场接我们,改由我认识的一位朋友黎先生派人来接。
儿子和儿媳到美国后,还没去过洛杉矶,听了我与王森林的交往十分感动,就订了机票,陪我一起走一趟。
刚到黎先生家,就接到了王大夫的电话。果然不出我的所料,王大夫此刻还在诊所忙着,我们约定晚上见面。黎夫人说,为了迎接我们,王大夫忙了几天,又是安排日程,又是考虑吃住,一切都是他操办的。
晚上八点,我们驱车来到了阿罕布拉市王森林的诊所。门关着,静悄悄的。突然,大门敞开,有人喊了一声鲍大姐!接着从屋里奔出一个人,嘴里不停地喊着鲍大姐、鲍大姐……不用说,这来人就是我日思夜想的王森林大夫了。只见他50岁左右的年纪,微胖的身材,慈眉善目,精力充沛,一把抱住我说:“我们终于见到了!”忽然又一把推开我,用医生特有的眼神盯住我的双眼,“怎么样?手术后好一点了吧?!还痛吗?”我强忍住激动的眼泪说:“真想早日见到你,托你的福,好多了!”他说:“我这里有检测仪,我再给你检查一下。”当晚他为我们在洛城有名的海鲜馆举行了欢迎宴,还请了黎夫人和好莱坞的一位作家作陪。席间,我和王大夫讲了我们之间不平凡的相识,大家都颇惊讶,见惯了美国社会世态炎凉的儿子说:“只有在中国人之间,才有这种非同寻常的友谊。”当晚,我们就住在王大夫事先为我们安排好的林肯酒家。
王大夫的诊所开在一条商业街的后街,离住所有半小时车程,是一栋二层小楼,有六间房子。进门是一间挂号室和候诊厅,循走廊走进去挨排有五间诊室,分别做针灸、按摩之用。一间放置眼病检测仪,一间治疗眼病。王大夫在这里为我检查了双眼的术后恢复情况,他挺满意地说:“手术做得很成功,你可以永远告别青光眼了!然后再做一次白内障,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写作20年了!”我发现这所诊所,规模虽然不大,但一切设施都是以人为本的。一进门就令人感到一种温馨的家庭气氛。客厅墙角上摆着一个电视,窗台下面有一个一米多长的大鱼缸,鱼儿在水里面欢快地游动;客厅的圆桌上摆着两筒饼干和巧克力糖,这是为病人和孩子预备的;治疗床前放着特制的蹬脚凳,供年老病人上下之用。走廊里有两台冷热滤水器,预防孩子烫伤,王大夫特意把热水的开关抬高。诊室里挂满了画家的水彩画和油画,加湿器里的水流潺潺,彩色灯光摇曳。病人进到这里,仿佛进入静凉的休闲宫,病体的压力先减去一半。王大夫说:“这个诊所刚创办,一切都在起步,明天还得去买一台微波炉,希望它将来能成为洛城有名的病友之家!”
王森林现在正是踌躇满志,大展宏图的时候,谁能想到他当初创业时的艰难处境?他是哈尔滨人,在家排行最小,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西医眼科,分配到大庆医院任眼科大夫。20世纪90年代曾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所属的长海医院进修。后来又到北京301医院研修。因为他爱交朋友,对人又真诚,颇受那里的同行的拥戴。他发现眼科这门医学真是太深奥了!越学越感到不足。他的一位好友到英国去进修,他则选择了美国。到洛杉矶后,他考入了加州中西医大学继续深造。在这里,他找到了做学问的门径。以中医的技术而言,难以诊断出眼病的病症所在,必须先依靠西医的技术来诊断出眼部可能发生的疾病,再以中医的辨证方式来获取最佳的治疗结果。学习期间,他研究了可采用中医来治眼科的疾病,包括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炎、脉路膜炎,及因高血压、糖尿病、贫血,及高度近视等等所引起的眼底出血,另外还可运用中医来调养因白内障或青光眼动手术后的眼部保养等。目前已通过了博士学位的考试。
 但学业有成不等于事业有成,况且孤身一人在美国这样的地方,学业也需要事业的支持。他在报上登了一则小广告,毛遂自荐:本人是个医生,会按摩、推拿、照护病人。第二天有人打电话来,说加州理工大学有个年轻人得了精神病需要有人看护。王森林应约来到病人家。他见孩子蓬头垢面,赤身裸体坐在床上,便拿起一把剪刀给孩子剪指甲,孩子问:“你是谁?怎么到我家来的?”王森林说:“我是你家的亲戚!”孩子又问:“我怎么不知道有这样的亲戚?”接着他从白天到晚上总重复这句话,显然不信任他。王森林干脆给他捅破这层窗户纸说:“亲戚有大范围、小范围之分,可以说全中国的人都是你的亲人!”孩子听了,脸色柔和了,开始相信他了。这孩子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因失恋而导致精神失常。发病时,常常被家人恶语相加,把他紧紧捆绑起来。王森林用温和的语言劝导他,解开捆绑他手脚的绳子,替他做按摩。孩子的病,时好时坏,有时会做出一些令王森林不能容忍的恶作剧。在门上设埋伏砸在开门进来的王森林的头上;把煮好的饭菜放在电扇上,突然打开电门,把饭菜吹满房间;有时甚至用削尖的笔刺向王森林的胸膛。对这一切,王森林都默默地忍受下来。后来他们成了好朋友,经常手挽着手去公园散步,到理工学院图书馆读书,一起到球场打球。三个月后,男孩终于康复,恢复正常。王森林又一次面临失业,为了挣足学费,他曾做过修锁匠,到重病人家里日夜守护,不管遇到什么磨难,他总是向着自己的既定目标——完成学业,开办第一家中西医结合的眼科诊所挺进!
但学业有成不等于事业有成,况且孤身一人在美国这样的地方,学业也需要事业的支持。他在报上登了一则小广告,毛遂自荐:本人是个医生,会按摩、推拿、照护病人。第二天有人打电话来,说加州理工大学有个年轻人得了精神病需要有人看护。王森林应约来到病人家。他见孩子蓬头垢面,赤身裸体坐在床上,便拿起一把剪刀给孩子剪指甲,孩子问:“你是谁?怎么到我家来的?”王森林说:“我是你家的亲戚!”孩子又问:“我怎么不知道有这样的亲戚?”接着他从白天到晚上总重复这句话,显然不信任他。王森林干脆给他捅破这层窗户纸说:“亲戚有大范围、小范围之分,可以说全中国的人都是你的亲人!”孩子听了,脸色柔和了,开始相信他了。这孩子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因失恋而导致精神失常。发病时,常常被家人恶语相加,把他紧紧捆绑起来。王森林用温和的语言劝导他,解开捆绑他手脚的绳子,替他做按摩。孩子的病,时好时坏,有时会做出一些令王森林不能容忍的恶作剧。在门上设埋伏砸在开门进来的王森林的头上;把煮好的饭菜放在电扇上,突然打开电门,把饭菜吹满房间;有时甚至用削尖的笔刺向王森林的胸膛。对这一切,王森林都默默地忍受下来。后来他们成了好朋友,经常手挽着手去公园散步,到理工学院图书馆读书,一起到球场打球。三个月后,男孩终于康复,恢复正常。王森林又一次面临失业,为了挣足学费,他曾做过修锁匠,到重病人家里日夜守护,不管遇到什么磨难,他总是向着自己的既定目标——完成学业,开办第一家中西医结合的眼科诊所挺进!
王森林的医德很快被人们传播开来。我在洛城住了不到十天,就遇见两件感人的事。我亲眼看到他为一位视网膜引起眼底出血的病人治疗。这位病人刚来时,左眼因眼底出血,视力几乎等于零。原来找西医治效果不佳,后来右眼也出血,双眼都出现危机,洛城还没有治眼病的中医诊所,就来找王大夫治。王大夫先用自己制的中医药材,把血止住并把瘀血洗掉,再用辨证治疗的方法来提高视力。三个月后,病人的双眼视力已基本恢复,能自己到诊所来看病了。在他的视力未完全恢复前,都是王大夫亲自登门为他做治疗,有时是他自己开车把病人拉到诊所,治疗后再送回家去。
有一天,诊所的事情忙完后,已是夜里十点多钟了。他说:“今天我要去看一个病人,她本来应当今天来看病的,不知为什么没来?”病人住在山上,开车要一个多小时。我决定陪他去。路上王大夫告诉我,这位病人叫戴亚娜,得的是抑郁症。王大夫一边开车,一边自言自语:“她今天没来,是不是在家里犯了病呢?”漆黑的夜,车开到了半山腰,王大夫下车冲着一所房子大喊:“戴亚娜!”我也帮他喊,足足半个小时,没人应声。忽然听见开门的声音,黑夜里站着一个年轻的女性,她就是戴亚娜了!呆呆地站在那里,脸上毫无表情。王森林柔声问:“你今天为什么未到诊所看病?”她说:“我明天去!”王大夫说:“不行,我现在就给你针灸”,戴亚娜说:“明天再针灸!”到了屋里,王大夫连续用温和的语言帮她解除心头的抑郁。原来戴亚娜正在和丈夫闹离婚,这种病症光靠药物治疗是不行的,必须辅以心理治疗,王大夫坐下替她开导了一个多小时,然后约定明天去诊所针灸,这才放心地离去。路上他又给戴亚娜的父亲打了电话,向他通报了情况,督促她女儿按时去看病。回到家里他显然已经精疲力竭,一头倒在长沙发上睡着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所看到的,只是王大夫行医的“冰山一角”。有些药都是王大夫先自己试吃,然后再用于病人;小小银针先在自己身上试扎后,再在病人身上扎。有的病人行动困难,他都自己开车登门施治;有的病人家里有困难,他就挺身而出。一对姓董的老夫妻,本来是老太太患病,尚未治好老头又病了,他就亲自到董家看护。
在洛城小住的一个星期里,王森林百忙中还没忘记带我们吃那里的美食,逛遍那里的名胜。但是这一切抵不过王大夫的医德带给我的心灵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