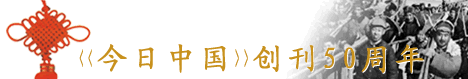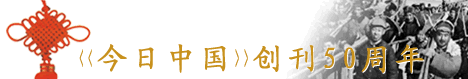“云南丽江地区文化部门日前批准加拿大华人于涌先生在当地建立一家民俗旧器私人博物馆。据悉,这是云南批准建立的首家专门展示纳西族民间生产、生活实用旧器的博物馆。”
──摘自新华社4月6日电讯
于涌:民俗旧器的守护者
本刊记者 张娟
“我这个人‘跨度’很大,出生在台湾,移居加拿大,现在丽江生活;学的化工专业,酷爱美术和雕刻,现在开办了一家私人博物馆。”初一见面,于涌就爽快地自报家门。他风趣地说博物馆的名字太长了──“丽江绿雪斋民俗旧器私人博物馆”,以下我们可以简称“绿雪斋”。
绿雪斋的故事
于涌告诉我,在博物馆成立之前,他在丽江古城开了一家茶馆。茶馆有一个很美丽的名字──绿雪斋,这是他的恩师李霖灿先生书斋的名字。
已经故去的李霖灿先生,曾任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是中国著名的纳西学学者、美术史家和画家,于涌曾拜师他的门下学习中国美术鉴赏。李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美术专业求学时,听人说起丽江玉龙雪山的壮丽雄奇,于1939年第一次拜会玉龙雪山,在日后令他魂牵梦萦的“锦绣谷”云杉坪,他发现玉龙雪山的雪是莹莹的绿色!绿雪奇境给了李霖灿源源不断的灵感,他据此创作了大量以玉龙雪山为题材的作品,并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生活在雪山周围的纳西族,成为中国纳西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丽江人至今仍感念李先生对纳西族的贡献,于涌说李先生后来成为丽江的第一位“荣誉市民”。而李霖灿始终带着浓浓的雪山情结,他自命为“绿雪斋主”。后来,特别请中国著名金石家、篆刻家曾绍杰书额“绿雪斋”,无论在台湾还是晚年去世时的居住地加拿大,这块牌匾都一直挂在老人的书房。1999年,于涌得李先生的首肯,携“绿雪斋”书额到玉龙雪山脚下的丽江古城,创办了以先生书斋之名命名的茶馆。
于涌说当时他的绿雪斋位于丽江古城的入口处,在文化圈中小有名气,他把茶馆的主题定为“茶与艺术”。用来做装饰茶馆的全都是纳西族传统工艺用品,所以人们称它是一个“比古城更为古老的地方”。
“七弯八弯”到现在的样子
说起建立私人博物馆的过程,于涌说自己“七弯八弯”,不知怎么就走到这条路上了。酷爱美术和雕刻的于涌,来丽江原本是为了寻找一个能激发创作灵感的地方,但鬼使神差般,他一到丽江就对生活在这里纳西人和他们古老的民俗文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于涌说他在台湾时就是一名“业余古董爱好者”,他曾“走眼”用高价买来一个共有十三节的竹烟袋,不过这烟袋后来被跟他熟识的三毛一眼看上买了去,于涌还杜撰了烟袋的来历:这是李渔书里提到的“十三太保”!买去以后一定认真爱护……
于涌在丽江看上的“古董”确切地说是民俗旧器,这些东西一定不是文物,但是和文物一样越来越稀少,于涌说越是民间的东西越容易流失,因为没有谁会把一个家用的老木碗作为文物来保护。哪个村子一富,老房子一翻修,老物件就少了。传统的生活用具和生产用具正迅速被现代的东西所取代,人们不经意间就把它们扔掉了,但这些东西在于涌眼中具有独特的价值。他现在收集来的旧器有500余件,包括木雕、石器、竹器、铜器、陶器、皮制品、木刻、建筑用的砖瓦等,这些东西是他两年多来在丽江民间走村串寨收集来的,每收来一批,他就到文物部门主动申报委请监管。于涌说在他的感觉里,每收来一件旧器的同时,收来的还有一个故事,一段历史,每一样东西都承载着丰富的民族文化的内涵,保留它们就是保留历史。
于涌风趣地说自己每天都在触摸历史,弯腰从一个陈旧的木箱中取出一个动物皮毛制作的箭袋,里面装着的箭蔟被认真地包裹着,他告诉我这是100多年前纳西人狩猎的用具,箭头上有草乌,一种毒性很强的东西,不能随便碰;进门的地方摆着的一个衣架是如今许多纳西年轻人都没有见过的纳西民间传统的新娘衣架;于涌小心翼翼地拿来一叠照片和文稿,“这几张是从民间购来的毁于清末的护国寺的壁画照片。这些手稿是我从老乡家厕所的手纸堆里翻找出来的,全是丽江县文化馆的和在瑞老人20世纪60年代初实地踏勘大定寺做的笔记,显然在当时老先生对如何拯救丽江文物已经有了一整套通盘打算,只是到后来赶上一个特殊的年代,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包括大定寺在内的一大批文物古迹夷为平地……”于涌指着缺角泛黄、并有多处洇迹的“丽江县文化馆公用笺纸”上和老先生工工整整的手迹、素描临摹与一串串长长的测量数据甚为感慨:“这是老一辈人的心血啊。”于涌还搬出一个铜罐给我们展示,这是他最得意的收藏之一,这个外表一般的铜罐,里面竟然有一层陶,从工艺上看是先制好外面的铜罐,再烧的陶,于涌说使用陶器和铜器各有利弊,这个罐子把两者的优点都结合起来了。他收集的旧物中,体积最大、价格也最高的一件就是现在“绿雪斋”所在的白马龙潭寺的大门,它原本属于一个大宅院,因宅院做了公房,分配多家人居住,大门便没了用场,于涌将大门连同屋顶的瓦、地上的砖及门前的石板等一古脑搬了来,安放在博物馆门口,他说,这才叫原汁原味。
于涌说,收这些东西并不是简单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纳西人信奉“置货不穷,卖货不富”,有些东西宁肯放在家中烂掉也不卖;有的人也许有些东西想卖又不好意思,这就需要拿捏得很准。
于氏“民俗说”
于涌说他对保留民俗的东西有自己的理解:民俗也要俗得有尺度,要精而不滥。
于涌认为民俗是有其背景的,它必须靠当地的一种文化作为烘托,很多东西离开它的环境,就等于割断它的历史,它也就会失去自己的味道。这些纳西族的旧器物,如果拿到北京去,可能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谈到民俗器物的保护,于涌认为最简单也最直白的一种方式,就是让它创造经济价值。当这个东西值钱的时候,人们就不会把它乱丢掉了。每个人都把它留下来,不就是保护下来了吗?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但如果能作为一个带动者,以自己的行动唤起广大收藏爱好者和社会对保护民间文物、保护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应当是一件很令人欣慰的事情。
要真正保护,一是让百姓知道它的经济价值,二是旧物新用,老的东西如果当盘子不合适,也许当勺子就能派上用场。
好多人把民俗文化保护抬得太高,又有许多人把它贬得太低,于涌认为应该给它一个适中的位置。它不是神话故事,也不是破烂,应该抱着一颗平常心来看待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