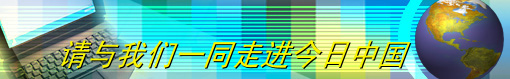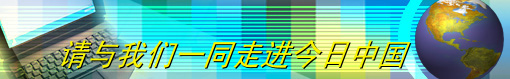“笛侠”伦慧的求学生活
文/范焱
两年前,为了继续学习长笛,伦慧放弃了在台湾朝九晚五的安逸生活,只身来到北京,在中央音乐学院拜师求艺,师从音乐学院的朱同德教授,却还没能正式跨进学校门槛。
“笛侠”是我送给伦慧的“雅号”,因为她将自己比作古代云游四海的侠客,在她的学艺道路上充满了曲折和艰辛。还是让伦慧自己讲一讲她在北京的求学故事。
我带着笛子,云游四海,爸爸说我是天生的流浪命。这没什么不好,可以结交各路朋友,也是别人羡慕我的地方。
我高中念建筑,之后在南投的事务所工作了三年,又在台北工作三年,原本以为我会这样一辈子下去,但途中出现转折,我转到北京来了。
小时候妈妈栽培我们学音乐,我一摸琴就哭,就没学下去。高中时进了学校的乐队,我试了长笛和萨克斯,不知道选哪个。后来一首“泰绮思冥想曲”打动了我,就决定学长笛。其实当时就是兴趣,谈不上什么技术。毕业后,我想这辈子还没做出持之以恒的事来,那就选一样乐器吧。进事务所后第一份薪水就买了一把长笛,又开始交学费到音乐教室找老师继续学习。我坚持参加各种音乐活动,提高自己的素质,后来还考进了南投县的管弦乐团。我觉得学长笛也是一种人生。我因为学了它,打开了我的路、视野,让我的生活变得不平凡,也发掘了我另外的个性。我做建筑时,觉得就这样子,没发现另一个我,学音乐后,你会发现完全不同了。后来我想到台北继续往音乐方面发展,可家里反对,就趁爸爸不在家,跟妈妈告别,开着车就走了。我到台北后半天在建筑师事务所工作,下午到音乐教室当柜台人员,假日到餐厅演奏,非常辛苦。
后来我学习遇到了困难,老师也没办法满足我了,应该另外寻求一条出路。家里人看我决心这么大,就不再反对,提议让我来北京。记得2001年2月过春节时我回家,爸爸对我说去北京吧。我说什么时候去?3月,走!特别干脆。
我很荣幸,也很幸运地从师于著名的长笛教授朱同德老师。1999年我第一趟来北京是观光性质的,当时准备了一首巴赫的曲子,朋友介绍了朱老师。我不知道大师级的教授是什么样,一进门,老师特别热情,一点架子也没有。他知道我紧张,就和我寒暄,放松一下。我把准备的曲子吹了之后,记得老师只说了一句:听得出来对音乐有感觉。其实是我水平低的一种委婉说法。然后他给我提了一些建议,我就回台湾去了。后来老师看我又来了特高兴。
在别人看来我对朱老师有点大不敬,可这是表面现象,在内心我其实很尊敬他,甚至地位超越了我爸爸。不是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嘛。他给我大量的练习曲,很难的,练手眼的反应,一步步提高。当然另一半还要谢谢我自己,耐得住性子,每天练习。
我长进得很快,中间回过台湾,吹了笛子之后,周围的人包括我以前的老师说不一样了,脱胎换骨了。当初我来北京是磨练基本功的,如今总算有成果,也不枉此行。另外,我想试着考音乐学院。
现在我来北京已经两年,生活上大致已经习惯了。你看我讲话口音都变了。在北京我会倒公车,坐地铁,不会迷路,有时还帮人指路。有了一箩筐的新朋友,这是我快乐的地方。除了台湾学生外,我跟班上同学都很要好,她们也会来我家过夜、做饭。我还上健身房调适自己,把自己养得挺好,总算没给家里添麻烦。
学了长笛,我的感情丰富、敏锐了,对生活变得多愁善感,很能体会,有感触。这才烦恼。这样也没什么不好,这叫人生。有哲学的态度,困难的时候,艰苦的时候,我可以笑心相对,快乐的时候我把它看成是上天掉下来的礼物。很能调适自己的心情。
我知道有好多困难,可半路出家又怎么样?有志者事竟成嘛。我的人生态度是这样的:不论做得如何,只求尽心尽力。一直到合眼的那一刻,扪心自问,我这辈子有什么没做的、遗憾的?如果没有就不虚此生。
当然,我的生活少不了音乐和幻想。我说它是我的一号男朋友,我男朋友只能屈居第二,他总抱怨可不可以加分做一号。
今年我祈望修成正果。
这就是伦慧的故事。今后的人生之旅还很长,不知道“笛侠”今后会云游到哪里。但我想音乐与长笛会始终伴随着她,而伦慧也将继续在艰苦的求艺道路上努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