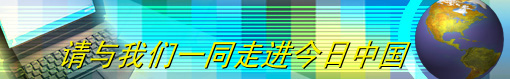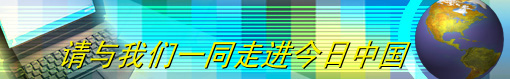瞬间即是永恒
张薇
 |
| "让中国精神高高飘扬--放风筝抗非典"活动在北京举行,参与者群情激昂。 |
4月开始,作为一名生活在疫区的职业记者,我没心没肺地到处奔波。北京市疾病控制中心、SARS实验室、地坛医院、皂君庙东里隔离区、北方交通大学隔离区……这些人们惟恐避之不及的重灾区,都曾留下我来来去去的身影。
无休止的采访,无休止的敲字,无休止的发稿,无休止的绞尽脑汁策划,无休止的一日三餐吃盒饭,无休止的凌晨两点就寝、无休止的找不出时间打理自己,无休止的没有闲暇回顾过去。
两个月后的今天,SARS已不再肆虐,生活慢慢恢复正常。一切正在回归到没SARS的从前。
此刻,当我静静地坐在电脑旁,端着一杯醇香的咖啡,享受着久违的轻音乐时,许许多多的瞬间和细节便出现在眼前……
跟随着工作人员,我忐忑不安地走向三层的SARS实验室
4月16日,在对疫情做了一系列动态报道后,我所在的《北京娱乐信报》正式成立了非典报道组,执行总编孙瑜亲自带领10多个记者兵分数路冲向非典一线。我被派往北京市疾病控制中心的SARS实验室。
那天早上,天很蓝,草很绿。大街上戴口罩的人还很少。SARS的严重性,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手中拎着自己的第一个“SARS口罩”和几位同事如约来到北京市疾病控制中心。刚进中心大门,一块“向SARS宣战”的大牌子赫然呈现在面前,几个穿白大褂的门卫警惕地拦住我们要求登记。此时,我不由自主地戴上了口罩,使劲将绳子紧紧地系在耳朵上。
我的任务是采访疾病控制中心最危险的地方SARS实验室。奇怪的是实验室并不在疾控中心大院,而在离中心数百米开外的一处院落的一座楼的三层。据说,楼房的第一层是艾滋病实验室。我小心翼翼地尾随着工作人员,忐忑不安地走向三层的SARS实验室。在走到楼道中间时,我们开始紧张地穿戴预备好的防护服、帽子以及防护鞋套。走进走廊尽头的一间屋子时,工作人员又要求我们戴上防护眼罩。
慢慢进入实验室,首先看到的是一面巨大的玻璃墙,墙外放着各种卫生用品和药物,是安全区也是监视室;而墙内是隔离间,安放着实验室的核心部件。
当天,我在实验室看到林长缨博士和一位女医生模拟做一组SARS病毒的血清实验。林博士先穿上了一层连体的银白色厚型“猴衣”,又穿了一套蓝色隔离服,接着又戴上了两层口罩、防护眼罩以及橡胶手套……最后才达到防护级别。看着我紧张的样子,林博士笑着说:“不能让一丝皮肤露出来。”
第二天,我的稿件以大通版的形式见报,引起了读者的广泛注意。我母亲看到后,特意打来电话,当听见我还在不停地敲键盘时,她简单地问候了几句话就挂断了。事后,父亲告诉我,我母亲那几个晚上一直睡不着。
今天,我反问着自己:“如果当时真的会遇到危险,会不会后悔进去?”
可视电话带来的感动
 |
| 彭梦楚通过可视电话给战斗在非典一线的妈妈献上了一束康乃馨。 |
4月20日,曾有过一面之缘的北大科技园博雅投资公司副总宋党生来电,说有一种新型的高科技产品“捷视宝”可视电话,想寻求合作。瞬间,我想到了隔离区,想到了里边的医护人员,想到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却长期不能和家人见面的困境。随之一个大胆的想法涌上心头:“把可视电话安进隔离区,让白衣天使们能和家人安全地见面说话!”
经过努力,4月24日,18部可视电话像眼睛一样安设到了北京市各大非典定点医院。
4月25日16时,通过可视电话,年近六旬的本报社长崔恩卿与身处防治非典隔离区的北京地坛医院二病区贾双萍护士长进行了隔离区内外的“面对面”对话。
崔社长问贾护士长现在最想念的人是谁?她说,是自己的老父亲。贾护士长的父亲身体一直特别不好,在她进入隔离区之前,父亲就在北京医院急诊看病,父女已经有好多天没有见面了。贾护士长告诉崔社长,她与其他家人沟通的惟一途径也就是打电话,但是白天太忙,没有时间,只能在晚上夜深人静时和家人互相问候一声。此时,崔社长的眼泪落了下来。
在通话的短短几分钟内,在媒体业界征战一生的崔社长竟然几次落泪。当时我的心情是感动的,也是甜蜜的。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策划的“可视电话联线”报道,在这个非常时期,是多么地深入人心。
在抗击非典的战役中,有一支鲜为人知的队伍,赴120急救中心支援的的50名巴士司机。
4月,北京120急救中心用于接转非典病人的救护车司机出现了严重不足。接到请求援助50名司机的信息后,北京巴士公司紧急召开了动员大会。在短短的半个小时之内,巴士公司就有260名司机志愿报名。经过认真的挑选,50名优秀司机外加8名后备司机于4月26日开始了培训,28日,他们告别家人在120急救中心正式上岗。
5月2日,我需要通过可视电话采访一位巴士司机及其家属。选择采访对象时,和巴士公司120急救中心临时党支部书记张兴华商量了很久。张书记极力推荐一位叫杜春强的司机。他说,杜春强是公司的外聘职工,开始定的名单没有他,但是他强烈要求了多次,并强调自己是一名退伍兵,又是党员,应该到救援一线去。公司领导再三考虑,最后才满足了他的请求。
下午,我来到杜春强家。他的妻子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有见到丈夫了。她说,丈夫使的是“先斩后奏”,申请上一线的事,事先没有和家人打招呼。到了26日,公司开始培训后,他才告诉了家里。
5时左右,可视电话终于接通了,杜妈妈立即体贴地将电话递给孙凤芝,杜爸爸则紧紧盯着可视屏幕看着儿子。
“老公,你还好吧?”孙凤芝一句温柔的问候,让屏幕里的杜春强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全副武装”的杜春强看着妻子,隔着厚厚的口罩依然掩饰不了他的阳光般的笑容……
孙凤芝拿出了一张早就准备好的纸条。原来,她把准备与丈夫说的话早就写在了一张纸上。这张纸就放在电话的旁边。她羞涩地说,只怕纵有千言万语,见到丈夫后会表达不出来。在那张纸上,孙凤芝写着:你要好好工作,服从领导,服从分配。你要好好地保护自己,做好一切防护工作,珍爱健康,不要惦记家里,我们都很好,我们等你胜利完成任务安全回来。我们的儿子也很好……她对丈夫的爱和惦念已全部融入朴素的语言里。
杜春强61岁的妈妈,也和儿子一样在为抗非典忙碌着。杜妈妈在居委会工作已有11年了,非典肆虐京城后,年事已高的杜妈妈和居委会的4名同事一遍一遍地为小区消毒,指导居民预防非典。在通话中,杜妈妈反复叮嘱儿子执行任务要多加小心。
“爸,妈,我们来任务了,马上就要出发!”通话还没有几分钟,杜春强就放下了电话,屏幕上出现了短暂的模糊,电话里传来众人说话的声音。原来又有新的病人被发现,需要他们立即赶到现场,杜春强就这样还未来得及和家人多说几句话,就又上路了。
3岁的小朋友指着电视里每一个小汤山的军医叫爸爸
5月30日,六一儿童节前夕,我主持策划了《今年六一“不收礼”
三地儿童在信报庆六一》的四地联线报道。
整个活动的运作从5月28日下午开始。我们决定找小汤山医护人员远在家乡的孩子,让这些孩子通过可视电话给好久不见的父母送礼物,表演节目。主题确定后,当晚,我就开始联系小汤山。从护理部的赵主任、政治部的卫主任,打电话的次数数不清,可是由于他们工作太繁忙,电话总是说一半就不得不挂断。
第二天上午,小汤山医院护理部的赵主任在百忙之中终于给我找到了几个地方医护人员以及家属的名单。我的一位同事王佳开始了另一项烦琐的工作。重庆、乌鲁木齐、昆明、武汉……打了无数遍长途电话后,当晚终于确定了几家外地协办的媒体,然后通过他们又确定了另外的几位参加活动的孩子。
其间,我突然又萌生了一个念头,请少儿节目主持人董浩来现场主持!来不及兴奋,我迅速和中央电视台青少频道的朋友联系,得到了董浩的手机号码。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拨通董浩的电话,和蔼的董浩听了活动的介绍后,欣然答应来信报主会场主持节目。随后,我们还与新浪网取得联系,决定活动当日进行网上直播。
5月30日14时,活动如期举行。董浩带着夫人如约而至,新浪新闻中心负责人亲自带队在现场进行直播。整个活动有近20个孩子和小汤山医院的爸爸妈妈“面对面”交流,北京、重庆、乌鲁木齐三地的孩子们通过可视系统不断地喊爸爸妈妈,有的孩子给父母表演了幼稚的节目,有的孩子给父母画出一幅美丽的画。一位3岁的小朋友在妈妈的怀抱中,指着电视里每一个小汤山的军医叫爸爸,而他真正的爸爸却还在小汤山联线现场之外的地方为人民奉献着自己。
活动结束后,董浩深有感触地说,“这是我主持20多年节目以来,最特殊、最让我感动、也最值得铭记的一个儿童节了!”他说,“在主持的过程中,就仿佛感觉自己真的在和这些医护人员零距离接触,真的感觉到这些亲人们相见时脉搏的跳动。有好几次都想落泪,可是还要主持节目,只能忍回去。”
而今,铭记我心间的,除了活动现场的感动,就是非典期间人和人心灵的贴近。这是在灾难之外,SARS赐予我们的另一种幸福。
谢飞第一次看清精心照料自己25天的医护人员的脸庞
 |
| 著名导演谢飞病愈出院。 |
非典以来,住进地坛医院的导演谢飞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5月初,病情逐渐好转的他,通过可视电话接受了信报的独家采访。
当天和谢飞的对话不到10分钟,但是和谢导的主治大夫蒋荣猛谈了很久。蒋大夫身穿隔离服,在可视电话的屏幕上我只看到一个大口罩和一双眼睛。电话里的蒋大夫听起来很年轻也随和。他告诉记者,刚来医院时,谢飞的病情确实很严重,发烧、胸闷、呼吸困难、肺部阴影等症状非常令人担忧。在多种手段治疗下,已经有很大的好转,按照现在的情况,10天左右谢飞就可以出院了。
5月16日,谢飞果然病愈出院。
当日下午,地坛医院热闹非凡。在众多媒体闪光灯的簇拥下,只戴口罩的谢飞,身穿一身休闲西服,怀抱鲜花,精神抖擞地走出了病区。他的身后就是4月22日接他入院的蒋荣猛大夫。蒋大夫和上次在可视电话里的形象大不一样,脱掉了防护服、摘掉了口罩和帽子。他说,听到出院的消息,谢飞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认清所有照顾过自己的医护人员,为了满足他的要求,病区的李主任、两位护士长还有好几位小护士都脱掉防护服跑出病区,来参加欢送仪式。
“这是李主任啊,你……就是蒋大夫!”走出隔离区的医护人员围着谢飞,他激动地看这眼前的一张张曾经被隔离服包裹的严严实实的脸庞,仔细地分辨一位位救命恩人。当走到挽救自己于生命边缘的蒋荣猛大夫面前,一向含蓄的谢导热泪盈眶地握住他的手,激动地说:“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蒋大夫欣慰地笑着,频频亮起的闪光灯照耀着他眼角的一滴泪花。
在人群的背后,我找到了谢飞的爱人崔老师。曾为丈夫的安危操心不已的她悄悄地躲在汽车边上,脸上挂着掩饰不住的喜悦。她衷心地说道:谢飞能康复出院,全仰仗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社会各界的关怀!
看着镜子中的长发,陈鲁妮闭着眼睛举起剪刀
非典期间,最让我感动的一位女性是陈鲁妮。
陈鲁妮是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医院胸科中心生物医学实验室主任、中国空军总医院呼吸科客座教授,数年来一直在瑞典从事急性呼吸道窘迫综合症的治疗和研究。疫情严重时,她告别了丈夫和两个女儿,带着价值200余万元人民币的医疗设备及药剂,回到了祖国。
5月15日开始,经过多次电话预约,直到17日下午,我才在空军总医院一栋空荡荡的大楼里见到了繁忙的陈鲁妮。
那是空军总医院刚刚改建完成的一栋住院大楼,尚未正式投入使用。简陋的“研究室”里,四张桌子拼成一张工作台,空军总医院副院长高和、呼吸科主任张波以及朝阳医院院长王辰的两位研究生正在忙个不停。工作台旁摆着一台无创呼吸机和另一台插着许多管子,看上去挺像立式饮水机的古怪仪器。长发飘扬,笑容腼腆的陈鲁妮说,这就是自己飘洋过海带回来的“宝贝”一氧化氮治疗仪。一氧化氮治疗仪最大的特点在于,能把一种一氧化氮的气体药剂通过呼吸机传输给呼吸衰竭患者,展开治疗。其治疗原理是一氧化氮能改善病人缺氧的状态,能减轻病人的肺部炎症反应和渗出。
陈鲁妮带来的一氧化氮治疗仪由芬兰科学家研制,一氧化氮气体药剂则由瑞典科学家研制,都是专利产品,目前我国还没有引进。这次她回国的主要目的就是把两台一氧化氮治疗仪和40瓶一氧化氮气体药剂送到SARS临床一线。一瓶药剂可以连续使用30个小时以上,40瓶能救助许多病人。
从5月中旬开始,陈鲁妮就投入到仪器的调试和实验中。5月底,陈鲁妮把已经调试好的机器送进了宣武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的非典隔离病房。
6月初,再次拨通她的手机,她说自己差不多是已经“住”进SARS病房了。听到这句话,我不禁想起在上次的采访过程中,那个一直小心翼翼戴着口罩的女性。记得她悄悄告诉我,作为一个母亲,最害怕的就是把任何可能的危险带给孩子。所以她每天工作时都戴口罩和隔离帽,吃饭时也经常躲开人群,一个人吃。
但是,在夏日炎炎的6月,这个胆小的母亲却作为技术指导人员勇敢地走进了隔离区。
她在电话中告诉我,为了避免病毒感染,她已经剪掉了一头长发。挂断电话,我仿佛看见,一面巨大的镜子面前,端坐着的陈鲁妮看着镜子中的长发,闭着眼睛缓缓举起了剪刀……
瞬间即是永恒,细节就是全部。记录瞬间和细节就是见证历史。
在今天,在此刻,回想自己所经历的人和事,回想SARS期间,自己始终穿梭在偌大的城市里,做出了一系列无愧于职业记者的选择时,我甚至幸福地想落泪。虽然,谁也不曾知道我是心怀恐惧走进隔离区的隔离线内,谁也不曾知道在最危险的时刻男友甚至“威胁”说要把我绑架在家中,不让我出去。但是,我走过来了,阴霾渐去,暖暖的阳光终于照耀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