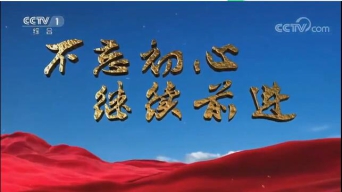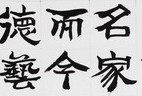用文学搭建中拉沟通的桥梁——中国作家阿来的拉美之行
“我并不是像一般的游客一样去所有人都要去的地方,尤其是去国外”,阿来说。他的原则是,他要去的国家一定是通过文学的描述对那个国家历史、现实有过印象,而且恰巧那个国家的一些作家曾经在他的文学之路上发生过一些影响。阿来的拉丁美洲之行就是出于这样的召唤。
“聂鲁达召唤我来到拉丁美洲”
2016年,阿来接到孔子学院拉丁美洲中心执行主任孙新堂的邀请电话,首先感到智利是非常遥远的国家,但是他同时想到,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对年轻时的他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当天晚上,阿来从书柜最上层的地方把聂鲁达的诗作《漫歌集》(过去译为《诗歌总集》)找出来。这本诗集购于1984年,距离上一次阅读它已经过去多年。
阿来出生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2000年,41岁的阿来凭借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在购买聂鲁达诗集的那个年代,年轻的阿来当时主要从事诗歌写作,后来才慢慢转向到了小说写作。
阿来已经二十多年没有读过聂鲁达的作品,对于诗歌也有点疏远。“但是重新阅读《漫歌集》,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的那种感觉还在,年轻的时候想走向广阔的世界、向聂鲁达学习、把诗歌写得无限宽广的那种野心还在,所以就觉得我一定要来智利。”
6月14日,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在孔子学院拉丁美洲中心的报告厅,阿来向在座的青年学生和文学爱好者再次回忆了那个重读聂鲁达的夜晚,以及聂鲁达对于当时的中国年轻作家和中国文学的深远影响。阿来说,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文学既要坚持传统精神,又要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的文学经验。那时候虽然形式上的殖民主义(在中国)已经永远结束了,但是西方的文化霸权、文化殖民主义还远没有停止。在中国文学刚刚走上新的道路的时候,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经验,例如怎么表达自己的历史、怎么表达自己的价值观、怎么创造自己的美学风格,对中国作家来讲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阿来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思想背景和文化需要上,阅读了一批第三世界的文学作品,包括拉丁美洲的文学,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聂鲁达。
“尤其是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遭到当时智利政府通缉时,聂鲁达在流亡时期写下的那本《漫歌集》,在我的年轻时代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中国到智利的路上,在三十多个小时的飞行当中,阿来几乎又把这本书全部读了一遍。
“从社会认知价值上讲,它包含了一些反抗西方霸权的意识”,阿来说,聂鲁达用诗歌的方式描述了西班牙人征服这块大陆的残酷历史,以及殖民统治之后人民的觉醒和所创造的辉煌。重要的不是所述内容,而是聂鲁达用宽广、自由的方式,把过去诗歌很难包容的那些内容、很难处理的题材,用看起来容易的方式包含在了他的诗歌当中,并且运用了过去诗歌中没有出现过的修辞。“对于现实的揭示、表达、艺术性在聂鲁达身上都特别奇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我觉得在诗歌史上在这一方面和他达到同一高度的,只有美国人惠特曼。”
阿来解释,中国传统的诗歌形式与当今社会的宽广和复杂不适应,虽然中国在新文化运动以后也开始一些自由诗歌的写作实验,但是历史依然很短。究竟什么样的方式才是真正中国的自由诗歌的方式,而且能够全面、宽广地表达现代社会?像聂鲁达这样的诗人,就提供了过去中国诗歌传统当中所不包含的经验。
“我就是略萨笔下的阿尔贝托”
结束了智利的紧张行程,阿来来到印加文化的发源地——秘鲁,在天主教大学孔子学院、里卡多帕尔马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了主题为“我就是略萨笔下的阿尔贝托”的文学讲座,与秘鲁大学生和文学爱好者一起分享了自己对秘鲁著名作家、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作品的认识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阿来的讲述深刻生动、妙语连珠,过程中不时传出笑声和掌声。
《城市与狗》是略萨最为轰动的长篇小说,是其1962年根据自己少年时在军校学习的亲身经历创作而成。 阿来在二十多岁的时候读了略萨的三四部长篇小说,当时他在一所中学里教书,刚刚从事文学创作不久。《城市与狗》所描述的年轻学生的反叛行为,给他的印象非常深刻。“主人公阿尔贝托一边和他的同学们参与所有那些反抗学校规定的活动,但是好像一直有一个另外的阿尔贝托在冷静地记录这些事情,我在年轻的时候、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就想,可能写作带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种能力。”
“阿尔贝托跟那些军校学生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他在反抗、叛逆当中不断地学习,但是跟所有人不一样的是:他喜欢上了写作。”阿来认为,所谓作家、诗人就是略萨笔下的“阿尔贝托”,他们并不是大众当中的另外一种人,他们本身就是大众的成员之一;大众所有的经历,所有的快乐、痛苦、希望,他们都一样具有;他们又能在经历这些同时,灵魂超脱于此,像上帝一样审判自己。他们有了这种审判能力的时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要放弃现世的生活。
《城市与狗》也是略萨的自传体小说,很多自传性的小说作品会拘泥于现实或作家的经历,即“审判自己”的力量很弱。“我觉得略萨有一种批判的能力,他批判社会,但是首先把批判的矛头首先对准了自己。”阿来说,作家从对自己的审视和批判,再到对社会的解剖和揭露,便体现了一个作家对社会承担的责任。
“文学是有最大公约数的沟通工具”
“我从太平洋彼岸来到南美,在智利讲聂鲁达,在秘鲁讲略萨,是想让当地民众知道中国作家十分关注拉美文学作品。尽管中国和拉美距离遥远,但文学交流能拉近人民之间的距离,希望今后双方能译出更好的作品”,阿来同时希望更多的拉美人来孔子学院学习汉语,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文学和文化。
在阿来眼中,文学在世界人民之中是一个有最大公约数的沟通工具:“世界上有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他们的制度是如此的不同,有如此多的表面的差异,但是在我看来、在文学的眼光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远远小于他们的共同性。”
在来到拉美之前,阿来以及他的作品已经被世界各国的读者所熟知。其代表作《尘埃落定》的中文版销售超过两百万册,英文版在2003年被美国买走版权的时候,创下了15万美元的版权交易记录。《尘埃落定》在2003年就有了西班牙语译本,书名为“Las amapolas del emperador”,不过早已售罄,孔子学院拉美中心的孙新堂主任费尽周折,才在阿来到智利之前拿到了两册旧书。在孙新堂的协调下,阿来的更多作品西文译本也在翻译当中:他的短篇《月光下的银匠》计划收录到《人民文学》的外文杂志《路灯》的西班牙文版中;其长篇小说《蘑菇圈》已经交由墨西哥汉学家莉亚娜(Liljana Arsovska)翻译,计划明年5月由中国的五洲出版社、智利的罗姆出版社(LOM)在北京和圣地亚哥同时出版。
作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阿来的特殊身份也引起了拉美文学爱好者的好奇。阿来指出,人们在对于陌生文化的认知过程是一个不断纠错的过程。西方人最初认为西藏人都长得像一个巨大的蚂蚁,每日忙于挖金,至今外界还对西藏存在很多误解;同样的错误也发生在外界对拉美的认识。这些事实都告诉人们,由于历史和认知的局限,很多自认为先进的文化习惯对其他文化妖魔化、扭曲化,最终导致了不同文化的相互隔阂。
阿来还回应了关于传统文化发展的观点。他说,传统文化不是也不应是一成不变的,当整个世界迅速变化时,我们也应该鼓励传统文化顺势发展。这样才是活的、有生命力的文化。他风趣地举例说:“当所有人都住在高楼里,我们不能要求印加人的后代还继续住在马丘比丘的遗址上”。
作家阿来此行在两个国家4所孔子学院举办了5场讲座,接受了7家电视台、电台、报纸媒体的采访,所到之处受到当地文艺界的热烈欢迎。孔子学院拉美中心“中国作家讲坛项目”今年还将邀请刘震云、西川、麦家、周瑟瑟、鲁若迪基等著名作家赴拉美和加勒比孔子学院举办各类文学活动,提升孔子学院的文化品牌,积极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