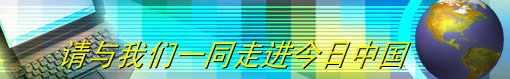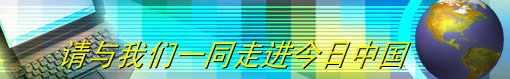美术人语
——我看中国美术馆
编者按:新中国成立10周年首都十大建筑之一的中国美术馆,经过装修扩建后于2003年7月23日重新开馆。美术界人士对此有何评价呢?这里邀请了三位美术人,请他们谈谈各自的看法。
2003年,中国美术馆事业的分水岭
水天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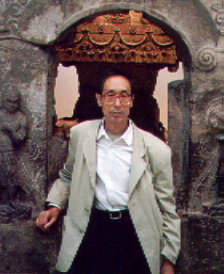 |
| 水天中:研究员,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美术系主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研究所所长。《中国美术报》和《美术史论》主编,《中国油画》常务编委,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油画学会理事,《油画家》副主编,现专门从事中国现代绘画史和美术批评研究。1993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
中国美术馆经大规模装修后重新开馆,有了藏品的长期陈列,可以说这是国内美术馆建设的历史性转变。2003年是我们的美术馆事业的分水岭。现在,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大体遵循历史发展脉络的20世纪中国美术作品的常年陈列。
在策划此次“开放的时代”邀请展的过程中,我们对展览方式的改变进行了尝试。首先,打破按画种分类评选、陈列的惯例,将展品分为几个艺术类型(文化主题),更加关注艺术的文化倾向和精神价值。其次,不同类型的新媒体艺术正式进入国家美术馆的大展,这显示了对待当代艺术的开放心态。最后,打破了“一人一件”的以平均主义尺度对待艺术的陋规。
策展人制对于中国的展览活动并不是现在才有,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国内一些大型展览(包括去国外的巡回展览)就已经由策展人主持,傅雷、刘海粟、徐悲鸿都曾以策展人的身份主办过重要的展览。只是到五十年代以后,事事强调集体出面,策展人才退出了中国美术展览的舞台。在不久的将来,希望国内能出现适应不同艺术方面、掌握不同艺术状态的策展人。但它不会从根本上提升全国美术创作的水平,因为不同的策展方式只能改变对现有创作的观察、选择角度,而不可能改变美术家的修养和技巧。
今后,美术爱好者们有了更多的现场观摩艺术大师原作的机会,这对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艺术素质,提倡人们的美育观念,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迈向世界一流,任重道远
尹吉男
 |
| 尹吉男:教授,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主任,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硕士研究生导师,被誉为“敏感而又冷静的艺评家”。1996年任《读书》杂志专栏作家、《美术星空》栏目总策划、《东方》杂志专栏主持人,曾策划了《20世纪中国女性史》《发现曾侯乙墓》《点击黄河》等多部系列文化电视片,著有《独自叩门——近观中国当代主流艺术》《后娘主义——近观中国当代文化和美术》等专著。
|
其实,中国美术馆要想真正成为世界一流美术馆,单在收藏艺术精品方面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曾经近百年的战乱已经使我们错失了收藏我们自己和国外美术品的时机。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初,作品收藏大部分是靠画家、美术家的觉悟,像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当初被美术馆收藏的价格仅为400多元。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前,花20元、100元甚至免费就能收藏到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师的作品,现在花一百倍、一千倍的钱都买不到。美术馆的基础是收藏作品,有了藏品,才能办陈列,进行研究。如果不加紧收藏,我们当代的优秀作品就会流向海外,国家美术馆为子孙后代积累文化财富的功能将因此而丧失。如果我们收藏基金的申请工作再做得更好一些,我们的艺术家把眼光再放得更远一些,这样留给后人的遗憾也就会少一些。
《百年美术——中国美术馆藏精品陈列》属于回顾性展览,它的前提和基础是艺术史的鉴别与梳理,但它的学理性分析和主题特色还有待提高。对于美术史研究来讲,展品的摆放是非常有讲究的。百年美术史,为什么选择了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在这个位置出现,像这种历史背景的交代和解说是不可以一笔带过的。
从目前发展趋势看,策展人机制将会被更多的展览活动所接受,但我觉得策划人带来的危机也是相当可怕的。策划人的产生应该是民主程序的补充与延续,可艺术其实常常想超越民主的程序。那么究竟如何来确定艺术品的价值,就成为策划人的难题。我们在做当代艺术策划的时候,为了尽可能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背景、不同信仰下的东西都呈现在一个地方,只有构造一个巨大的文化超市。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也塑造了一种生活模式,包括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和国家的关系,和民族文化的关系,观众被培养出了一种趣味,比如开车去买东西是一种品位。而它们一旦被品位化、美学化以后,一些体现真正个人的艺术就很难找到了。
美术馆,我的良师益友
翟欣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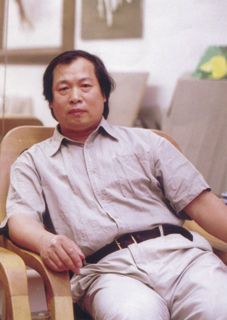 |
| 翟欣建:现在中央美术学院附属中学任教,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美术家协会理事。曾组织编写《中央美术学院附属中学素描基础教程》。《心灵的歌》、《女工》、《女人体》、《舞者》、《黑色与白色的梦》等多幅油画作品屡次在国内外艺术展中展出。 |
说来也是缘分,现在中国美术馆的馆址,正好是我老姨家40年前的住址,就是双捻胡同一号。记得小时候常到老姨家去玩,那是一所北京典型的三进门式四合院。后来,国家要建美术馆,这一带居民也都拆迁走了,老姨家也搬到了汪芝麻胡同。1962年,中国美术馆的落成填补了中国没有国家美术馆的空白,这对北京乃至全国,都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在学生时期,我参加过学校在美术馆举办的活动,也目睹了“文化大革命”在这里举办的“黑画展”。后来,我到附中工作以后,离它更近了,美术馆每天都能映在我的眼帘里,不管春夏秋冬,还是晨雾晚霞,都在我心底留下了美好回忆。美术馆伴着我走过了前半生,它是我的朋友,是我的老师,也是我心中的一块净土圣地。
前不久我去了重新装修的美术馆,这次我的确也享受了一次国家级美术馆的待遇,无论从墙面的颜色还是地面材质的选用上都使人感到色调高雅、舒展流畅,考究的休息座椅就好像是展厅里的艺术作品。我觉得中国美术馆完全可以立足于世界一些著名的美术馆之列,具有强烈的东方艺术精神,但如果真想成为世界一流的美术博物馆,还需要扩大空间和面积,增加艺术种类和艺术含量,提高更优质的服务。
可以这么说,我是在美术馆的熏陶与培养下逐渐成长起来的,希望以后到这里参观的人们络绎不绝,这里的展品陈设更加恢弘大气,弘扬光大民族精神,美术馆永远都是我的良师益友。
(本刊记者张渊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