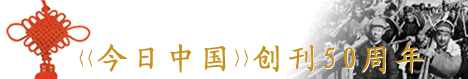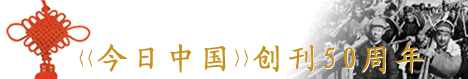寻访哈萨克人的夏季牧场
张力

盛装的哈萨克姑娘 |
寻访哈萨克人的家园往往需要经过一番长途跋涉。当我从北京飞到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再沿天山北麓亚欧大陆桥到达西边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首府博乐的时候,人们不断告诉我,或者说是在催促我:去吧,到赛里木去!你不会失望的,因为游牧的哈萨克人正在前往他们在那里的丰美的夏季牧场。
路经艾比湖
地图上的艾比湖标得清清楚楚,可是在我手中的《新疆旅游指南》上却没有找到它,它怎么会被遗忘?在火车上,我看到了辽阔的艾比湖,由于光照很强,远处的艾比湖就像一面银白的镜子;因为被荒漠紧紧包围得太久了,看不到一点人的踪影。我长时间地守在车厢结合部的窗前,静默无言的艾比湖让我心动,以至想扛起沉重的行囊马上下车。
旁边的一位长者也在凝望着它,眼中饱含着更多的深情,像是自言自语:“上世纪70年代湖水还漫到现在铁路的地方,后来渐渐没水了,艾比湖几乎只留在了地图上。我60年代支边到这里,一直就看着它。今年非常可喜,几场雨后,艾比湖又恢复得相当大了!”
此行,我更希望找寻人与自然的结合点,找寻游牧民族停留的地方,所以没有走近艾比湖,而是选择了它的姊妹湖——赛里木。

参加一年一度的阿肯弹唱会 |
遇到布来提
像曾经看到过的西藏纳木措湖一样,在白云和雪山的映衬下,赛里木湖碧蓝得令人难以置信;从公路上一步步接近它,直到它完全展现在眼前,这时你又会发现它清澈见底。越向远离公路的深处走,离哈萨克人的牧场就越近,风光也越迷人。
哈萨克人的毡房和木屋沿湖边排开,我投宿到一顶小号的毡房内,里面铺着红地毯,还有几床很厚的干净被褥。外面已经有人在问:“喂,朋友,要不要骑马?”我钻出毡房,见一个黝黑的青年牵着一匹枣红色的骏马,这应当就是久闻其名的伊犁马吧。在这样的湖光山色中,在真正的草原牧场上,恐怕没有人能抵挡骑马的诱惑。
牵马的哈萨克青年自我介绍,他叫“布来提”,是勇敢的意思。他在畜牧学校学了三年兽医,但没找到对口的工作,于是就把家里牧羊的马牵出来“搞旅游”。布来提显得挺有经验,看得出我对什么感兴趣,他带我向山坡上挺拔的松柏林走去。今年的雨水格外好,绿草甸子上遍山黄色的金银花怒放,还间杂着蓝紫色的小花。马儿并不急于载我前行,总是低头啃食嫩草。
上陡坡时,我要求下来,好让这匹三岁的马别太吃力。布来提对此很高兴,马也趁机饱饮了一番山泉。看着他抚弄马鬃的样子,我问道:哈萨克人是不是与马有很深的感情?他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举了一个例子:哈萨克男人喝醉后,只要爬到马背上,抱住马脖子,马就会把他驮回自己的毡房。我注意到,这一路他虽然挥动马鞭,但从未真的打在马身上。不过布来提说,明年他就不想再牵马了,而想开辆出租车。这让我感觉有些意外。

走向塞里木湖畔的夏季牧场。 |
赛里木湖畔
来到后山,可以看到哈萨克人在搭建各自的毡房,他们不但使用骆驼、马匹,有的还开来了卡车;羊群在草坡上安逸地吃草,牧羊犬静卧在草丛中。整个宜人的夏季,他们都可以安顿在这一带,让他们的羊群足足地长膘,同时兼顾旅游业。哈萨克人每年游牧的路程大约有七八百公里,通常羊群在头年的11月交配,来年的4月产崽,而6至8月就要在夏季牧场增膘。
按照哈萨克人的习俗,我远远地下马向一户人家走过去,男主人在搭建毡房的骨架,女主人则在搬运堆放在路边的家什,她正背着一扇蓝色的毡房门板。他家的儿子正在和邻家的孩子玩耍,虽然几个小孩子非常可爱,但布来提却告诫我不能夸他们,因为哈萨克人忌讳生人夸奖他们的孩子,认为那样会带来厄运。
一位毕业于民族大学的哈萨克女导游古丽努尔告诉我,新疆现在大约有120万哈萨克族人,目前,大部分哈萨克人仍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也有小部分因医疗和子女上学等原因,选择了半游牧或定居的生活。古丽努尔特别强调,哈萨克人十分热情好客,来者不拒;他们中间很少发生偷盗、抢劫,也没有乞丐,即使孤儿也有人照管,因为无论谁家有难处,不用求人,大家都会鼎力相助;哪怕自己只有一袋面,也会分出大半袋给别人。
祖国幅员广大,哈萨克人居住的地方地处西部边陲,当我骑在白马上望着天边最后一抹晚霞的时候,已经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了。哈萨克小伙子拍马送我回毡房,白马奋蹄奔跑起来,我们两个在一匹马上紧夹马肚,身体离鞍,我脖子上的相机几乎被颠下来。很快跑到小毡房前,我跳下马,小伙子忽然一拉缰绳,让白马表演了一个完全靠后腿直立的高难动作,他用握着马鞭的右手行个举手礼,白马嘶鸣一声,扬蹄而去。

"阿肯"(哈萨克民间艺术家)正在弹唱。 |
北疆夏牧场
我在北疆继续追寻游牧的哈萨克人的足迹,在通往阿勒泰的路上,不时会看到山坡上垒放的石头。一问才知道,这是牧民的“指向石”:摆一块,表示附近有路;摆两块,表示有水;摆三块,表示有人家。
转过几个急弯,一下子看到了开阔的阿合贡盖夏季牧场。只见彩旗飘舞,聚集了很多牧民、羊群和马匹,也有一些人是开车或骑摩托车赶来的。他们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盛大的哈萨克族阿肯弹唱大会。那里排列着十几座大毡房,毡房后的涓涓细流边上支着一排大锅,热腾腾地煮着刚宰杀的羊肉,美餐一顿是节日必有的内容。
哈萨克族的男女老少夹道欢迎远方的来客,拍手齐唱他们古老的《迎宾曲》,那节拍就像骏马奔跑一样热情欢快。
我被迎进一间毡房,地毯上已经摆满了足够十几个人享用的食物。用餐之前先要洗手,但洗手之后千万不能甩手,那是对主人的极不尊重。我随着主人端起了金属酒杯,饮过之后想把酒杯放下,却发现杯底是尖的,端起来就不容易放下了。
我急于观看阿肯弹唱和民族运动项目,就钻出了毡房。一个正在小溪边梳妆的姑娘告诉我,她马上要参加一种叫作“姑娘追”的传统活动,就是小伙子骑马在前面跑,姑娘挥舞马鞭在后面追;实际上是给游牧的青年男女们创造一个交往的机会。她不由分说就往我身上喷了些香水,在我躲避的时候还说:“没关系的!”意思是让我也沾沾他们的喜气。
化妆后,她回到毡房里换衣服,再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一身盛装,装饰着银色花纹的帽子上插着猫头鹰的羽毛。哈萨克人认为猫头鹰是一种神圣的鸟,它的羽毛能辟邪,也象征着少女的纯洁。这个19岁的哈萨克姑娘骑着一匹高大的枣红色的马跑远了,谁也不必为她担心,因为她已有12年的“驾龄”。
很快,我听见了哨声,接着就和草坡上千百个喝彩助威的人一起,看到了远处一对对男女飞马跑来,那个穿红衣白裙的姑娘最醒目,她在马上的英姿与刚才小溪边化妆时判若两人。姑娘们尽管紧追不舍,但她们的鞭子并没有狠狠打在小伙子的身上。哈萨克女子的长裙都很鲜艳漂亮,在草原上不但很悦目,据说必要时还可以起到“流动厕所”的作用。
哈萨克人自古就有一套自己的优生优育的做法,他们不在本部族或血缘相近的部族求亲,他们遵循着一条有趣的“规则”:男子求亲要走过七条河,想必这样就离本部族相当的远了。
阿肯弹唱的即兴歌声响在了耳畔,赛马和叼羊的紧张场面展现在了眼前。我记起一路上常听人说,哈萨克是“马背上的民族”;有人还告诉我,歌和马是哈萨克人的两个翅膀。只要走到他们中间,就绝对会赞同这种说法。
无论多么好的风光,也许只有人,才是这万物之魂。在天山北麓辽阔的大草原上,自古以来,勤劳勇敢的游牧民族以他们的身姿将大自然装点得更加美好,同时牢固维系着边疆的稳定和民族团结。我们看到的,或许就是一部活的历史、一种活的文明;所以我们有理由将它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遗产,加以珍视和延续。
中国哈萨克族,人口近120万,主要聚居地位于新疆北部,四周由天山、阿尔泰山和塔尔巴哈台山等山脉环绕,中间是准噶尔盆地和伊犁盆地。伊犁河、特克斯河、额尔齐斯河、额敏河和乌伦古河等纵横交错,高原湖泊点缀其间。冬季寒冷,夏季凉爽,温差分明。盆地周围的群山是良好的夏牧场,河流两岸和山谷丘陵,是适宜的冬牧场。哈萨克人世代在这里从事游牧,也有少数人兼事农耕。
哈萨克族的历史,可追溯到西汉的“乌孙”。“哈萨克”,据传说意为“战士”,或“白天鹅”。这一族称最早见于15世纪中叶,是从金帐汗国分裂出来的操突厥语的一些游牧部落组成。哈萨克族信仰伊斯兰教,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现通行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哈萨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