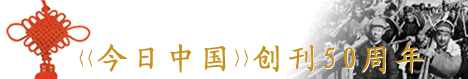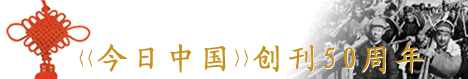漆艺长河浪淘沙
鲍文清
费了好大周折才找到了在北京东郊的乔十光工作室——大漆园。
一栋二层小楼,立于满眼麦田的旷野之中。院门便是豆棚瓜架。架上垂着尚未成熟的葫芦,大量的红花绽放在绿树丛中。小院主人乔十光教授一面向我介绍他亲手种植的花草树木,一面领我到两棵小树下,他说这是他精心移来培养的漆树,现在还未成材,若干年后,就能从漆树流下的液汁中提取原料,供他作漆画之用了。
室内,一张大案子用以作漆画之用,四周墙上挂的都是漆画,有的是从中、外美术馆展出后归来的老作品,有的则是尚未出阁的“新嫁娘”。园中之一侧是专为荫干漆画的荫室,亦属生产车间。楼上的一间工作室,是他绘水墨画的地方,他解释说:作漆画很辛苦,夜以继日地打磨,趁晾干的空隙,为追求轻松随意的情趣,自己也作些水墨,意在放松。楼上还有一个平台,备有民居式的木桌、木椅,可闲坐着看山,看树,看遍地的庄稼。他说:冬天时还可以看茫茫田野的白雪。
漆画世界
谈起漆画,人们会想到漆器。它们既是姐妹,又是母子。说是姐妹是因为它们都是由漆派生的两个分支。说是母子,是因为中国漆器的历史很长,漆画的历史却很短,漆画是在漆器的传统基础上衍生发展而成的。
漆器和漆画之漆,是从漆树上割取下来的天然液汁,它的抗潮、防腐、耐磨的性能不仅可以保护器物,它的深邃、柔和的光泽还可以美化器物。中国人的祖先首先发现并利用了这些特质。浙江余姚河姆渡第三文化层发掘的六千多年前的朱漆碗,便是中国也是世界最早的漆器实物。中国不仅是丝绸之国,陶器之国,而且还是漆艺之国。像以中国为中心的汉字文化圈一样,也有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漆文化圈。这个圈波及日本、朝鲜、越南、缅甸等亚洲国家,并誉满全球,其历史堪称灿烂辉煌。然而,近代却没落了下来。
历史进入了20世纪60年代,传统漆艺中出现了一种绘画的趋向,有人称之为漆画运动,站在最前列的就是现任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乔十光教授。
60年代初,越南磨漆艺画来中国展出,这使当时正在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研究生的乔十光大受启发,他想:中国传统漆艺积淀了丰厚的技术资源,为什么不能创造出中国特有的漆画呢?这个极新的设想,立即得到院长张仃及张光宇、庞薰琹、雷圭元等著名艺术大师的赞赏,在他们的支持与指导下,乔十光和他的同行,经过20年的努力,终于让漆画成了一个独立的画种,走上了绘画艺术舞台。1984年在全国美展上独立展出。这些漆画以金、银片、贝壳等为原料,然后经过涂漆、荫干,打磨成画,能现出与木刻、水墨画、油画迥然不同的风格,独具韵味。所以一经展出便在画坛引起注视,使人为之耳目一新。
用漆作画,不同于国画家在宣纸上、油画家在布上作画,而是一个很繁琐的过程。首先他必须是一个画家,像画画那样先设计、构图,然后他们必须又是一个漆艺家,还要付出很多的体力劳动,从涂漆、褙布与刮灰到镶嵌、彩绘、打磨、推光……荫干。一幅画从开始到完成,一般都要两三个月的时间。40多年来,乔十光就是在这种艰苦劳动中一步一步攀上了中国漆画的高峰。
1987年在中国美术馆中央大厅,举行了首次乔十光漆画展,展出作品100件,中国美术界的前辈吴冠中、蔡若虹等均在报上著文称赞。
两年后,他又首次在日本10多个城市展出他的漆画,并获得日本富士台的国际奖。1992年又赴美术之国法国巴黎举办了个人展,有二十几幅作品售出。英国维多利亚?阿尔博物馆,也收藏了他的漆画。他又在日本举办了“巴黎风景漆画展”。1996年,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乔十光漆画近作展。最近,他又应邀赴美国洛杉矶,在那里向美国人介绍漆画艺术。
无悔的选择
乔十光的童年和初中时代都是生活在朴素的农村,是在贫瘠的山东省馆陶县(今属河北)度过的。拾柴、割草、采野果、种田等他都干过。他天生的美感,眷恋着这诗画般的野趣,深深地接受着大自然对他的哺育和熏陶,单纯朴素的农村生活和纯美的大自然滋润着他的艺术心灵和纯朴的品格。
后来他考进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经过5年的勤奋学习,使他掌握了熟练的绘画技巧,但他仍不满足,决心闯入一个别人尚未涉猎的新画种——漆画的世界里,进行研究和探索。
乔十光的研究课题从福州漆器技术开始,他专程去福州,拜著名漆艺大师李芝卿为师,从配制材料、制胎,到镶嵌彩绘、研磨等等,虚心求教,细致琢磨消化,每个工艺细节都会提出十几个,甚至几十个问题,往往把师傅也问住了。
漆画要在水里打磨,一双手泡在水里连续几小时,甚至接连几天的打磨,拿着水砂纸的手指头,都会浸出血来。对漆器用料天然漆的皮肤过敏,是乔十光面临的一大难关,尤其是酷暑炎夏,常常被漆“咬”得浑身皮肤红肿,红斑成片,奇痒钻心,整夜难以成眠。被漆“咬”得脸庞肿胀,痊愈后,皮肤松垮,年轻轻的竟是满脸皱纹。他的妻子想念他,要他拍张近照寄回去,他只好为难地推托过去。他对这些毫不在意,还是一味地沉浸在对漆的捉摸中,默默地体察着漆的特性和神秘;默默地品尝着不可言喻的美感和快慰。
有人问他:“你的漆画水平这么高,到过哪些国家留学呀?”他风趣地回答:我是留‘闽’的留学生。”在福州一呆就是近两年的光景,他回到学校后继续潜心研究中国漆画的历史和东南亚各地的漆作。他感到日本的漆器和越南的磨漆画都非常好。中国是漆的故乡,应该比他们干得更好。于是,集体宿舍的双人房间变成他的漆画工场,乔十光搬来一张破的讲台,做荫干漆画之用。漆画的干燥自然的温度和湿度是很难达到的,必须人为地去创造。因此,在乔十光的宿舍里,长年累月笼罩着浓烈的漆味和潮湿臭气,而他却忘我地陶醉在大漆的迷茫朦胧中。
明天的路
如今乔十光已经年逾六旬,应该是再创漆画、更新风格的时候了。而他却患了帕金森病,常常往返于医院和漆作坊之间。他明显地消瘦了,脸色腊黄,他仍在不停地劳作,但已不能像以前那样不知疲倦地忘我了。据说这种病不易治愈,只能控制着不让发展或延缓发展。他走路已很迟慢,说话轻缓。奋力创建的工作室,似乎暂时成了隐居养病的别墅。暂时的病痛并没有使他献身漆画的愿望泯灭。采访中,他滔滔不绝地从古代帝王的龙蹲,到民间贫民的马桶,谈起漆画的历史从“人画平地,天画一半”谈到漆画的特殊创作方法……
作漆画是他的主业,同时他还承担着教学任务。他还编著了《漆画的制作和艺术表现》,并任《中国传统工艺?漆艺卷》等专著的主编。
谈起明天的打算,他说:我这一辈子就交给漆了,没别的本事了。漆是很独特的东西,要认识它的脾气很不容易,既要尊从传统中已经证实的漆的优势,又要不断继续发掘漆的新潜能,漆画的发展史,就是对漆的认识逐渐深化的历史,否则就真的是漆黑一团了,不可能达到千变万化的境地。
他的房间里挂着一幅对联: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还有一幅条幅:“布衣亦尊”。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安贫、乐道、敬业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