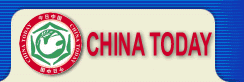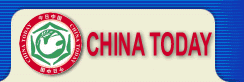|
两年前朱镕基总理曾用“民怨沸腾”来形容人们对电信垄断及其弊端的痛恨,今年“两会”期间他又指出,中国政府将对垄断行业,包括电力、电信、铁路和民航进行体制改革,改变其垄断地位。这一系列公开表态,说明政府已经感觉到对垄断开刀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了。
垄断:该寿终正寝了
李晓佳
最近,公众舆论的火力似乎集中在垄断身上。这大概是一些行业屡犯众怒所致:去年民航宣布禁止折扣然后上调票价;春运期间铁路全面提价30%;电信固定电话资费调整明降暗升;移动通信单项收费千呼万唤不出来,只端上来一道中看不中吃的套餐。恰逢此时,工商管理部门宣布将用半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对限制竞争行为比较突出的垄断性行业开展反限制竞争的专项执法行动。于是开始有人在媒体上叫骂,振臂一呼,应者四起了。
独特的中国垄断
 自从垄断与人类的经济活动一起问世以来,它就一直为人所诟病。中国早在西汉武帝时代就有过一次激烈的经济政策辩论,主题是应否实行盐和铁的国家垄断经营(论辩过程载入著名的《盐铁论》),反对者指其为“与民争利”,即在道德上是不好的。近代经济学问世以来,对垄断的挞伐上升到了理性的层次,认为它破坏了经济学终极意义上的完美境界:完全自由竞争。 自从垄断与人类的经济活动一起问世以来,它就一直为人所诟病。中国早在西汉武帝时代就有过一次激烈的经济政策辩论,主题是应否实行盐和铁的国家垄断经营(论辩过程载入著名的《盐铁论》),反对者指其为“与民争利”,即在道德上是不好的。近代经济学问世以来,对垄断的挞伐上升到了理性的层次,认为它破坏了经济学终极意义上的完美境界:完全自由竞争。
然而完全自由竞争的极乐天堂从未在尘世间出现,而大大小小的垄断倒普遍存在。随着分析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垄断产生的原因很多,影响也不一样,不宜一概否定。首先,优秀产品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造成事实上的垄断局面,例如微软。再者,投资巨大而单位产品利润较小所客观要求的规模经济也会形成垄断格局,例如卷烟工业中的每个厂家必须占据全国市场的6%-12%才能维持最低的有效经营。另外,部分行业所具有的非竞争性特殊性质(投资规模极大,重复建设会造成巨大浪费等)使其成为所谓的“自然垄断”行业,例如交通、电力、邮政、电信通讯、城市供水、供气等。最后,专利权的排他性使用在一定期限内也会形成垄断,而且这种垄断还是必须的: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补偿技术和产品创新的开发成本,给予创新所有人高额利润,以激励全社会的创新发明活动。
目前,理论界已经认识到,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内存在着垄断的不完全竞争状态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在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和公众也已经学会如何区别对待:对于创新形成的垄断予以保护(严格的知识产权法规);对于正当竞争、优胜劣汰以及规模经济形成的垄断给予宽容(例如对微软的同情);尽量缩小“自然垄断”的范围,迫不得已的,也尽量引入招标等竞争机制,并且代表消费者的利益对实行垄断经营的企业进行严密的监管(例如政府对成本进行严格核算,限定最高价等)。
中国的垄断之所以屡犯众怒,乃是因为它基本上不属于上面的类型,而且还具有一些让人难以容忍的特色。
一是垄断现象广泛存在,远远超出了必要领域。垄断不仅存在于军工、造币、大型公用事业等领域,也存在于与国家安全并非十分密切的所谓“自然垄断”领域,如电力、电信、铁路、城市供水供气等,甚至还存在于本应是竞争性的领域,如石化、石油、民航、银行、保险、证券、汽车等。
二者,中国的垄断不是竞争的结果,不是专利的赋权,甚至也不是什么“自然垄断”的产物,而是鲜明的行政行业垄断。它建立在政府保护基础之上,以法律法规为护身符,通过行政性审批制度,不仅在行业内独霸天下,甚至向竞争性领域延伸,以限制、驱逐其他竞争者的手段获取暴利。
再者,中国的垄断具有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政企不分。政府往往是垄断企业的所有者或大股东,不仅不能代表消费者对垄断企业进行严格监管,反而常常和它们结成共谋的利益关系,有时候比企业本身还更关心垄断利益,例如民航总局就总是担心航空公司亏损,不惜赤膊上阵,亲自限折提价。一些垄断企业甚至担负着行政管理职能,自己监督自己。
再次,中国的许多垄断具有自我强化趋势。不仅企业从垄断中尝到了甜头,效益奇高,有动力也有能力对政府部门施加影响,行政主管部门则明里暗里参与分肥,巴不得局面继续维持,就是国家和地方财政也形成了对垄断行业的依赖性,害怕打破垄断后财政收入的损失,因此政府缺乏打破垄断的动力和勇气,反而有强化垄断的动机和诱惑。
最后,中国的垄断问题还和产权制度、公有制等难题纠缠在一起。众多垄断巨头都是国有企业,其所在行业往往被看成“要害”和“命脉”,垄断找到了自己的理论依据。打破垄断,不仅有经济利益上的复杂性,而且牵涉到国有资产、工人就业等问题,具有政治上的敏感性。投鼠忌器,往往成为垄断企业天然的保护伞和现成的说辞。例如民航机票打折,就有人出来发话:要警惕国有资产“流失”。
无人能赢的棋局
这些特点使中国的行业垄断更加顽固,危害也更大。纯经济学观点来看,垄断不仅使产量不足、价格高昂,而且还会引起社会总体福利“无谓”的损失。
 最为明显、直接的受害者就是身为平头百姓的消费者了。首先他们要承受垄断高价和毫无道理的额外收费。例如,中国人均GDP仅是美国的1/50左右,但中国国际长话平均价格却是美国的6倍。中国每户每月平均市话费用40元左右,占平均收入的5%,而美国只占1%;此外,电话初装费、月租费、入网费,民航的机场建设费等等,一收就是数十年,有人说,这好比进饭店吃饭,要先交“空间占用费”和桌椅租金。陕西省省长大笔一挥,全省每部手机每月话费单上就多了10元“扶贫基金”。其次,服务恶劣,强买强卖。几乎所有的垄断行业都以服务质量差和服务态度恶劣而闻名,有绰号为证:“水老虎”、“铁老大”、“电霸”等等。消费者非但不是“上帝”,轻则受白眼,重则挨训,连起码的尊严都没了。安装电话必须买指定电话机,通自来水必须购指定配件,供电所强制更换指定伪劣电表,还要由指定施工队安装。再者,在价格上随心所欲,好点的走个听证会形式,自听自证;坏点的,如晴天一声霹雳,说涨就涨。例如今年春节,招呼不打一个,火车票价就涨了30%,辛苦一年的民工平白被剥了一层皮,有人解嘲说,就当是车上遭抢。这一切都使垄断成为千夫所指,投诉连年上升。例如电信、邮政,2000年的投诉比1999年增长了28.8%,今年一季度又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2.3%;水、煤气、电等公用事业方面,2000年比1999年投诉上升6%,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35.7%。 最为明显、直接的受害者就是身为平头百姓的消费者了。首先他们要承受垄断高价和毫无道理的额外收费。例如,中国人均GDP仅是美国的1/50左右,但中国国际长话平均价格却是美国的6倍。中国每户每月平均市话费用40元左右,占平均收入的5%,而美国只占1%;此外,电话初装费、月租费、入网费,民航的机场建设费等等,一收就是数十年,有人说,这好比进饭店吃饭,要先交“空间占用费”和桌椅租金。陕西省省长大笔一挥,全省每部手机每月话费单上就多了10元“扶贫基金”。其次,服务恶劣,强买强卖。几乎所有的垄断行业都以服务质量差和服务态度恶劣而闻名,有绰号为证:“水老虎”、“铁老大”、“电霸”等等。消费者非但不是“上帝”,轻则受白眼,重则挨训,连起码的尊严都没了。安装电话必须买指定电话机,通自来水必须购指定配件,供电所强制更换指定伪劣电表,还要由指定施工队安装。再者,在价格上随心所欲,好点的走个听证会形式,自听自证;坏点的,如晴天一声霹雳,说涨就涨。例如今年春节,招呼不打一个,火车票价就涨了30%,辛苦一年的民工平白被剥了一层皮,有人解嘲说,就当是车上遭抢。这一切都使垄断成为千夫所指,投诉连年上升。例如电信、邮政,2000年的投诉比1999年增长了28.8%,今年一季度又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2.3%;水、煤气、电等公用事业方面,2000年比1999年投诉上升6%,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35.7%。
普通消费者受到的侵害看得见、摸得着,媒体也喜欢打抱不平,因此显得格外突出。实际上,其他经济部门的损失更大,只不过不被注意罢了。垄断行业几乎都是社会经济的基础行业。众所周知,良好、廉价的基础服务是经济主体健康发展的前提之一,反之,就会起阻碍作用。目前中国企业劳动力成本低廉,但水、电、通讯、运输等成本却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这一优势,甚至使企业不堪重负,降低了它们的利润,削弱了产品竞争力。这一损失很难有确切的估算,但的确十分惊人。
一直有人辩护说,虽然消费者和一些企业受损,但垄断维护了国家和政府的利益。这真是个天大的谎言。首先,垄断利润绝大部分都转化成了部门利益、集团利益乃至私人利益,真正转为国家利益的少之又少。垄断部门当年靠国家巨额资金起家,却一直巨额亏损(邮政、铁路、电力、民航等),年年要财政追加输血,好点的也不过数年前才扭亏为盈。钱都到哪里去了?都转化成了最气派的大楼、最臃肿的机构、最庞杂的人员,最可观的工资和最齐全的福利。其次,就算垄断行业多给财政上缴了几个钱,那也不过是眼前的芝麻,损失的西瓜要大得多。全国其他行业的企业因为增加了额外成本而降低了利润,从而也减少了对财政的利税贡献,正所谓“得之东隅,失之桑榆”。再次,目前垄断行业对国家经济政策目标的达成造成了极大的阻碍。家电一直打不开农村市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电价格太高,消费不起。又如,近年来经济增长乏力,居民储蓄如天文数字,民间投资热情却不高,这主要是可进入的领域大部分已饱和,而有利可图的领域则处于垄断状态,民间资本不得其门而入。最后一点,垄断还对国家威信造成了损害。由于政企不分,消费者对垄断的满腔怒火往往顺路烧到政府头上,例如飞机调价,大家骂民航总局;电话调价,大家骂信息产业部。
既然消费者、其他企业、国家都受损,那么垄断行业本身获益,应该不成问题吧?答案也是不一定。眼前,垄断行业银子滚滚,工资高高,似乎受益颇丰。然而,长期缺乏外部竞争压力和内在改良动力,加上国企本身的痼疾,使得垄断企业成本极高,效益低下,远看是个巨无霸,近看不过是个胖嘟嘟的棉花包,十分虚弱。例如人保、人寿、太平洋和平安四大保险公司垄断了全国95%以上的市场份额,拥有规模庞大的数千家分支机构,然而中国的保费总收入尚不及美国的2.5%和日本的3.5%。再如电信,中国已建成世界第二大固定电话网、第三大移动通信网和第三大互联网,然而每部固定电话平均每月拨打国际电话1.63分钟,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1998年资料);平均拨打国内长途电话也才31.8分钟(1999年资料)。这种“热装冷用”的商务模式,不仅没有充分发挥电信网络的作用,造成了巨大的投资浪费,而且抬高了单位通信成本,使得电信业的财务基础很不牢固。对此,垄断部门自己也是心知肚明,所以有了眼下最为有趣的一个现象:面对WTO,底气最足的是国家最早撒手不管、充分竞争的家电和纺织行业,最害怕的则是拥有庞大资产、一直养在襁褓里的垄断行业,因为关起门来可以称王称霸,一旦真老虎来了,纸老虎难免现形了。
如果说,行政垄断在过去特定时期内还曾发挥过集中资源、统一管理等正面作用,那么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于国、于民、于他人、于自己均一无是处,成了无人能赢的棋局。除极少数领域不得不如此外,垄断已丧失了继续存在的理由。
天边的阴影
1999年“两会”期间,朱镕基总理曾用“民怨沸腾”来形容人们对电信垄断及其弊端的痛恨;2000年春两会结束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又说中国电信的价格还要成倍的降低;2001年3月15日回答记者提问时他又指出,中国政府将对垄断行业,包括电力、电信、铁路和民航进行体制改革,改变其垄断地位。这一系列公开表态,说明政府已经感觉到对垄断开刀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了。的确,形势逼人。
垄断对整个社会经济造成的损害正逐渐为人们所认识,来自垄断行业内部的“垄断有利于国家利益说”已被揭穿,公众舆论在去年和今年开始形成对垄断“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消费者利用法律武器自我维权的意识也已深入人心,向有关部门投诉乃至向法院起诉都屡见不鲜。例如铁路春运涨价,有河北律师起诉;电信资费调整,有北京、湖南几位律师和中国消协的法律工作者提起法律诉讼;陕西加收“扶贫基金”,有大学法律教师起诉。同时,有关政府部门也开始认识到,继续维护垄断利益,对国家和政府都没有什么好处。
 然而真正对垄断构成威胁的还不是媒体上的文章和法院的起诉书,而是WTO的迫近。加入WTO不仅意味着享有成员国的待遇,也意味着承担应尽的义务,在一定时限内开放国内市场,允许外资进入诸多垄断行业就是义务之一。根据美国单方面公布的中美双边协议,金融方面,入世两年后外国银行可对中国企业开展人民币业务,5年后从事人民币零售业务,取消地域限制和客户限制,享有国民待遇;证券方面,允许合资证券公司中的外资比例达到33%,合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比例达到49%;电信方面,允许外资在合资电信企业中占有49%的股份,1年后可增至50%;允许美国互联网服务商在中国开展业务;外商将获准参与卫星通讯业务等等。这些规则不仅针对中国,而且针对所有世贸成员国。 然而真正对垄断构成威胁的还不是媒体上的文章和法院的起诉书,而是WTO的迫近。加入WTO不仅意味着享有成员国的待遇,也意味着承担应尽的义务,在一定时限内开放国内市场,允许外资进入诸多垄断行业就是义务之一。根据美国单方面公布的中美双边协议,金融方面,入世两年后外国银行可对中国企业开展人民币业务,5年后从事人民币零售业务,取消地域限制和客户限制,享有国民待遇;证券方面,允许合资证券公司中的外资比例达到33%,合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比例达到49%;电信方面,允许外资在合资电信企业中占有49%的股份,1年后可增至50%;允许美国互联网服务商在中国开展业务;外商将获准参与卫星通讯业务等等。这些规则不仅针对中国,而且针对所有世贸成员国。
为了应对这股潮流,各国已纷纷行动起来,打破国内垄断,对外开放。例如,美、日、加和部分欧盟国家已于1998年1月1日全面开放电信市场;南美阿根廷也在2000年11月开放电话业务;新加坡则将原定的基本电信业务开放时间两度提前,从2007年提前到2002年,再提前到2000年,终于在2000年4月1日完成了开放。
各国之所以要迅速打破垄断,一方面是为了通过把现有垄断企业搬出温室,尽快增强它们的体质,以免在未来竞争中不堪一击;另一个考虑则是在发展迅猛、创新频繁的领域(如电信等),如果不加快国内竞争的步伐,在为期不远的国际竞争中必然落败,使整个国家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因此,如果中国的垄断行业还继续沉醉在惟我独尊的迷梦之中,数年后狼群入寇,不仅自己要被撕得遍体鳞伤,恐怕整个国家和民族都要付出沉重代价。
怎么办?
垄断肯定要打破,但以为只要国家发一道命令就能解决问题,却不免思维简单。解决垄断问题很复杂,必须看条件是否成熟,而且要根据客观情况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从目前来看,打破垄断已经具备了比较充分的条件。
首先是技术条件。有许多“自然垄断”是基于技术原因,例如传统的电话线路每家只铺一条,就像只有一条自来水管一样,这独一无二的市话线就成为电话公司锁定用户、建立市话和其他电信业务垄断的基础。新兴技术则可以打破这一制约,例如刚刚出现的社区宽带网技术,直接传输声音、图像和数据,实现人们常说的“三网合一”,长途电话和市话的区别也将消失。社区零散用户通过宽带网结成一个整体,自由选择不同的电信服务商,彻底从技术上打破垄断控制。另外,现有的有线电视网改造为宽带网的技术也已成熟,更加有利于突破垄断。
其次是管理条件。许多垄断的造成是因为在竞争环境下无法进行有效管理,要么免费搭便车严重,投资者没有收益,要么造成区域分割,因此像电力、交通之类只能实行全国统一垄断运营。随着技术条件和管理经验的进步,具有自然垄断性的基础网络和运行于其中的服务已经可以分开,突破垄断。例如铁路实行“网运分离”,将干线铁路网基础设施与具有竞争性的客货运输分开,前者集中管理,后者自由竞争;电力实行“网电分离,竞价上网”,对全国主干输变电线路统一管理,而各个电厂竞争上网,出售电力。
最后是资金条件。许多公用事业之所以具有自然垄断属性,是因为在当时除了国家财政,没有任何私人力量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投资建设,也没有任何人有力量从事正常的经营维护。随着社会资金的不断积聚,筹资、融资方式的推陈出新(例如银行借贷、发行证券等),这一点已经日益不成问题。
具备消除垄断的条件之后,下一步的问题就是如何一步步突破垄断。目前来看,政府反垄断的做法是单纯行政执法,由工商管理部门行政查处。工商部门决心也很大,例如最近北京市工商局就宣称把反垄断矛头首先指向保险业,保险业开会写文章辩驳,双方在媒体上打了一回嘴仗。然而热闹归热闹,效果却值得怀疑。早在1999年,国家工商局开展过一次反垄断重点专项整治,这次已经是第三次大规模整治行动了,显然,最多只是碰了垄断的几根毫毛而已。
工商局自有苦衷。目前,有关反垄断的条款散见于不同法律中,主要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价格法》,而且两法中均未正式使用“垄断”一词。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仅仅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执法机关,查处起来不仅底气不足,而且有些垄断巨头根本就不让你查,例如《电信管理条例》和《电力法》等就规定本行业的垄断行为归电信和电力部门自己管。为了结束混乱状况,对付垄断于法有据,有专家指出,制定《反垄断法》已成当务之急。事实上,早在1987年,我国即已着手准备制订《反垄断法》,1994年便已列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1999年开始,反垄断立法步伐明显加快,估计很快即可面世。
立法之后的问题是执法。在中国,谁都知道立法容易执法难。司法还未完全独立的情况下,反垄断法很可能在地方政府和部门压力下失去作用。例如前面所述律师、法律工作者诉铁路、电信,最终不是败诉就是不了了之;陕西诉手机“扶贫基金”附加费,则根本就不被受理。所以有学者对依靠反垄断法对付垄断持保留意见。
反垄断法律主要是一种惩罚性的消极应对措施,而积极的、根本性的措施莫过于打开行业大门,允许竞争者进入。事实证明这种做法虽然不是药到病除,却也立竿见影。因为只要有足够多的竞争者进入,独家垄断就不可能,寡头垄断也很难。例如有了联通,电信的表现就要好得多,虽然两者都还不能令人满意。现在又有了一些更令人兴奋的消息,如铁通进军固定电话业务等等,希望这不是走走过场。
然而竞争者的进入要能够彻底动摇垄断格局,还得有一个前提:大家在一条起跑线上。中国联通刚成立那段日子就吃够了“后娘养”的苦头,中国电信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不给联通互联互通的机会,在中继线问题上多方限制。显然,要想举办一场公平的比赛,裁判和运动员就不能是同一个人,也不能是一家人。
因此,解决行政垄断的关键不在于“垄断”,而在于“行政”。只有政府部门彻底转换角色,割断与垄断企业的一切利益纽带,从垄断利润的分肥者过渡到公平规则的维护者,才能真正瓦解垄断体系,重建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对政府职能的认识要有一个根本转变:政府不应掌握大量经济资源亲自进入市场操作,而应清心寡欲,垂拱而治。目前,加入WTO和世界范围内向小政府的回归,都是我们进行这一改革的有利环境。这一点,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了。
今年3月26日上午,国务院体改办主任王岐山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上语出惊人:入世,将是全面打破垄断的“惊险的一跳”。当天下午,朱总理在会见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外方代表时,似乎对如何“跳”作了注解:中国将进一步转换政府职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