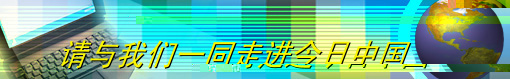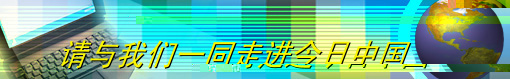贾樟柯:从“地下”到“地上”
小尹
 |
| 贾樟柯(右)与《任逍遥》女主角(钟) |
贾樟柯曾是中国著名的“地下导演”,至今的作品只有故乡三部曲《小武》、《站台》和《任逍遥》,虽然数量不多,且都是“地下电影”,却也在国际电影节上拿了不少奖项。相比过去十年来其他数名地下导演,贾樟柯可谓幸运。2004年7月底,他的电影《世界》通过了中国广电总局的审批,正式代表华语电影参展威尼斯电影节,并初步决定将于年底在中国国内公映,这标志着这位“地下导演“已经“浮出地面”。
在西方,“地下电影”一般说来是指在非院线上映的电影,从内容上说会涉及到反主流社会、反政府、反主流道德等,而观众也一般是年轻人,其电影对于电影形式和电影本体的探索也是不遗余力的。而中国的“地下电影”,内容上倒是根本没有反社会、反政府、反道德的特征,其被禁的原因,是这些影片在没有送交国家电影主管部门审查或者在审查没有被通过的情况下就送出国外参加比赛,从而不能获得在国内公映的权利。
贾樟柯的头三部电影就都属于这样的“地下电影”。
贾樟柯的第一部电影《小武》于1997年5月拍摄完成,故事发生在山西汾阳——一个正在由县改市的县城:午后烈日灰土弥扬的街道、五金店里邓丽君软绵绵的滥情歌声、路边小摊的刘德华画片、因陋就简的台球桌以及叼烟的小青年……整日游荡在这里的,是窃贼小武。他被朋友和情人拒绝,家里人也不接受他。
他经常在拆建的破败的县城里晃荡,最后被父亲赶出家门。最后小武在一次例行“工作”的时候,被公安干警抓获并被铐在电线杆上。街上的行人冷漠地看着他,他冷漠地看着街上的行人。
影片用写实的长镜头展现了处在变革时期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和人们的精神状况,非职业演员本色、真诚的演出也为影片增色不少。这部影片在一系列国外电影节获奖: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首奖:沃尔夫冈·斯道奖,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亚洲电影促进联盟奖,第20届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热气球奖。法国《电影手册》评论:“《小武》摆脱了中国电影的常规,是标志着中国电影复兴与活力的影片。”德国电影评论家乌利希·格雷格尔称贾樟柯为“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
载誉归来后,贾樟柯来到上海,筹备他的第二部电影《站台》。贾樟柯回忆说:“《小武》在柏林首映后,反响很好,因为影片已经获了奖,上影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开始对我感兴趣。他们与国外一些同行谈合作时才知道原来国内还有我这么一个导演。”贾樟柯在这种欢迎自己的氛围中很快做出决定:要在上影厂完成《站台》。这大概是贾樟柯第一次萌生与上影厂的合作念头,那段时光他过得相当开心。1999年1月,上影厂因故终止了与贾樟柯的合作。
最终,在海外资金的帮助下,贾樟柯还是完成了《站台》的拍摄。《站台》的故事仍然发生在他的故乡——山西汾阳,仍然用写实的手法表现县文工团的几个年轻人之间的感情和20世纪80年代社会变迁几个人的命运。他们从“站台”这个起点出发,经受了花花世界的洗礼,最终还是回到“站台”,只是早已物是人非。
《《站台》就像是一部信息量很大的资料性故事片。故事里含有关于80年代的大量信息,影片主人公崔明亮身上似乎集中了这一时代的很多特点:这个青年文弱,戴眼镜、曾经穿过喇叭裤、蓄过长发,有艺术家的气质,但似乎缺少艺术天赋,爱情上很痛苦,对所恋的人却保持着忠贞的友情。这个人就是80年代年轻人曾经有过的一部分。
站台》是一部半自传性质的电影,也是他个人最喜欢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在他念大学的时候就一直酝酿着了。这个东西不拍出来,他就做不了别的事情。因为80年代是他怎么也忘不了的一个时代,拍出来,他才能轻松。
与《小武》一样,《站台》在国外的电影节上获得了各种各样的荣誉,但却没有让贾樟柯感到多少欣喜。他说:“《站台》在2000年9月威尼斯电影节上的反响出乎我的想像,这又是我最失落的时候。”在国外越受肯定,贾樟柯越期望自己的电影能与国内观众见面。
2002年,贾樟柯完成了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任逍遥》。也许真如他自己所说,拍完《站台》后就放下了心理的重担,《任逍遥》一改前两部电影沉重的写实风格,显得诡异迷离。
电影讲述了山西大同失业工人子弟的生活,19岁的少年彬彬和小济抢劫银行未遂的故事。当谈起为什么要拍这个片子的时候,贾樟柯说:“我感觉到那里的年轻人有一种压力感。一方面,他们的生活环境比较落后,变化缓慢;另一方面,因特网等现代传媒又让他们了解到外面存在着一个跳跃和丰富的世界,从而在内心深处产生一种矛盾感和压力。”
同年,《任逍遥》入选了第55届戛纳电影节参赛影片名单,但最终没有获得任何奖项。有媒体评价说相比前两部电影,《任逍遥》显得做作而不够真诚。
2003年,贾樟柯再次向上影厂申报新电影《世界》的立项。
2004年1月8日,各大电影厂都收到了电影局一号令,贾樟柯正式解禁了。《世界》剧本也很快审查通过,“没有必须的修改意见,只是建议。有的我采纳了。”4月13日,贾樟柯的影片送广电总局电影局双片审查,17日就拿到了结果。“他们工作效率很高,提出三条修改意见都是我能接受的。我看到了一种努力,他们的工作方法、对电影的认识都灵活了,尽量在配合尊重制片方,如果按电影工业规律这么做下去,我会很乐观。”
《世界》仍然是讲底层外来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据看过该影片的业内人士透露,此片已经完成了后期剪辑,但是音乐还没有配好,看到的只是录像带,视听效果和影院效果无法相比。但是《世界》的雏形已露,并打上贾璋柯浓厚的个人风格烙印:整部影片包含了大量的山西方言,只能看字幕才能知道主人公的对话;音乐、舞蹈仍然是贾璋柯难以割舍的情怀,片中不断出现歌舞场面;情节冲突并不强烈,侧重刻画小人物的生存、精神深处。
投资方把影片送威尼斯电影节参赛,7月28日,贾樟柯接到威尼斯评委会主席马柯·穆勒助手的电话:“你入选了。赶快准备一下故事梗概、剧照、导演的话。”电话匆匆挂断,贾樟柯并不完全确信,直到29日他也从威尼斯官方网站上看到自己的影片才松了一口气。因为按照投资人的计划,《世界》完成后肯定得借国际电影节的宣传再回国上映,而威尼斯的时间刚好赶上,他不用等待其他电影节,可以直接按部就班地参赛、回国上映、开拍新片。
不管9月威尼斯电影节是否能获奖,但贾樟柯应该不会再有做“地下导演”的尴尬和遗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