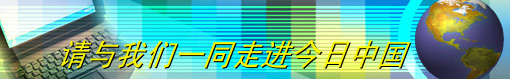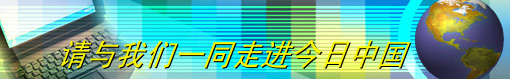严仁英:中国围产保健之母
祝 璇
 |
| 严仁英近影 |
91年前,她出生在天津的一个大家族中;她的祖父是被誉为“旧世纪一代完人”的南开大学创始人严修;27岁毕业于协和医学院,并成为中国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的得意门生。她是一位杰出的妇产科、妇幼保健专家,更是一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她就是严仁英。
临床医学里长出的一个“怪胎”
严仁英的早期教育,是在祖父家里开办的幼稚园和小学完成的。严仁英说祖父对她的影响很大:“我觉得在家庭里头祖父教给我很多东西。我的人生态度、能够宽容对事、能够很好地与人合作,可以讲都得益于老人家中西合璧的教育方式。”
1935年,严仁英从清华大学生物系考入协和医学院,选择了妇产科作为终生的事业,这个选择很感性:“我学妇产科就是因为我喜欢看见产妇一个人儿来了两个人走。”在严仁英看来,“做妇产科大夫是迎接生命的到来,工作很有成就感,所以就愿意上妇产科”。
刚到妇产科的严仁英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记得那会儿我还在协和做学生的时候,一有机会就呆在产房,老师们忙着做手术,我们就在那儿守着。那产妇有的喊叫,有的呻吟,可是我的老师一来了就都没声音了。我就奇怪,想老师有什么魔术啊,怎么回事啊,只要她一到坐到产妇旁边,拿手摸着产妇的肚子,给她听胎心,跟她说现在都进展到什么情况了,跟那个产妇一边聊天一天给她做检查,产妇就非常安静了。我就觉得这位老师真是特神奇。”严仁英提到的这位老师就是中国妇产医学界的泰斗、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教授。
经过五年的学习,1940年严仁英获得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并被留在妇产科工作,作了一名住院医师。林教授对严仁英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希望她成为自己的接班人。“我觉得在临床上没有搞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这一点对不起我老师,我从临床转向保健了。”严仁英“检讨”说,而事实上,她是在在经历过大量临床实践,接触过大批触目惊心的病例之后才转向的。
建国之初,严仁英曾和丈夫一起为妓女检查身体,在这项工作中她深刻了解到旧社会妇女所受的摧残。1964年她到北京密云办的“半农半医”学习班,又切身体会到当时农村缺医少药,妇女疾病不能及时发现、治疗而给她们带来的种种痛苦,看到了妇女们遭遇非意愿妊娠时所面临的危险。她逐渐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临床工作每次面对和治疗的是一个人,而保健面对的是一个人群,医疗只能救治一个人,预防则可造福一大群人。
1974年严仁英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成立了计划生育研究室,与国内一些知名的专家协作,试验使用前列腺素、中药穿心莲等终止早期和中期妊娠(临床应用成功率达90%以上),以及可逆性女性绝育手术等,为今天的药物流产奠定了基础。80年代初,严仁英在北京郊区进行围产保健试点研究,采用高危管理法降低母婴死亡率,使围产儿死亡率大大降低。在她的大力推广下,围产保健技术应用于全国。中国围产儿的死亡率也由1988年的15.13‰,降低到1997年的10.93‰,大约每隔三年下降10%, 严仁英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的围产保健之母”。1996年,严仁英的关于神经管畸形的研究成果被国家卫生部采纳,全国80%准备生育的妇女服用了叶酸增补剂后,每年出生的先天畸形儿童减少了5万例。
 |
| 1975年,严仁英(右)与恩师林巧稚在妇产科学术会议上。 |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严仁英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妇女青春期、产褥期、更年期的心理保健和病理防治方面的研究。在实践中她把生殖保健从生物医学的概念,扩展到了社会科学的范畴,生殖健康服务也从单纯的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扩展到涵盖一生的一条龙健康服务。
严仁英开玩笑说她自己是临床医学里长出来的一个怪胎,是“革了临床医学的命”,因为从临床出来搞保健,在别的地方还没有。把临床医生对一个病人的关注与责任拓展到对整个社会,整个人群更加深切的关怀上,严仁英认为这是自己做的非常值得的一件事。
“新中国妇女的标本”
1951作为妇产科大夫的严仁英参加慰问团赴朝鲜慰问志愿军,并于1952年参加中国抗美援朝总会组织的由中、英、法、意等七国专家组成的调查团,前往朝鲜调查美军发动细菌战的罪证。1953年在德国柏林展览会上,严仁英用流利的英语和翔实的资料向参观者讲述了美军发动细菌战的暴行。从那以后,严仁英又多次作为新中国妇女的代表出现在国际场合,在很多问题上承担着形象大使的重任。
对于这些工作,严仁英常说自己是“不务正业”,她还开玩笑说:“我一直到12岁还没出过家门,幼儿园、小学都在家里上的,到上中学了才出来,所以老有点野性大发,老想往外跑。”事实上这些工作确实曾使她一度脱离妇产科的工作,谈起这段经历,严仁英风趣地说:“我们搞妇女保健工作跟妇联的工作比较接近,所以他们常常愿意带我出去,另外我能讲英文,身体也比较好,我就说我是一个好标本,我要把新中国的妇女形象展示给外国人,让他们看到中国妇女真的是解放了,不再是他们心目中的裹着小脚的形象。所以这种‘不务正业’,就变成了正业了”。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
| 严仁英与丈夫王光超共同为我国医学事业做出贡献,被誉为"杏林双彦"。 |
严仁英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她的丈夫王光超是原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的哥哥,在“文革”期间,严仁英与王光超被诬为“刘少奇伸向北医大的黑手”。1966年她从北京医学院妇产科主任被贬为卫生员,当时她正患甲亢,但仍然被派去抬担架、打扫卫生,就是这样的一项工作她也做得非常出色,直到现在那儿的老职工还说:还是当年严教授打扫的厕所最干净。虽然受尽磨难,但提起这段经历时她的表情淡淡的,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对于她来说这些不算什么:“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对于“文革”期间对她进行迫害的造反派,严仁英后来与他们和睦相处,似乎那些事情从未发生过。她说:“那个特殊年代里,他们做的那些事情并不是对着我个人的,而是因为他们忠于毛主席,忠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我根本不怪他们。”
2003年7月,严仁英失去了共同生活60年的丈夫。谈起故去的丈夫,严仁英充满了深情,她至今仍能清晰的回忆起对丈夫最初的印象:“有一天,一个得了白喉的小男孩,被家里人抱着冲进门诊时,他憋得整个人都紫了,王光超就找了手术的包马上给他的气管切开了,孩子立刻就从窒息当中就解脱出来,喘气就自如了。我当时想这个人将来肯定是个好的外科大夫。”
接受采访时,严仁英常常会呵呵地笑,这笑声极富感染力,如孩子般天真、爽朗,能够让人感受到她内心的纯净和乐观,在这种笑声里一切困难都将不再是困难了。不过严仁英也有担心与忧虑:“预防工作跟临床工作的比重应该怎么确定,国家应该花多大力量来重视保健工作,提高保健工作人的水平和待遇,让保健工作能够更深入地到群众中去,让广大群众在这方面得益,我觉得这方面做得还不够。”
现在,90高龄的严仁英仍然每天坚持工作半天,她有一个愿望,她希望自己能一直工作到2006年。或许,对于她来说生命就意味着工作着的每一天……
(文章及图片由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