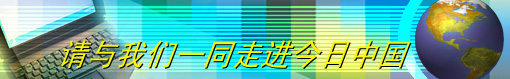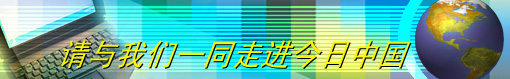奥运会:最炫的超级秀
文/小
乔
 每年有10亿观众收看奥斯卡颁奖仪式,2000年,220个国家和地区,几乎世界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转播了悉尼奥运会节目,近40亿观众通过电视收看了奥运会的赛况,悉尼奥运会网站的点击率达到了90亿次。奥运会已成为世界上最吸引眼球的超级秀。
每年有10亿观众收看奥斯卡颁奖仪式,2000年,220个国家和地区,几乎世界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转播了悉尼奥运会节目,近40亿观众通过电视收看了奥运会的赛况,悉尼奥运会网站的点击率达到了90亿次。奥运会已成为世界上最吸引眼球的超级秀。
奥运则不仅是体育最广泛的表达,而且超越了金钱的左右、政治的隔阂、种族矛盾和性别差异,成为人类最有力和最直接的沟通舞台,它包罗万象而奇炫。奥运会成了一个能够给观众带来全方位享受的超级秀,有辉煌,有失败,有庄严,有八卦,但奥运会绝不沉溺于此,它的结局永远都给人希望,观众永远可以从中看到人类向自身极限挑战的崇高,真的是很难再找出比奥运会更好看的了。
所有人的游戏
大脚飞鱼伊恩·索普说:“奥林匹克精神的意义在于:世界各地的人民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合而为一。大家在一起平等竞争,无论你来自哪个种族,皮肤是什么颜色,从事何种职业,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途径可使人们建立如此水平的友谊……每一位运动员都代表其国家将世界融为一体。”
顾拜旦在恢复奥运会时曾希望通过体育比赛来替代国家之间的战争,但百年来战火并未平息,种族、信仰、国籍、政治立场都深刻影响着奥林匹克运动。但国际奥委会始终在为保持奥林匹克运动的独立性而努力,在承认奥林匹克运动与政治不可分割的同时,拒绝成为任何国家的政治工具。1960年,国际奥委会禁止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参加罗马奥运会,并于1970年正式取消了南非国家奥委会的资格,直至1992年,取消了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才获准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1992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禁止南斯拉夫运动员进入他国领土参加国际比赛。国际奥委会经过斡旋,使南斯拉夫运动员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巴塞罗那25届奥运会比赛。国际奥委会也公开批评了美国国会对北京申办奥运会的非议和干涉。
奥林匹克运动为各民族和种族的人们提供了公平竞技的舞台。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黑人运动员杰西·欧文斯,五次打破世界纪录,夺得4枚金牌,成了一道跑得最快、跳得最远的“黑色闪电”。这让希特勒十分不快,他指令德国跳远运动员卢兹·朗战胜欧文斯,但朗对欧文斯亲如挚友,还帮助欧文斯改进起跳的技术,欧文最终跳出了8.06米的新奥运会纪录。希特勒气急败坏地离开了看台,并拒绝与欧文斯握手。欧文斯说,他到这里来不是为了与元首握手,而是为了获得胜利,他已经获得了。
1972年9月5日,11名犹太运动员在慕尼黑奥运会上成为纳粹恐怖活动的牺牲品。但正是在这届奥运会上,美籍犹太人马克·史毕兹拿到了7枚金牌,成为奥运史上获得金牌数最多的人。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上,吉娜·汉普希尔高举火炬跑入了体育场,而她的祖父杰西·欧文斯成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奥林匹克运动员后,也只能从侧门进入体育场,因为他是黑人。
 1988年汉城奥运会开幕式上,韩国和朝鲜的180名运动员,在白底、蓝色的朝鲜半岛地图旗帜的引导下,伴着《阿里郎》的歌声一同步入会场,体育跨越了政治的隔阂。
1988年汉城奥运会开幕式上,韩国和朝鲜的180名运动员,在白底、蓝色的朝鲜半岛地图旗帜的引导下,伴着《阿里郎》的歌声一同步入会场,体育跨越了政治的隔阂。
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女儿凯西·弗里曼点燃了奥运会主火炬的圣火。据说连最强硬的种族分子看到这一场面也忍不住泪盈眼眶。英国《每日电讯报》评价说,“还有什么和体育有关的东西能比弗里曼的这个动作更让人感动呢?”
最优秀者的比赛
1983年萨马兰奇亲赴美国洛杉矶,为因“隐瞒职业化”身份而被取消奥运会金牌资格的美国运动员吉姆·索普昭雪平反,并亲手将两枚被没收的金牌交还给他的儿子,结束了一桩持续了70年的冤案。萨翁的这一举动,向全世界表明,奥运会决心告别狭隘的“业余原则”,向包括职业运动员在内的所有高水平运动员敞开大门。
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23岁的索普获得了五项全能和十项全能两项金牌。半年后,却因他曾为每周15美元的酬劳参加过棒球队,违反了业余原则,被取消了奥运冠军资格。美国业余田联曾扣下杰西·欧文斯在1936年奥运会上获得的四枚金牌,因为他曾靠跳踢踏舞、与赛马进行过人马赛跑谋生。他说:“人们说作为一名奥运冠军,与一匹马赛跑实在是有失体统,但我又应该做什么呢?我是有四枚金牌,但你不能以此为生。”业余原则曾被视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基本原则。但要做到业余与职业间泾渭分明却很难,运动员只有把主要精力和时间用于训练才能达到最佳竞技状态,许多运动员长期训练的花费只能靠国家或企业赞助,真正能够做到业余的恐怕只有那些有闲阶层。
20世纪60年代,打破业余原则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奥运会应是世界上最优秀运动员之间的竞赛,而不管他们是否是业余运动员。国际奥委会也逐渐改变了态度,不再禁止对运动员的财政支持,运动员可以像艺术家或科学家一样得到赞助以补偿他们的工作和做出的牺牲。
有人将1988年汉城运动会称为业余体育的终结,1990年通过的新版《奥林匹克宪章》彻底抛弃了“业余原则”。奥运会向职业运动员的开放,意味着奥运会将成为世界上第一流运动员的竞技场。过分职业化也许会奥运会背离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和宗旨,但毕竟观众因此可以看到全世界第一流的“演员”的最高水平表演,比赛场面也将更加激烈和扣人心弦。
最性感的秀
有人将悉尼奥运会称为“女性奥运会”,因为2000年正好是女性参加奥运会一百周年。在参加悉尼奥运会的11084名选手中,38.3%是女性,是历届奥运会女性运动员比例最高的一届。
现代奥运会的创始人顾拜旦认为,女子参加奥运会不切实际,毫无趣味和美感,让女性的身体在观众面前晃动实在是有失观瞻。1900年法国人玛格丽特·阿博特和母亲参加了奥运会的九洞高尔夫球项目的比赛。百年后,女选手参加了奥运会44%项目的比赛,现代五项、撑杆跳高、链球和举重等比赛中都有女性的身影,现在只剩下拳击和摔跤还没有女性参与。国际奥委会计划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让女运动员的比例增加到50%。
竞技中男性和女性充满美感和吸引力,奥运会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性感的秀了,有什么比充满力量和美的身体更性感?不仅运动装变得越来越性感,健美的肌肤本身就是最美丽的衣裳,运动员们纷纷在奥运会上,“裸露”出镜。格里菲斯·乔伊纳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飘逸的黑发,五彩长指甲、豹子般的身材、飞样的速度,是人们记忆中永远难忘的花蝴蝶。荷兰女游泳运动员德布鲁因艳丽的彩妆、发达的肌肉、美人鱼般的线条,更让人惊为水中的阿芙洛狄忒。
性感吸引着观众的眼球,也吸引着广告商的投资,为运动员们带来运动场外不菲的收入。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被伊恩·索普因为“性感的鼻子和双脚”被选为劳力士表的代言人。运动所散发的性感,运动明星们所代言的产品和他们魅力四射的身体,更是成为时尚追逐的热点。
商业化魅力难当
据估计,划入悉尼奥委会的收益高达20亿美元,悉尼奥运会组委会主席耐特兴奋地表示:“连我们自已都没有想到,悉尼奥运会竟能创造如此巨大的收益。”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局从目前看也非常不错,已有可口可乐、柯达、松下、斯伦贝谢神码、恒康、三星、维萨、斯沃琪等8家跨国集团公司,以每家不低于6500万美元赞助价值与国际奥委会签约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TOP(The
Olympic Partners)计划成员。美国NBC广播公司、日本NHK广播公司、欧洲广播联盟、澳大利亚电视台、新西兰电视台等签订的电视转播合同将支付2008年奥运会15.8亿美元的费用。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基本收入已有了保障。
商业化似乎从现代奥运会诞生之日起就在所难免。在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上,人们因为富商乔治·阿维罗夫出资建造了体育场,而为他雕了大理石塑像,顾拜旦的名字不但没出现在官方的宣传品中,甚至还被说成是“一个试图盗取希腊遗产的贼”。1896年雅典奥运会开幕式的正式节目单上就有柯达胶卷的广告,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体育场内有里普顿茶叶的海报,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露天赛场有德士古石油及其他广告……但这些都还只是广种薄收,以至于1977年国际奥委会要求各城市申办1984年奥运会时,得到的反应是令人沮丧的。因为1976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奥运会花费了12.7亿美元,超出预算10几倍,留下了一笔至今仍未还清的债务。
出乎意料的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奥运会商业化的转折点,美国南加州的旅游业商人彼得·尤伯罗斯不仅成功开创了民间筹办奥运会的先例,还为这届奥运会赚取了2.22亿美元的巨额利润,从此各国对申办奥运趋之若鹜。
尤伯罗斯引入了“赞助商”的概念,并在TOP计划中将赞助商提升为发起人。他将发起人的数目限定为30家,开出的底价是400万美元,他强调专营权和垄断权,规定在每一个行业里只选一家企业的排他性原则。日本富士公司以1000万美元中标,甩开竞争对手柯达公司,把其在美国的市场份额由5%提高到了10%。在胶片行业中,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增加1000万美元的收入。
奥运会目前已是世界上最强的品牌之一,国际奥委会在TOP计划中取得的收入从1988年的9500万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5.5亿美元,几乎是每4年翻一番。而电视转播收入从1964年的200万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13.31亿美元。估计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收入将达到14亿美元左右。
商业化是使体育运动适应现代社会的一个最有力的因素。利用商业手段寻求发展,已经成为当代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国际足联秘书长赛普·布拉特说:“只要商业不影响体育的精神、形式、地点和成绩,我们不能阻挡它的发展。”
奥运会的商业化目前还是有节制的,坚持在奥运会比赛场地及其上空不准进行任何形式的广告宣传,使其成为惟一没有商业广告的运动会。但商业化还是开始影响奥运会竞技运动的正常进行,许多比赛的时间安排,不得不应拥有转播权的电视广播公司的要求而调整。
商业化对推广奥运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亿万观众可以在电视中收看奥运会的赛事;会徽、吉祥物等的商业化运作,无形中推广了奥林匹克文化和精神;广告商所推出的奥运明星偶像,让无数青少年为体育而痴迷……可能正是商业化使奥运会更像是一个热热闹闹的超级秀了。
更高、更快、更强
 悉尼奥运会百米飞人之战,美国选手格林和琼斯分别在男女百米决赛中轻松胜出,许多人将此归功于他们特制的跑鞋。在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过程中,含有高科技的“鲨鱼装”、“水晶鞋”、“黄金鞋”层出不穷。体育运动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奥运会成为各国科技水平的展示和竞技。使用兴奋剂将这一追求推向极致,这其中有经济利益的驱动,更反映出人类超越自身极限的企图。
悉尼奥运会百米飞人之战,美国选手格林和琼斯分别在男女百米决赛中轻松胜出,许多人将此归功于他们特制的跑鞋。在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过程中,含有高科技的“鲨鱼装”、“水晶鞋”、“黄金鞋”层出不穷。体育运动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奥运会成为各国科技水平的展示和竞技。使用兴奋剂将这一追求推向极致,这其中有经济利益的驱动,更反映出人类超越自身极限的企图。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奥林匹克运动中使用与反对使用兴奋剂的斗争就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地进行着。国际奥委会兴奋剂检测越来越严,悉尼奥运会首次增加对促红细胞生成素EPO的检测。对违禁者的处罚不断加重,他们将面临4年禁赛,甚至终生禁赛,即使是4年禁赛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与奥运会的永别,因为很少有运动员能够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保持最佳的竞技状态。尽管如今,仍有运动员铤而走险。
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加拿大短跑名将本·约翰逊在男子100米决赛中第一个冲过终点,并打破了世界记录。他兴奋地说:“这个世界记录将保持50年,也许是100年。”可是仅仅过了几个小时,他的胜利就变成了奥运史上最大的丑闻之一。奥林匹克药物控制中心在约翰逊的尿样中发现了国际奥委会明令禁止的药物,他被禁赛两年。1993年,他的尿样又呈阳性,被终身禁赛。约翰逊丑闻之后,有人采访了900个加拿大田径运动员,多数人说即使兴奋剂可能会危害健康,但只要有机会得到提高成绩的药物帮助,他们也会这么做。
参加奥运会是每个运动员的梦想,要获得在奥运赛场上展示自己的瞬间,要经过无数的竞争,一旦获得参赛资格,他们就要表现出最最精彩的一面。许多运动员一生也许只有一次参加奥运会的资格,因为新人、新记录不断出现,而运动员自身的潜力是有限的,毕竟是血肉之躯。这让人想到一句广告词:“更高标准,更多努力,突破极限无止境。”真的是永无止境吗?人类真能超越极限、挣脱生理肉身桎梏吗?兴奋剂是摆脱这一桎梏的尝试吗?
“兴奋剂会完全和运动说再见吗?不会的,绝对不会,兴奋剂的服用永远都存在。”曾任国际奥委会医务委员会主席的梅罗德说。更有生物学家认为,“反兴奋剂运动最终肯定要被击败。我们将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允许运动员自由使用生物科技来改造自己的身体,惟一的限制就是要在安全的医嘱下进行。”也许未来,人类还要进行基因的干预和修补,就像上帝一样。
城市的水泥丛林使人类奔跑跳跃的能力越来越差,日渐臃肿的身躯使运动精神越来越脆弱,也因此我们观看别人在赛场上奔跑跳跃的兴致越来越浓,他们仿佛在为我们奔跑竞技,在呐喊助威声中,蛰伏在内心深处的竞技欲望得以宣泄。我们为超越极限而狂喜,也为在家乡只见过20米长游泳池、奥运会有史以来游得最慢的几内亚选手莫桑巴克而喝彩。我们需要刺激的比赛,更需要内心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