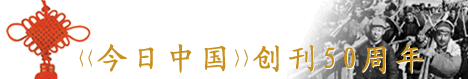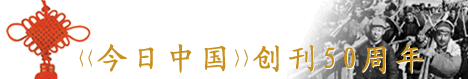赫哲族是中国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其族称源于赫哲人自称的“赫吉色勒”,意即居住在“下游”、“东方”的人们,史籍上有“黑斤”、“赫金”等称谓,新中国成立后,统一定名为“赫哲族”。赫哲族有语言,无文字。解放前因战乱、瘟疫等原因,一度仅剩下300余人,目前赫哲族约有4000多人口,主要居住在黑龙江省的同江、抚远、饶河等地。直到20世纪初,赫哲族仍处于原始公社末期,传统的生产方式以捕鱼为主,兼事打猎。今天,他们已经实现了几个时代的跨越,各项事业的发展基本上与全国同步。
虽已告别黑龙江边的那个村落,但我怎么也忘不了那条亲切的小街、那些质朴的人们、那只木船上飘撒起的鱼网和笑声……

走进赫哲人家
张力
对于中国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赫哲族,我最早是在小学课本上知道的。
秋日里,我终于有机会带上出门采访的那套行囊,登上北去的班机,去寻访世代居住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赫哲族人家。
进村
 汽车在大北疆的旷野中一路奔驰,路边遍开着五彩的扫帚梅,经依兰、佳木斯、富锦,于夜色中驶入北方边陲同江市。次日早起,我们打听到赫哲族最集中的聚居区是在50华里外黑龙江边的街津口乡。在当地同仁的热心带领下,我们沿着平坦的公路急切地赶往这座已让我们感到亲切的乡村。两侧视野中是金黄待收的庄稼,远远就望见了一片村舍,经过横跨在清澈河水上的白色大桥,驶入长约200米的街道,两边排列着邮局、储蓄所、小饭馆、美发店、台球厅,还有一间招牌格外醒目的网吧,这就是街津口乡的主街和中心了。
汽车在大北疆的旷野中一路奔驰,路边遍开着五彩的扫帚梅,经依兰、佳木斯、富锦,于夜色中驶入北方边陲同江市。次日早起,我们打听到赫哲族最集中的聚居区是在50华里外黑龙江边的街津口乡。在当地同仁的热心带领下,我们沿着平坦的公路急切地赶往这座已让我们感到亲切的乡村。两侧视野中是金黄待收的庄稼,远远就望见了一片村舍,经过横跨在清澈河水上的白色大桥,驶入长约200米的街道,两边排列着邮局、储蓄所、小饭馆、美发店、台球厅,还有一间招牌格外醒目的网吧,这就是街津口乡的主街和中心了。
我们下了车,先遇见一位尤大爷,他就是赫哲族人。他拉开木栅栏门,引我们走进自家的小院。一排三间红砖瓦房,蓝窗框上挂着红辣椒,房前房后开满鲜花,旁边有一间小木刻楞(挂鱼的木屋),再往前是一片绿色的菜园。
屋内敞亮洁净,墙上挂满全家老少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尤大爷1952年穿黑色学生装,留分头,坐在美式军用吉普的模型里的留影。他的老伴儿也在家,老两口有二儿二女,都已工作成家,姑爷和儿媳都是汉族人。尤大爷告诉我们,赫哲人与其他民族通婚已很普遍,这也是赫哲族得以重新壮大的原因之一。
民族舞
去赫哲族博物馆的途中,我们意外地看到一个戏台子,一位穿民族服装的中年男子正一边弹奏电子琴,一边指导中学生排练歌舞。他叫吴宝臣,是乡文化站站长。这个魁梧的汉子带着北疆民族特有的豪爽,热情地介绍说,赫哲人历来能歌善舞,过去凡是祭神、庆丰收,或打鱼打猎归来,都会载歌载舞,跳舞的队伍有几百人,走上很远的路。从1985年开始,黑龙江一带的赫哲人又恢复了每四年一次的盛大节日——农历六月二十八的“乌日贡”大会,人们会尽情唱起“依玛堪”(说唱艺术),赞颂驱恶避邪的萨满神。他说,我现在弹唱的曲子都是即兴自编的,得益于自幼父辈们的口传身教。他起身为我们表演了一番皮鼓舞,腰间的几串银铃铛哗哗作响。停下来,他不无遗憾地说,现在江里没有大鳇鱼了,所以鱼皮鼓也改成了鹿皮鼓。我看到他们的服装上有一个明显特征,都绣着美观的波浪花纹,一问才知,那叫“云卷儿”,表达着对蓝天白云和江水浪花的赞美。
老校长
在村民引领下,我们来到乡中心学校的教师新居,见到了退休老校长尤玉镯。老校长夫妇对政府拨专款建的两室一厅带厨卫的大平房十分满意,前后小院也种满了蔬菜、花草。尤校长曾作为赫哲族唯一的代表参加第八届全国人大,在5年中提出多项议案。人们进村前经过的那座大桥,就是议案得到落实的结果。
更让他自豪和欣慰的是,他的家庭是赫哲族绝无仅有的教师之家,全家共有10人当上了人民教师。他和老伴儿是赫哲族第一批高中毕业生,又同在一所学校教书。大女儿教语文和数学,大女婿是现任校长;二女儿教语文;三女儿教美术和社会课,三女婿教体育;大儿子教历史;小儿子教语文,小儿媳负责计算机课。记者在计算机室见到了他的三女儿和小儿媳,在操场上遇见了正在示范托排球的三女婿,在树林边找到了组织学生劳动的小儿子。
毕叔
 出了学校,在街口见一位大叔正凑近我们那辆越野车仔细打量。问他有什么事,他用粗硬的大手握住我的手连声说:“好!好!你们能来边疆看看少数民族太好了!”接着,这位体格强壮、面色红润的毕大叔就自告奋勇地成了我们的向导。他领我们去找这个村最有发言权的老村长,也就是那位吴宝臣站长的父亲。转了几排房也没找见,邻居说他们全家都去地里收土豆了。毕叔不罢休,领我们跑到江边,解开缆绳,跨上一条铁壳小船,打着了马达,招呼我们:“上船,找他去!”
这又是个意外之喜,能够在碧波荡漾的黑龙江上乘坐赫哲人的渔船,对岸就是俄罗斯的下列宁斯科耶,真是相当惬意。江面上凉风习习,我们穿了几件衣服还觉得冷,60多岁的毕叔却只穿一件圆领衫在船尾稳稳地掌舵。毕叔自豪地说:“咱这条铁壳机动船,在整个街津口乡也算是一流的!”他又指着不过10米长的船体各部位风趣地介绍说:这里是宿舍,这是食堂,这是厨房,这是鱼库,这是阳台。
船行至河汊处,毕叔拢起双手冲对岸的坡地上喊:“二哥!”我们担心听不见,毕叔有把握地说,顺风,保证没问题。他还告诉我们,村里的人都是亲套亲,从娘家论,他得管吴老汉叫二哥。不一会儿,坡地后面果然冒出了个人,是吴家二儿子。他系住毕叔甩过去的缆绳,我们跳下船,跟着他穿过没膝的草丛,走上土坡,便看到了在一小块河套地里收土豆、摘豆角的祖孙三代人。
出了学校,在街口见一位大叔正凑近我们那辆越野车仔细打量。问他有什么事,他用粗硬的大手握住我的手连声说:“好!好!你们能来边疆看看少数民族太好了!”接着,这位体格强壮、面色红润的毕大叔就自告奋勇地成了我们的向导。他领我们去找这个村最有发言权的老村长,也就是那位吴宝臣站长的父亲。转了几排房也没找见,邻居说他们全家都去地里收土豆了。毕叔不罢休,领我们跑到江边,解开缆绳,跨上一条铁壳小船,打着了马达,招呼我们:“上船,找他去!”
这又是个意外之喜,能够在碧波荡漾的黑龙江上乘坐赫哲人的渔船,对岸就是俄罗斯的下列宁斯科耶,真是相当惬意。江面上凉风习习,我们穿了几件衣服还觉得冷,60多岁的毕叔却只穿一件圆领衫在船尾稳稳地掌舵。毕叔自豪地说:“咱这条铁壳机动船,在整个街津口乡也算是一流的!”他又指着不过10米长的船体各部位风趣地介绍说:这里是宿舍,这是食堂,这是厨房,这是鱼库,这是阳台。
船行至河汊处,毕叔拢起双手冲对岸的坡地上喊:“二哥!”我们担心听不见,毕叔有把握地说,顺风,保证没问题。他还告诉我们,村里的人都是亲套亲,从娘家论,他得管吴老汉叫二哥。不一会儿,坡地后面果然冒出了个人,是吴家二儿子。他系住毕叔甩过去的缆绳,我们跳下船,跟着他穿过没膝的草丛,走上土坡,便看到了在一小块河套地里收土豆、摘豆角的祖孙三代人。
吴老汉
 我们坐在暖阳照射的地头聊起家常,清新的空气和四周的景色让人格外舒爽。吴老汉说,赫哲人历来能吃苦,不屈服。日本军队当年为了控制这一带,把赫哲人都撵到山里去了,但还是有赫哲人冒死过江参加了苏联红军,还有的参加了抗联。解放后我们得到政府特殊的关怀,各项发展差不多与全国同步。从60年代开始,原来的舢板船和网具得到改进和更新;80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大伙儿有了积极性,我们夫妇俩最先开上了夫妻船,以前赫哲族妇女是绝对不能上船打鱼的;90年代兴起铁壳机动船,近几年江上又出现了承包经营的大游船。1996年,柏油路通到了村里;前年,又通了程控电话,有了闭路电视;听说后面的街津口山还要开辟成国家级森林公园……
我们坐在暖阳照射的地头聊起家常,清新的空气和四周的景色让人格外舒爽。吴老汉说,赫哲人历来能吃苦,不屈服。日本军队当年为了控制这一带,把赫哲人都撵到山里去了,但还是有赫哲人冒死过江参加了苏联红军,还有的参加了抗联。解放后我们得到政府特殊的关怀,各项发展差不多与全国同步。从60年代开始,原来的舢板船和网具得到改进和更新;80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大伙儿有了积极性,我们夫妇俩最先开上了夫妻船,以前赫哲族妇女是绝对不能上船打鱼的;90年代兴起铁壳机动船,近几年江上又出现了承包经营的大游船。1996年,柏油路通到了村里;前年,又通了程控电话,有了闭路电视;听说后面的街津口山还要开辟成国家级森林公园……
作为世代以渔猎为主的赫哲族人,吴老汉说,30年前我一次就在后山遇见上百只狍子,现在连野兔都难见到了。黑龙江水已经被农药、除草剂、化肥和城市污水污染了,加上打鱼的太多,网眼比手指头还细,前些日子我出去10天,才打了15条鱼,要是在早能打回上万斤,100多斤的大鱼都不稀罕。
千百年来赫哲人传统的生产生活资料都直接取自自然,打鱼的网是用树皮内膜撮成的;赫哲人穿的是鱼皮衣裤,外面套狍子皮;船就是家,一靠岸挖个“地窨子”就住下了;连装饰物都是在桦木皮上涂的画。如今,村里多数人家盖上了瓦房,有的还带厨房、卫生间,甚至有浴缸;很多人已由单一的打鱼转为开垦土地、多种经营,年轻一代的赫哲人更是走出村子,到外面去寻求得更大发展。另一方面,即使在年长的赫哲人家,也已经寻觅不到多少民族特征,甚至在他们的箱子里已找不出一件民族服装、乐器或别的东西。在社会进步的同时究竟丢失掉了多少有价值的传统,恐怕现在谁也说不清。
喝“小烧”
太阳偏西的时候,吴老汉夫妇和毕叔决定,用“江水炖江鱼”来款待我们。当下,两条小船载着我们顺江而下。头船由吴老汉掌舵,他老伴盘腿坐在船头;行至江心,只见老太太起身,手脚麻利地开网、撒网。我们这条船纯粹成了观赏船,看落日辉映的江面上老渔翁夫唱妇随,煞是动人。头船在江上划出一道银亮的弧线,又兜回来起网、收网,待靠拢我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忙着从网上摘鱼了。鱼都不大,共有半桶,数一数,竟有9个品种。
小船泊靠在岩壁下的滩涂上,大伙儿燃起篝火,吃起了“塔拉哈”(柳条穿的烤整鱼片)、土豆丝拌生鱼,更有赫哲人待贵客的江水炖江鱼,盛着自酿“小烧”的瓷碗频频碰撞在一起。
送行
 辞别的那天,毕叔早晨5点就在我们投宿的家庭旅店外面等着为我们送行了。头天晚上,毕叔一高兴多喝了几杯“小烧”,早起时竟觉得有点头晕,又喝了三两,才算解了酒。
辞别的那天,毕叔早晨5点就在我们投宿的家庭旅店外面等着为我们送行了。头天晚上,毕叔一高兴多喝了几杯“小烧”,早起时竟觉得有点头晕,又喝了三两,才算解了酒。
一脸富态像的旅店尤老板和他那位勤快的媳妇也早早起来了,让我们饱饱地吃了一顿苞米面粥、大饼和自家腌的咸菜之后,领我们到他家新开的120平方米的“赫哲族歌舞餐厅”,打开了价值3000多元的家庭影院。毕叔换上全乡最讲究的那套民族“礼服”(正是老校长去北京开人大会议时穿的),郑重地握住话筒说:“请允许我为远方来的朋友献上几首歌。”他高声唱起《北京颂歌》,字正腔圆。接着唱了《雄伟的天安门》,然后是深沉悠扬的《草原之夜》。我们正沉醉于歌声中,突然停电了,而毕叔并不受干扰,继续从容唱完了这首据说是当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战士自编自唱的经典歌曲。
不知是眼前的氛围还是歌中的意境感染了我们,大伙儿一时相对无语。还是毕叔豪爽,笑着大声说:“现在太方便了,有空我坐飞机看你们去!”
是的,分别就意味着下一次的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