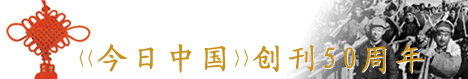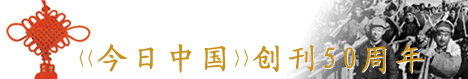元元:关注百姓 关注生活
张娟
义不容辞地把百姓的意见和建议带到党代会上去——党代表元元
世上没有黄金时间,只有黄金栏目——主持人元元
以市井新闻为卖点却如此卓而不群,也就如此地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业界评价元元主持的节目
最早注意元元,是受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的影响:每周日上午学完画,会雷打不动地速速回家——要不就赶不上看《第七日》了!原以为吸引他的是一档精彩的动画节目,后来才发现是一个并不十分美丽的女孩子带着一种外冷内热的劲儿有滋有味地“说”新闻。儿子说“元元姐姐倍儿酷,说话特有意思,我们同学都喜欢看《第七日》!”有这么“铁杆”的“年轻”观众,《第七日》成为北京电视台的名牌栏目、收视率最高达到11.9%,创下了非黄金时段的最高记录也就不足为奇了。而被观众称为“仗义直言的刺丫头”的元元从每周一次的《第七日》到现在每天在《七日七频道》栏目与观众见面也同样顺理成章。
八年如一日 元元在说话
 |
| 元元在《七日七频道》工作室。 |
元元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语言去感悟生活,很多电视观众说听元元说话是一种享受。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经过元元的点评立马变得有味道起来。对此,元元有自已的理解:“有人说我们的节目说得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承认,生活嘛,就是由一件件的小事组成。事儿俗,但观点不能俗,视角是百姓的,观点就不能再是世俗水平,这就靠功力。”
元元姓刘,名字就叫元元,她说自己在大学里学的是德语,至今做主持人已有8年了。——一个非“科班”出身的人在竞争激烈的主持人行当里打拼并能辟得一席之地,该有怎样独到的功力?
讲起自己的“成长过程”,元元说是“命好”:1994年进北京电视台,做记者跑新闻,1995年,创办新闻评论节目《点点工作室》,用同仁的话讲“元元开始崭露头角”,这个栏目成为北京电视台一档颇有影响的栏目。1998年创办《元元说话》,元元说,用主持人的名字包装节目,得看主持人能不能真正成为节目的灵魂,体现这个节目的定位,而这给她带来的压力也可想而知,她引用了当时电视台一位老记者的话——“只有这样的小毛丫头才这么不怕送死。”1999年,台里节目调整,《第七日》竞标成功,定位是一周新闻综述加评点。元元说,刚开始做《第七日》时,忽然有一种“小马拉大车”的感觉,一周里的重大新闻太多了,而且这些事又都是大家知道的、关心的,栏目必须突破的点是新闻的再传播,要在“再”上去拓展空间,好多东西报过一遍,但下落如何,延伸的细节如何,新闻背景如何,这些都成为他们再挖掘的内容,再加上自己独特的视角和观察,做成具有独家风格的东西。事实证明,做得还不错,很受观众欢迎。今年新增了《七日七频道》,栏目有一个响亮的口号:“七七四十九,想看天天有。”元元说,“一提起生活,人们一般想到的就是衣食住行,有点琐碎,也有点麻木。其实生活中有很多事情值得细细品味,我们要透过生活的百态去挖掘事件背后的人物内心世界,从而对人们的生活观念和态度起到引导作用。”她说,8年来她和她的同事们一点点地做起,从一事一议到新闻综述加点评,从一个节目到一个栏目,一路过来,效果还算令人满意,她觉得自己是在进步,节目也在与时俱进,但有一点不变的是,他们始终将百姓生活作为关注的焦点。
元元的节目以小见大,从《七日七频道》春节特别节目“生活在变”中可以略见一斑。元元以“多”和“少”对比,从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真实记录一年里百姓生活的变化,而我们也能从中体会到“元元风格”。
买房的人多,房子的问题不少
买彩票的多,中大奖的少
孩子上学接送的多,自己来回上下学的少
自行车防盗的办法多了,丢车的还是没见少
节水的措施多了,浪费水的现象也不少
送给老人的礼物多了,能陪他们在家聊聊的少了
过节出门旅游的多了,在家呆着的少了
街头体育设施多了,锻炼的年轻人少了
用手机的多了,用呼机的少了
学英语的多,敢张嘴说的少
网恋多了,和爱人的话少了
挣得钱多了,睡眠和锻炼的时间少了
用电脑打字的多了,字写得好的少了
离婚的多了,早婚的少了
电视速配的多了,父母包办的少了
家里烧气儿的多了,烧煤的少了
大人出国的少了,孩子们出国的倒是多了
炒股的多了,赚大钱的没见着多
中介服务种类多了,上当受骗的不少
大公交多了,小公共少了
喝桶装水的人多了,喝自来水的人少了
美容的多,毁容的也不少
规范执法的多了,乱收费的少了
吃冬贮大白菜的少了,吃特菜的多了
荧屏上帅哥靓妹多了,能让我记住的少了
古装戏多了,现代剧少了,公安剧多了,农村戏少了
明星投身公益的多了,总想着挣钱的也不少
华人进军好莱坞的多了,国产影片获奖的少了
歌星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多了,场面火的少了
……
把观众当回事儿
 |
| 在校园里采访大学生。 |
元元说她想做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而不是屏幕前念念稿子的那一种,从开始担任节目主持人的那天起,她一直同时兼任制片人,参与从节目策划、制作乃至推广经营的每一个环节,始终是节目组的灵魂和核心。元元告诉我,每次播出的稿件,大部分出自她的手,有的稿件由主笔撰稿,她再按自己的风格加以修改,补充观点。“现在忙得一塌糊涂,单写稿子就压得我喘不过气,说实话,有时真是强努着,”元元说,一直以来栏目就想物色一个写稿子的人,但还没有找到特合适的。录制节目的摄影棚,没有字幕提示一类的东西,她必须将稿子一字不差流利地背出来。虽然是自己写的,但十几分钟、几十分钟的节目还是得花好几个钟头录制,有时出了摄影棚,腰都直不起来了。
电视里的元元似乎永远有说不完的话,那些让观众听来很“各色”却又容易让人认同的“理儿”,也好像信手拈来,元元说,其实哪里有那么容易,有时看似简单的几句话“半宿半宿睡不着觉才琢磨出来”。元元说,不夸张地讲,她和同事们每天都在接受考验:如果选择大家都不了解的领域,那节目做起来反倒容易,而她们的节目和普通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相同的事情如何从中找到新的角度,真得下大功夫才行。
元元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自己的节目能得到观众的满意和认可,这是自己工作的终极目的,也是安身立命之本。本着这个最朴素的出发点,元元说,自从担任主持人那天起,就不敢掉以轻心,在2001年底获得全国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金话筒奖后,元元曾向观众坦陈心迹:“我知道观众对我的期待,这种期待让我一刻不停地向前跑;这种期待让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有所顾忌,或许永远都无法潇洒人生。别说停一停,歇一歇,等一等了,就连出趟远门都得跟观众‘请假’。”了解元元的人都说她是工作狂,元元没有否认,她说,对观众的珍视,是支撑她全力投身工作的动力。她最高兴的事儿是观众的事情通过节目得到解决,但也有许多时候很无奈:“观众对我的期望太高,有时候帮不上忙,我觉得心里挺不踏实的。老百姓有时没法讲理去,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说实话,这是一个误解,我们是传播新闻的,不是解决问题的职能部门,电话打过来,我说这事我们管不了,他说你凭什么管不了,你干嘛的?管不了还天天在那儿说什么?”元元说委屈过后,还是“检讨”和鼓励自己:更努力地做好“喉舌”工作!
把“民声”带上党代会
今年5月,在北京市第九届党代会上,元元成了记者同行追逐采访的对象,原来她此次不是去采访,而是以一名党代表的身份出席本次大会。元元说参加会的代表,基本上都是揣着市民的意见和建议来的,凭借热线电话的优势,她自己可以算是收集百姓声音最多的代表之一,她义不容辞地将这些声音带到会上来了。
房子、车子和孩子--元元说现在这可以说是百姓生活中最关心的“新三大件”,“可是这几方面都挺让人头疼的,我们接到的相关投诉和建议也就最集中。”拿物业管理来说,这是一个新兴行业,相关机制还不够健全,居民与物业公司之间出现不少纠纷。很多百姓都强烈呼吁政府有关部门能够加强对这一行业的规范管理。在大会小组发言的时候,元元代表还讲了自己的一个新发现,也是几年来自己制作节目过程中的深切感受:“从市民给我们节目打电话反映问题的内容,就能看出我们的生活质量跟前两年真不是一个档次了。比方说,以前我们接到的热线,净是反映什么水管不通了,出事没人管了,多是一些生活物质保障方面的问题。但现在再看,市民关心的不再仅仅是吃、穿、住这些硬件条件,还包括很多生活观念与理念的东西,这是最大的一个变化。”元元说,现在的百姓更关注自身的权益和生活质量,以反假出名的王海大行其道、“一元钱官司”在法庭上闹得沸沸扬扬、街道大妈会为噪音污染给电视台打来热线电话……这些都是最好的例证。
元元表示,自己是第一次以党代表的身份参加这种高规格的大会,除了记者本身具备的兴奋感外,还有一种“提高认识”的感觉,更增强了自己作为新闻工作者的强烈责任感。三句话不离本行,元元代表时刻不会忘记她的栏目——北京党代会《报告》中提到北京“人均GDP6000美元”、“人均住房20平方米”等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都是很值得关注的“新闻亮点”。
作为一档关注国计民生的栏目,为迎接党的十六大的召开,元元说栏目正在筹备二个系列节目,一是“把青春献给党”,主要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子承父业”的老前辈、老劳模、老艺术家的后代,比如作曲家雷振邦的女儿雷蕾、比如北京市百货大楼优秀售货员张秉贵的儿子等;另一个系列是“为官之道”,想选取不同领域的十个干部,通过他们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幸福兢兢业业工作的“为官之道”,反映出怎样才是百姓心目中的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