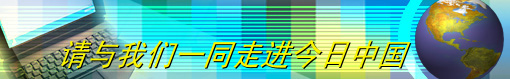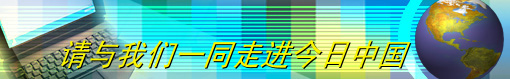中国制造
文/ 少君 (美国)
离开故土漂泊了十多年,每次回国都为带什么东西而发愁。早年这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事情,因为任何的泊来品,乃至几大件免税的电器,都会给亲友带来无限的欢愉。但这几年“MADE
IN CHINA”东西充满了美国的各种商场,上次很认真地买了一个很高档的尼康数码相机,在上海送给朋友做生日礼物,没想到在生日PARTY上打开包装盒后,原来还是“MADE
IN CHINA”。好像在美国已很难找出什么不是中国制造的礼品了。我每次只能跟亲友这样解释:如果你从我给你带回的礼物上发现印有“MADE
IN CHINA”这样的标签时,你千万不要惊奇,因为如今“中国制造”的商品已经“占领”了美国。 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从廉价店里的生活用品,到尼门马克斯的高档服装,还有那几乎百分之百的电视机和DVD,几乎都是“中国制造”,你甚至可以在国会山的众议员和参议员们的办公室里发现许多“MADE
IN CHINA”的文具与礼品。这一切,不但让我们,甚至也让土生美国人看到了巨大的中国在成长。现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已离不开“中国制造”了。
 |
| 作者近影 |
《远东经济评论》曾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欧洲的飞利浦公司上世纪八十年代投资上海,是想绕过关税壁垒向10亿中国人贩卖他们的电子产品,戏剧性的结果是,他们发现在中国生产的飞利浦产品并输向全球更有利可图,如今他们每年50亿美元产品有2/3从中国出口到其他地方,
在我刚到美国读书的时候,在大多数美国人眼里对中国的了解,还只是中国菜,CHINATOWN,矮矮的黄皮肤的说着稀奇古怪语言的亚洲人,一个遥远神秘的原始国度。但中国对我们这些留学生来讲,她曾经是我们生命的全部,我们在那里生,在那里长,在那里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从而了解了世界,赤手空拳地来到这个对我们同样陌生的国度。美国有许多像我这样的留学生,过去每天在自己的国家,从来不觉得皮肤、眼睛有什么特别,可到了外边,每天都会有不同的肤色的人走到我们面前,用他们的皮肤颜色具体地提醒我们:你,皮肤是黄的,眼睛是黑的。我们努力地学习着,适应着,企图了解融入这个新的世界。但对祖国的怀恋却永远无法消失在这个融入的过程。
从来不敢标榜自己多么有民族感,多么爱国,“爱国”这个词多数时候是用来自我调侃的。可到了海外,我发现原来我是很在意的,我在意我的肤色,我的属性。因为不管我走多远,走多久,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醒目地烙着“MADE
IN CHINA”,中国的一切都以不同的形式滑过我的身体,沉淀成今天的我,我做出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纵然我吸收了西方的许多文化精髓,但用的“吸管”也照样是中国式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感觉还时常缠绕着我,通过文字,我可以随时把“中国”由指间释放出来。
记得上一次离别北京的时候,我在宾馆大厅,听到一首熟悉的二胡曲《送别》,随着二胡开弦时的那一声“吱呀”,我不禁热泪盈眶,怕人瞧见,忙低下身子假装系鞋带。要走了,就有这首曲子来送我,一首普通的二胡曲把我的心绪演绎得那么伤感。
匆匆的行人在身边走过,没人驻足,这首曲子打动不了他们,因为他们没有漂泊过。
其实,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海外的人,对故国的怀念也许常常就是想吃一碗炸酱面,或者是在啃面包时特怀念六必居的酱油咸菜。因为故宫、颐和园、全聚德、沙锅居那就是我整个童年的记忆交响曲。在我看来,空阔的天坛公园就是那前奏曲,故宫和四合院是深沉的主旋律;颐和园和什刹海那美丽的湖水,就是单簧管和长笛吹出的奏鸣曲。不管我们走多远,灵魂中永远响的是这首思乡的曲子。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常常望月沉思:我们为什么来到美国?
美国是个高度发达的国度,飞机、汽车、计算机……几乎所有的现代科学技术都发生发展于此,它带有很传奇的现代化色彩,好莱坞又为它增添了一层浪漫,于是美国便以一个人间天堂的模样进入了我们的脑海。20世纪八十年代国内有一首歌唱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我们正是向往着这精彩踏上了这块土地,企盼着人间奇迹发生在我们眼前,那时真的不懂什么叫无奈。于是我们来了,带着一颗充满热望的心来了。十几年便在转眼间过去,我们站住了,找到了我们可以生存的那点空间,同时,我们也得到了一个认知,故乡永远是故土,无论你生活在天堂还是地狱。
韩少功在《读者生命,有一种硬度》中曾写道:“人可以另外选择居住地,但没法选择生命之源,即使这里有许多你无法忍受的东西,即使这块土地曾经被太多的人口和灾难压榨得疲惫不堪,气喘吁吁。你没法重新选择父辈,他们的脸上隐藏着你的容貌,身上散发出你熟悉的气息。也许更重要的是,这里到处隐伏和流动着你的中文,你的心灵之血。如果你曾经用这种语言说过最动情的心事,最欢乐的和最辛酸的体验,最聪明和最幼稚的见解,你就再也不可能与它分离。”
经历了种种欢乐和痛苦,我们用青春换来的只是一个生存的空间,而我们也许失掉更多。母亲从六十岁变成了七十岁,父亲从黑发变成了白发,这十年我们对他们是空白,他们对我们也同样,而且或许将是从那时至永远的空白。我曾在给我的学生讲课时说过:到美国留学定居,于我来说,是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这不是冠冕堂皇的说教,是一种真实的感受。
于是,当生存问题不再是生活中主要压力的时候,就忍不住老想回国。因为那是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天地。每次回来,又看见了那不太蓝的天空,又看见了拥挤嘈杂的人群,但却没有了厌倦,只有亲切,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多人,而且是越来越漂亮的中国人了。爱国常常被说成是一种情操,一种牺牲。其实都不是,而是一种精神上的需求与寄托。
对于这种来来往往的生活,不但朋友同事不理解,而且生长在美国的老婆孩子也无法理解。终于有一天,在我即将又一次起程回国时,女儿郑重地在我的行李箱上,用彩笔写下了一个大大的“WHY”
?,望着她双那困惑的眼睛,我轻轻地对她说:因为我是中国制造的。
少君小传:经济学博士。曾就读于中国北京大学声学物理专业,美国德州大学经济学专业。曾任中国《经济日报》记者,美国匹兹堡大学研究员,美国TII公司副董事长。现兼任中国厦门大学、华侨大学、
同济大学等数所大学的客座教授。
近年主要出版的著作有《现代启示录》、《西部报告》、《未名湖》、《人生自白》、《奋斗与平等》等,是现今华文创作文坛上知名的网络文学作家。1998年《世界华文文学》杂志将其选为年度封面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