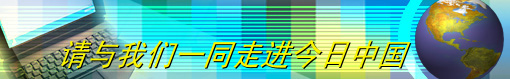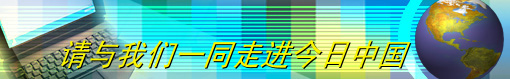为了免除更多人的痛苦
——访疼痛医学专家赵英博士
文/王 磊
人吃五谷杂粮,伤病在所难免。大多数伤病都会让病人产生疼痛感,有些病甚至在治愈后仍不能消除。这个时候,许多被疼痛折磨的人便不知道该去医院的哪个部门去寻求帮助。北京、广州等地的医院专门开设的“疼痛门诊”,为此类病人求医指点了迷津。卫生部北京医院的疼痛门诊是目前国内康复医学界组建的第一个疼痛门诊,它的创建者,便是从日本留学归国的疼痛学专家赵英。
坚实的医学基础
 |
| 赵英在北京医院疼痛门诊为患者治疗 |
1979年,赵英考入了白求恩医科大学医疗系。回忆起在大学的五年时光,赵英依然十分怀念:“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珍惜难得的机会,学习都很刻苦。而且,当时每一个大学生的心中都有一个远大的理想,都把自己的未来与整个国家的发展联系起来,真心实意地想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浓厚的学习氛围中,赵英不断地在医学的海洋里充实自己。在大学的几年里,赵英广泛涉猎了医学的各个门类,利用大量的时间在图书馆里翻阅了无数本介绍当时医学前沿领域的书籍,包括不列入考试范围的“课余内容”。虽然年青的她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知识对她选择日后道路有何影响,但是对科学的敏感使她本能地认识到这些知识的重要性。
从大学毕业后,赵英做过麻醉科大夫、西医诊断教研室的助教、针灸骨伤系的讲师,还曾经专门脱产学习过中医,接着又做了实验针灸教研室的讲师。这种不连贯的专业背景,从西医到中医,又回到西医的跳跃,对于许多从医的人来说都是要尽量避免的。然而赵英却与众不同,每次要转变学科背景的时候,她总是庆幸为自己未来的从医之路又铺垫了新的基石。
日本留学的日子
 |
| 赵英在日本东北大学麻醉刻科做客座研究员是与导师桥本保彦(右一)和导师兼子忠延合影 |
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是日本国内比较有名的医学院,尤其是它的麻醉科,在日本的医学界更是鼎鼎有名。1990年7月,赵英以自费公派的形式,客座研究员的身份到这所大学医学部麻醉科,攻读博士学位。
赵英的博士生导师桥本保彦是一位热心而又仔细的人,在详细询问了赵英的意愿后,他把赵英安排在了疼痛门诊部门学习。此时日本医学界对疼痛原理和治疗的研究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有相当的理论积淀和成型的治疗手段,最成功的病历就是治愈了前首相田中角荣的颜面神经麻痹。
桥本教授之所以把赵英安排到疼痛门诊,除了基于赵英在中国的医学背景外,更重要的是他对赵英的针灸水平极具信心。这一时期,在日本医学界流行一部反映中国医生利用中医传统的针灸方法实施手术麻醉的教学记录片,日本医生对此充满了好奇,而桥本教授与赵英则敏锐地认识到针灸也许会对治疗一些顽固性疼痛产生显著的功效。
凭借在国内打下的坚实基础,赵英很快就“露了一手”,用小小的银针缓解了许多颜面神经麻痹和腰腿疼病人的病痛。赵英的同事们也纷纷开始向她学习针灸技术。初露锋芒后,赵英对疼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在导师的指导下系统地学习镇痛的方法与原理。她所接触的第一本疼痛治疗专业书是若山文吉著的《神经阻滞法》,至今仍然爱不释手。
1994年,赵英获得了博士学位,此后她又留在疼痛门诊工作了2年。在这期间,赵英利用神经阻滞方法进行了5000多次治疗,为许多病人解除了痛苦。在长期的治疗慢性疼痛患者的过程中,赵英对各种病症有了深刻的认识,并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逐渐地,赵英在疼痛门诊闯出了一定的名气,许多病人慕名前来就诊。有一位来自日本山形县的70多岁的老太太,一生勤俭辛苦,在当地很有名望。然而长久的慢性疼痛却让她的生活充满了痛苦。赵英利用自己独特的神经阻滞与针灸的方法有效地缓解了老人的疼痛。从此老人便定期来找赵英就诊,有的时候甚至只是来与赵英聊聊天,她说这样似乎也能缓解一点病痛。赵英回忆起这位可爱的老人时,满怀笑意:“我回国了以后,老太太还特意到北京来看过我,她对自己的孩子说,我要到中国去看看我的‘女儿’”。
为了疼痛医学而奔走
在联络赵英做采访的过程中,感觉她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人,不断地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最终,记者的采访也是紧跟在一个医学研讨会之后展开的。赵英所忙的,是疼痛医学在中国的发展。
1996年,学有所成的赵英从日本回到了中国,进入北京医科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成为韩济生院士的学生。韩先生曾经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专门研究针灸镇痛的原理,他的许多理论为中国疼痛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韩济生院士的指导下,赵英选择了慢性疼痛治疗作为今后临床研究方向的开始。
这个时候,在国际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开始把“疼痛”作为一种专门的对象来研究和治疗。,国际疼痛研究协会(IASP)对疼痛的定义是:疼痛是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和情绪上的感受,伴随着现存的或潜在的组织损伤。最近,美国将疼痛列为与呼吸、体温、血压、脉搏并列的第五生命体征。
与一般的临床科室不同,疼痛门诊的特点是病种复杂,只要是有疼痛症状的,都可以到这里挂号就诊。赵英向记者介绍,目前疼痛的治疗以神经阻滞为主,辅以电刺激、针灸和心理治疗。治疗的目的,是让病人减少疼痛,而最根本的是“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
在她众多的病人中,一个患有带状疱疹的老人最让赵英记挂。今年89岁的老人一年多以前患了带状疱疹。由于这种病会对人的神经造成损害,因此老人虽然及时治好了属于皮肤科治疗范围的疱疹,但是却留下了后颈部神经痛的症状。这种疼痛发展到最后,老人只能每天采取跪姿休息,根本不能躺下。当他第一次来到赵英面前的时候,老人已被疼痛和失眠折磨得十分憔悴,甚至对子女说自己一辈子没有受过这个罪,“再也不想活了”。
赵英认真地为老人诊断了病情,详细制订了治疗方案。经过一次治疗后,老人当天睡了三个小时,经过两个疗程(二十次)的治疗后,老人已经能够正常休息、饮食,很快就出院了。“像这样的病人我接触了很多,由于表面的症状已经消失,因此病人再告诉别人自己的疼痛时,总是不被理解。治疗这样的病人,除了物理、化学的方法,还需要在心理上支持病人。”
在介绍中国的疼痛医学所面临的任务时,赵英熟稔地报出来这样几组数据:目前中国的慢性疼痛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大于60岁的老人中发病率高达65%—80%,在普通人群中也有35%。由于长时期的疼痛困扰,许多人的生活质量明显下降,患者不仅要应付巨额治疗经费的支出,甚至有人选择了放弃生命。
实际上,通过疼痛门诊的治疗,90%的慢性疼痛是可以缓解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疼痛可以预防!”赵英很是兴奋地对记者介绍自己工作的意义。然而当记者询问目前中国疼痛医学的发展状况时,赵英表示出了自己的担心。目前中国从事疼痛研究与治疗的机构依然不多,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合力”。
如今,赵英在疼痛医学上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她在国内康复学科里第一个设立了疼痛门诊;“慢性疼痛治疗神经阻滞技术的推广应用”已经获准列入“卫生部十年百项成果推广计划”,根据该计划,赵英正在研究的神经阻滞技术将向全国医疗系统推广;北京医院的疼痛诊治中心的筹建也在酝酿之中。同时,赵英对疼痛医学的研究已经获得了医学界的认可。目前她是北京康复医学会疼痛学分会的会长、中国医师学会康复学分会的理事。不过,对赵英来说,所有的成绩与声誉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每天出现在诊室门口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
2002年9月,赵英应邀再次到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进行学术交流。赵英感到具有近40年历史的日本疼痛门诊,在治疗对象、治疗手法上逐渐发生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不久的将来,会对中国的疼痛学科、康复医学科产生巨大的冲击。”面对这种冲击,赵英既感到兴奋,也多少有几丝怅然。兴奋的是这些新的治疗方法将极大地提高中国疼痛学的发展,惆怅的是何时中国的疼痛医学研究能在世界有显著的地位。
无论是兴奋还是惆怅,赵英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热爱。对于疼痛医学的重要性,赵英如是说:“疼痛目前是一个国家主要的健康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健康形象、国民身体素质的公共卫生问题。而从根本上说没有健康就谈不上小康,因此,对疼痛的认识和治疗,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文明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