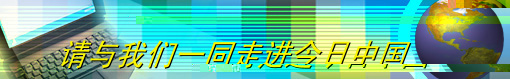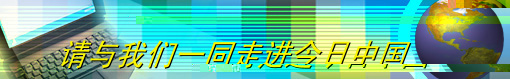生死相隔未了情
岑献青
 |
| 这就我的父亲母亲 |
妹妹从老家打来电话,说是天热了,妈妈找不到空调的遥控器,就哭了,因为往年天一热,老头就把电风扇、空调都擦洗干净,把遥控器准备好,今年老头不在了,她都不知道上哪儿找遥控器。
听着这话,泪水就掉下来,父亲走了,母亲的生命之水就一点一点地干涸了,生命之树也一点一点地枯萎了……
把两个人的铺盖搬到一起,就算完成人生第一大的事情了
母亲尽管来自乡村,却长得眉清目秀,因为读了几年书,比当时的农村女孩子多了一份少见的淑女气质。
据说当年追求母亲的人不少,但母亲几乎不为所动,以致有人暗地里嘀咕,这人是不是个“石女”啊?
父亲早年曾经读过师范,但没有毕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和几个同学一起离开学校,参加了粤桂边纵队。后来他常常回忆说,那天,几个人在翻越一座山头时曾经约定,革命胜利后,一定要带着自己的儿女来这里,给他们讲述当年父辈的革命历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但是革命胜利后,建设的工作更为繁忙,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机会得知,当年那几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是在哪个山头上指点江山的。
无论是以现在还是当时的标准,父亲都算不上那种能让人一见就倾心的人,但母亲就是把自己的一生放心地交给了他。其实不需要什么理由,看看父亲双眼里流露出来的自信、执著、果断以及宽容,就会理解母亲的选择。
当然,更多的理由其实在父亲的相貌之外。父亲1949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经只身携带情报进入敌占区;也曾经作为指挥员指挥了多次剿匪战斗;22岁就任广西崇左县太平镇的镇长,26岁担任县团委书记;当他成为县检察院副院长时,才28岁。在当年的剿匪、土改等等工作中,父亲与当地的百姓建立了极好的关系,连乡下不识字的老人听说父亲的名字,也会翘起拇指说:哎呀,他真是能干,在群众大会上说几个小时的话都不用稿子哩!
如果一个男人能对自己所向往的事业倾注全部的激情,奉献全部的精力乃至生命,而这个事业又是取信于民、造福于民的,那么,这个男人还不值得有着同样理想的女人去信任、去爱吗?
所以,没有什么卿卿我我,没有什么花前月下,曾经勇敢地反抗了家庭封建包办婚姻的母亲很自然地被父亲吸引了。
“大家说,该结婚了吧,就把两个人的铺盖搬到一起,就算完成人生第一大的事情了。”母亲说。
父亲就像一根坚固的绳索,拴紧了我们这个犹如浪中小舟的家
1955年8月,父亲在中南政法学院学习,转年的春节回家,与母亲一起,抱着我照了这张相,那时我还不满一岁。
从前看这张照片,心里有一种陌生的感觉。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几乎没有和父亲一起玩过,好像父亲从来就没有牵过我的手高高兴兴地走在街上,更不要说把我高高地驮在肩上了。
母亲却总是说,父亲在武汉学习时,给你买了一条花裙子。
又说,你看看这相片,父亲把你抱得那么紧,像是怕你摔坏了似的。
但那时,我就像一个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丝毫体会不出母亲这些话的用意。
后来,读了大学,只身一人到了北京,寂寞时,关于父亲的点点滴滴却常常地出现了。很小的时候,父亲经常外出开会,几乎每次归来,我们都会得到一只葫芦形的玻璃瓶,里面装有数十粒花花绿绿的糖豆。有一次,父亲带回来的是普通的小圆瓶,他很歉疚地说,那家小店拆了。父亲不知道,那小圆瓶里装满了肥皂水,用蕨杆杆一吹,五彩的泡泡给了我们许多欢乐呐。
“文革”中,父亲被造反派抓到煤仓当人质,晚上就让他睡在二尺来宽的传送带上,身下是几十米深的、往火车上装煤的大漏斗,稍不小心,就会跌下去,生死不测。我去给他送饭,冒着冷汗,战战兢兢地走在煤仓的边上,父亲哈哈笑说,回去告诉妈妈,这里挺好,没有蚊子。可第二天却让人带话来,不让我再去那样危险的地方。
1977年,我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当时父亲已离家在另一个地方工作,听说我拿到了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匆匆赶回家来住了一夜,这次回家,父亲留给我两句话,一句是“要学哲学”,另一句还是“要学哲学”。
在后来的许多年里,我才慢慢地体会到父亲留给我的是一份多么珍贵的人生经验!
母亲总是不断地强调,父亲其实是很疼你们的,可你们都不理解他。他的压力有多大,你们知道吗?如果没有父亲,我早就命归黄泉,这个家,早就没有了!
母亲说的是1957年她被打成右派的事。如果那时不是因为有身孕,她还要受牢狱之灾。她担心连累父亲,想离婚,又承受不了巨大的政治压力,想投水一死了之。
但父亲没有离开她。父亲就像一根坚固的绳索,拴紧了我们这个犹如浪中小舟的家。
哦,父亲,没有您,我们便没有母亲,没有这个家。您的爱,是通过母亲传送给我们的。
是啊,以前我们真的是不理解父亲,但后来我们长大了,经历了世事,也为人父母了,我们就深深地理解了我们的父亲母亲了。
在父亲离世后,重新翻看这张照片,有一种深沉的来自骨血的情感溢满身心……
哪个九十九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
 |
| 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初,父亲和母亲都离休和退休了 |
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初,父亲和母亲都离休和退休了。
于是就有了许多闲暇的时间。母亲只是终日地忙,忙家人的一日三餐。父亲则在兴致勃勃地经营着阳台上那几盆很大众化的花草,有时,也随了母亲到市场采购菜蔬。
家庭的温馨日日地浓郁起来,安静、平和,再不是从前老也见不到父亲的日子。老两口天天在一起,每天做的事情几乎都是相同的。凌晨四点多钟,父亲就起来了,把头天全家人换下的衣服放进洗衣机,然后去煮早餐,然后再睡一个回笼觉。起床后,吃点东西,然后从洗衣机里拿出洗净的衣物,和母亲一起,在阳台上晾衣服。
母亲把衣服撑在衣架上,父亲用晾衣竿把衣架高高地挂到铁丝上。
这成了我们家阳台上一成不变的风景。
母亲说,哎呀,俩老天天在一起晒衣服,习惯了,万一有一天谁走了,剩下一个怎么办?
父亲说,肯定是会有这一天的哦,那就一个人自己晒衣服呗。
哈哈一笑,又说,不过最好是我先走,你晚点走。我到奈何桥上等你三年。
壮族的歌仙刘三姐有这样一首歌:连就连,你我同心连百年,哪个九十九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
母亲就笑,你要先走了,我也不会呆太久。
父亲就说,是啊是啊,你也不要呆太久,人老了,独自呆着的日子不太好过哦。
于是,两个老人相视而大笑。
1984年,我回到父母身边生孩子,儿子出生后,为这个家添了许多欢乐和麻烦。母亲天天洗尿布,却总是眉开眼笑。父亲每天清晨第一件事就是来逗那小家伙,直到那小家伙将一泡尿如水枪似地淋湿他的衣服。
母亲说,你爸爸从不知道自己的几个孩子是怎么长大的,现在老了,倒有机会看小外孙如何一天变一个样了。
我问父亲:您遗憾吗?
父亲笑笑:哦,是有点遗憾呢。
1992年,我把父亲母亲接到北京住了一段。其时我的境况非常窘迫,只有一室一厅,但父母亲还是很高兴,因为他们知道,我曾经住过地下室、住过有如鸽子笼一般的房间、住过逼仄的筒子楼,现在的状况在他们看来,已经是大有进步了。
这张照片就是那年在北京大学的桃园里照的。在绿叶红桃中,我的父亲母亲就像一对快乐儿童。
现在,这个桃园已经消失了,代之以一片绿草地。
虽是生死两相隔,
这一份情缘却依旧相连
2003年11月,我赶回家,父亲做了一个很大的肝部手术,主刀医生向我和妹妹展示了那个丑陋的拳头大的肿瘤。我们都以为父亲要过不去了,结果医院说那是个良性肿瘤,而且父亲恢复很好,让我们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有一天我独自在病房陪他,他对我交代了种种后事,然后笑说,活了将近八十岁了,一生坎坷,但也一生坦荡,并且因此一生豁达乐观。而且,比起很多人来,还享受了日新月异的生活,所以,走了也就走了,没有什么遗憾的。
出院了,他却变得十分留恋起生命来。母亲说,有时,他会在阳台上坐着,望望远处的那棵苦楝树,说:“发芽了呢,春天真是来了。”
偶尔母亲陪他出门走走,在路旁榕树下的石凳上坐着休息,看路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他会感慨地说:“这个世界还是美好的啊。”
春节期间,父亲的精神挺好,家人建议他出门走走,他竟然也高兴地同意了。出门前,母亲为他细心地戴上帽子,围上围巾,然后用手摸了摸父亲的脸。父亲母亲一生的情缘永远凝固在了这张照片上。
如果没有什么变化,今年的春夏我们会有一系列的活动的。我和母亲今年的生日刚巧同在一天,我将要从北京回去,与母亲过一个“百年不遇”的奇特的生日,然后呼亲唤友,为父母举办一个盛大的金婚典礼,再然后,已近半百的女儿我,将领着年迈的父母北上,让他们在我新买的房子里住上一段时间。
谁也没有想到,春节刚过,父亲就被查出淋巴癌,很快就住进了医院,只有短短的17天,父亲便离开了人世。
我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母亲说,父亲走得很平静。起初,他还费力地举起手,比比划划地说着什么。后来,父亲渐渐陷入昏迷中。母亲时不时地拍拍他,唤他:“老头,老头,听得见么?”父亲很努力地睁开眼,朝母亲看看,嘴动了动,发不出声音。但他的手正一点一点地从指尖往上变凉。于是,母亲往他的手掌里放了一张字条,让他握着。他便拳起手,熟睡了,像是一个累极了的人。
字条上写的什么?我问母亲。
“你安心地走吧,在那边等我。我们的情缘未了。”
听罢,我泪如雨下,我的父亲母亲啊……
父亲火化那天,从为他换衣服、化妆到推入遗体告别室,我与妹妹自始至终在旁侍候,就在殡仪馆工作人员为他穿衣的那一刻,我看到了父亲手中的字条。
父亲走了,母亲常常做一个相同的梦,在梦中,她总是在不断地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去寻找父亲。醒来就要说:“这夜长长的,怎么也不到天亮的时候?”白天,不知干什么好,惶惶地,总陷在对父亲种种事情的回忆中,于是又说:“这天长长的,怎么也不黑?”
但母亲知道,她的字条已经被父亲带到那边去了。
前不久,我们和母亲一起,为父亲和母亲买了一块共同的墓地。母亲说了,那里就是他们老两口未来的共同的家。她想告诉父亲不要常常在桥头上站,那样会太累。南方的日头太毒,会把人晒晕的。每天在桥上看一看,累了就回家里等,她一定会如约而至……
虽是生死两相隔,这一份情缘依旧相连,一头握在父亲的手中,一头牵在母亲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