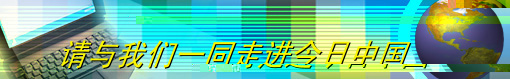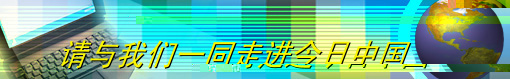“恒温”的爱情
本刊记者 张 娟
 |
| 喜结良缘 |
王大吕在家中属“主事儿”的一方,被孩子称作“政府”。而老伴孙曾鑫则称她为“保护神”。接受采访时,王大吕主讲,老伴好脾气地端茶倒水,偶尔从旁作些补充,还时常引起“批评”。奇怪的是,你从中感觉到一种和谐,这是一个典型的“女权”模式的家庭。
王大吕70岁,孙曾鑫73岁,退休前两人都是一家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我们的感情没什么波折,平平淡淡地过了一辈子。”王大吕这样总结他们的爱情。
三次大病“串”起的生活
 |
| 摄于1968年的全家福 |
上个世纪50年代,孙曾鑫和王大吕大学毕业后,先后被分配到北京的一家设计院工作,参加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
“从结合来讲,我们很顺利:在一个科室工作,一个学建筑,一个学结构。又是江苏老乡;从家庭来讲,都算书香门第,又都是家中独生子女,可以讲是门当户对。”王大吕说就这样,两个年轻人开始了他们共同的生活。
几年后,三个孩子相继出世。“我们的收入,在当时的设计院是中等水平,他挣82元钱,我的工资是56元,要养活包括双方老人在内的7口人。虽然生活条件不好,但没觉得怎么苦。”王大吕说。由于工作性质,两人常年累月地出差在外,三个孩子只能交由姥姥独自来带。“那时我们出差多是到四川、云南等地的深山里去,住在农民的房子里,夜里经常被大老鼠惊醒。工作条件很艰苦,打着雨伞在外面画图是经常的事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二人的噩运也从此开始。1966年6月,单位要抓“反革命”,因为要占用办公室,孙曾鑫在与同事在腾空办公室时,脑袋不小心被重物撞了一下,当时根本没在意,继续搬东西,后来觉得头痛、看东西重影,到单位的医务所去看,被认为是“神经性头痛”,吃了很多药,仍然头痛得厉害,到北京宣武医院一检查,脑袋里有一个鸡蛋大的血肿,初步诊断为血管破裂后的瘀肿,属于“占位性病变”。单位通知当时在湖北出差的王大吕尽快回北京,含糊其辞地告诉她“小孙得病了,让你回来照顾”。“我当时脑子嗡地一声,一夜没睡觉,想到种种可能,又都排除了:会不会游泳淹死了?不可能,他一是胆子小,再一个水性好,估计不会是这个;会不会是中毒性痢疾?应该不会,他一贯很注意卫生;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肯定病得特严重,要不然不会叫我回去,说不定人已经摆在那儿了……”王大吕说当她赶回北京时,由于精神紧张,在去往医院的路上,觉得迎面来的汽车好像都在往自己身上开。当时已昏迷的丈夫间或清醒时重复的一句话是:“我要大吕回来。”现在回忆起来,王大吕仍心有余悸:当时我32岁,他也才35岁,如果人没了,三个孩子怎么办?我们这个家怎么办?“7月1日做手术,医院让我签字,告诉我手术的三种可能:一种是病人在手术台上下不来;第二种可能是也许不是外伤,而是癌症,就是活下来可能时间不会很长;第三种可能,最好的结果,切除病变,但也有可能残废,要做好伺候他一辈子的准备。”我告诉大夫,尽管三种结果我都得接受,但最希望的还是人能好好地活下来,伺候他一辈子我认了。王大吕说当时看病时要填“家庭成分”,万幸的是小孙家是“中农”,说如果病人换了是她,不知结果会怎样,因为她们家是“地主”成分。就在小孙治疗期间,孩子的姥姥因为是“地主婆”被清出北京,赶回老家去,王大吕就一边上班,一边照顾病人,一边照料孩子,独自撑起了这个家。王大吕清楚地记得手术后丈夫转到在小汤山的疗养院做恢复治疗,有一次她去探视,早上5点从家出来,正赶上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城里的公交车几乎都停了,她一手拎着衣物,一手拎着炖好的汤,一直走到下午两点多才赶到那里。
也许就是从这次病开始,这个家确立了这样的模式:女人是男人的精神支柱,老孙说王大吕是自己的“保护神”,他们这一代人的爱情没有山盟海誓、花前月下的浪漫,更多的是对爱人、对家庭的责任感,他们的爱情没有大起,也就没有大落,是“恒温”的。
祸不单行,到了1967年11月,身体刚恢复、上班不久的孙曾鑫又患病了,当时因为“清理阶级队伍”,医院里的医生忙于运动,专家们都被“清理”了,结果他的病被误诊,按“气管炎”来治,越治越厉害。几个月后确诊为肺结核时,已经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血了,但医院病床紧张,一时住不进去,处于开放传染期的他只能住在家中,医院每天来人给打点滴。尽管王大吕十分小心,但全家人还是被不同程度地传染上了,几次检查后,发现孩子们都没什么大问题,夫妻才放下心。王大吕说当时的日子真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她用了一个词:“相依为命”!“好在他那时年轻,身体底子也好,所以就那么抗过来了。”1969年,全家随单位“战备搬迁”到山西太谷。那段日子过得清苦,连油都没有,吃得是盐水煮菜,营养严重缺乏,结果小女儿的结核病犯了。那是一段能把人折腾死的日子。
2000年6月,这对夫妻又一次遭受考验:老孙被诊断患了肺癌。王大吕说,比起前两次,她镇静多了,一是年岁大了,身体到了出故障的时候,二是孩子们都长大了,能替她分担,再一个到了一定年纪,对生老病死的认识也坦然了许多。“有病就治病,没有什么好怕的,怕也没用。”被切除了两叶肺的老孙现在的状态很好,手术后经过十多次检查,各项指标都很正常。“主要是病灶切除得彻底,再一个就是乐观,最关键的还有大吕的鼓励和照顾。”作为志愿者,老孙经常去301医院为做化疗的患者现身说法。
二次创业为自己挣够养老金
1990年退休后,两个人没有像别人那样安享晚年。退休前他们曾多次到深圳出差去做工程,感受到深圳特区与内地的不同,观念上也超前了很多。王大吕说当时两个人的想法是,要把眼睛睁大,要看远,不能只盯着眼前的那点东西。“那时我们俩人的退休工资都只有100多元,买个彩电还得女儿资助。这将来怎么能够自己养老?靠孩子吗?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日子,况且也都不宽裕。而且公费医疗制度的改变势在必行,得趁着还干得动,为自己的将来做些打算。”于是两人筹划到深圳去打工,他们把北京的家锁起来,一走就是10年!等再回来时,家里挂满了蜘蛛网,王大吕开玩笑说“像奶奶庙”。
“我觉得工作了几十年,真正体现人生价值是在这十年。因为我们工作的时候赶上了各种运动,我们把自己的青春和才华都消耗在各种政治运动中了。”孙曾鑫评价他们当时的状态是“放虎归山”,在那里他们找到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价值,“那是一个人才和知识被空前重视的地方,”说起这一段,老孙争着与老伴一起“主讲”。不过还是遭到了批评:刚去深圳时,他们夫妻二人起先应聘在不同的公司,一个在城里,一个在郊区,当时因为工地没有电话,二人联系起来不方便,老孙为此感到不适应,想回北京,“他离开我就没主心骨”,对于老伴武断的结论,老孙笑眯眯地说“那不一定”。
后来两人到了一个公司,在一个工地上工作。一个负责结构,一个负责建筑。老孙解释说“结构”是管“骨头”,就像一个人的骨架,是管一座房子它的柱子要多粗,要多少钢筋,基础要多大,承重量多少;而“建筑”相当于人的皮肉、服装,如何布置合理、实用、美观。一般来讲民用建筑,“建筑”最重要,而工业建筑,“结构”就比较重要。
深圳呆的6年多,基本是在香港公司,做了好几个项目。以质量赢得香港老板的尊重,老板最欣赏王大吕的一句话:“我们出卖技术,但不出卖人格。”他们说这是五十年代国家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做人的准则。王大吕说:“后来人家都认为我们都做了楼盘负责人,怎么着也得赚几百万回来,但实际上没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准则。靠劳动和技术,为自己赚下了养老金,我们已经非常知足。”
在深圳的几年里,两人收获最大的是在规范的技术环境下工作,整个工程从文字、手续、技术来往函件等都是与国际接轨的,这比内地早了一步。正是有了这个基础,后来两人又“跳槽”到上海干了三年多。
十年后,两人回到了家。一个65岁,一个68岁,他们准备安度晚年。回家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卖掉8麻袋的书和资料,彻底“洗手不干”了。并把那一年定为自己的“旅游年”,去走亲访友,游山玩水……然而旅游回到北京后不久,老孙被查出癌症。
如果还有下辈子就不再结婚
王大吕说人老了以后,最怕的是两人之中先走掉一个,而这又是一个必然的结局。她有些感伤地说,如果还有下辈子,她就不再结婚。不是不爱家人,正是因为太爱他们,哪个都放不下,所以才牵挂那么多。“就说我们两人吧,如果我先走,我会放心不下,谁来照顾老孙的生活,一辈子他已习惯我来管了,如果我不在了,他的日子该怎么过?这是最让我牵挂和放心不下的。而如果他走得比我早,我会为他伤心,大家一起相守了几十年,如果突然没了,我不敢想像自己该如何面对那种孤独……”老孙深有同感:树老怕空心,人老怕冷清。特别是他生病后更觉得对老伴的依恋,他说老年人的爱情其实很简单,就是两人能相守在一起,大家能一起去买买菜,雨天出门时嘱咐对方别忘记带雨伞,互相牵挂着,很平淡、很琐碎,但也更加珍贵。他说王大吕说的“下辈子”是不会有的,他们最应该珍惜的是现在的日子。
“享受人生,愉快生活,活一天就快乐一天”是他们现在的生活态度。王大吕说总听到有的老人不知怎么打发时间,他们没有这种担忧,每天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她经常会到电视台去做观众、录节目,很多时候王大吕会带老孙还有她所在的社区合唱团去。“有的栏目组比较大方,会给一个盒饭,发一瓶矿泉水,有的栏目可能是经费紧张吧,什么都不给,我们就自带。”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日子充实。王大吕说由于在深圳时养成的习惯,她穿的衣服色彩都很艳丽,因此每次节目她的镜头都会很多。王大吕最高兴的是有一次参加“相约夕阳红”节目时与著名藏族歌唱家雍西同台演唱,雍西还向她献了哈达。
老孙说王大吕的歌唱得非常好。上中学时,上海国立音专毕业的老师就特别看中王大吕唱歌,曾推荐她读上海音乐学院,但当时国家正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对青年人来讲,国家需要是第一位的,王大吕没有选择唱歌这个专业。但唱歌成为了一辈子的爱好。到北京工作,有了第一个孩子后,王大吕考取了北京市工人业余合唱团,在工人文化宫活动,经常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参加录音,《祖国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都是她们当时经常唱的曲目,现在王大吕又参加了社区的合唱团。
好静的老孙喜欢画画,家里的墙上挂满了他的画作。他们很珍惜现在的日子,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快乐。王大吕在家练习唱歌每天必唱的一个曲目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受。
2003年,王大吕被评为“北京市健康老人”,“这个评选标准很严的,只有身心健康才能当选,我就没这个资格了。”老孙很是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