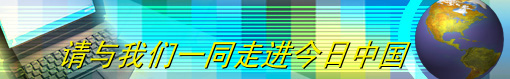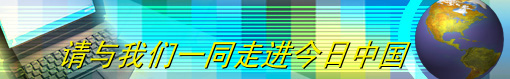何时农民将不为看病发愁?
文/本刊记者 乔天碧
“只要了解一下有多少城里人死在家中,又有多少农民死在家中,就能了解中国农民的医疗状况。目前的状况是,大多数城里人死在医院,而许多农民是死在家里或赶往医院的路上。”四川省峨眉山市市长何金文在谈到农民医疗问题时这样说。医疗问题是目前农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有统计显示,目前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还很严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人口已占到贫困人口的50%。医疗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民的身体健康,还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活质量。
马医生和他的卫生室
 |
| 马医生在为村民就诊。 |
马泽东是峨眉山市的一个山村,马苹村的乡村医生,他在自家房子旁开设了一个卫生室,为村子38平方公里的2000多个村民提供医疗服务。曾是一名赤脚医生的马医生在村里行医快40年了,2002年他被评为全国优秀乡村医生。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赤脚”的是从事体力劳动的,而医生则是一个专业技术性非常强的职业,“光脚板的医生”可以说是中国人的首创。20世纪50年代,为解决中国农民的医疗问题,中国政府创立了与城镇的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体系并行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70年代,合作医疗覆盖了全国90%的行政村,当时每个人民公社,甚至生产队都有自己的医疗机构,除了重病之外都可以诊治。亦农亦医、半农半医的农村保健员应运而生,1968年,农村保健员被正式命名为“赤脚医生”,据1978年的统计,当时全国有160万名赤脚医生。他们大多是出身好,稍有文化的农村青年,马医生就是村子里根红苗正的青年。1966年,大队通知刚刚初中毕业的他去学针灸、学草药,他成了“脖挂白毛巾,肩背小药箱”的赤脚医生。
凭着合作医疗、公社保健站,还有赤脚医生这三件法宝,中国农民的健康状况得到了长足的改善,农村的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传染病死亡率大幅降低,农村居民的平均期望寿命延长了30多年。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称其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惟一范例”
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福利医疗制度,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陷入了危机,到1985年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覆盖率降至5%。赤脚医生也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一把草药、一根银针”毕竟只能解决小灾小病,由于缺乏严格系统的专业训练,救死扶伤的背后难免有耽搁人命的事情发生。实行“联产承包”后,自身的生活成了问题,许多赤脚医生改行做了民办教师,或专职务农。1985年,卫生部宣布取消“赤脚医生”名称,经考核合格者改称为乡村医生,并颁发乡村医生证书,“赤脚医生”退出历史舞台。
凭着多年的行医经验和努力,马医生完成了由“赤脚医生”向“乡村医生”的转变,还开了自己的卫生室。现在,他还坚持做赤脚医生时的作风,经常下乡给病人看病,送医上门。春节刚过,一个家离诊所有两里地路程的老太太,因为洗澡着了凉,发高烧。半夜三点多钟老太太的儿子上门来请他出诊,马医生二话没说背起药箱就走。
马医生和大多数乡村医生一样,实行“四免”,即免收挂号费、诊断费、注射费和出诊费。卫生室的地面铺有地砖,墙壁上贴着瓷砖,消毒室、观察室、药房一应俱全。药房里的药品都是从镇卫生院进的货,一盒藿香正气水进价1元5角,售价2元,马医生还有些赚头。因为村民不富裕,马医生就把药拆散了卖,还可以赊药。除了为村民提供医疗服务,他还负责村里近600名育龄妇女的保健工作,并承担村里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及健康教育,组织婴幼到镇上的卫生院去注射疫苗的工作。村里人都很信任马医生,说他技术很好,特别是小儿科看得最好。村里人还喜欢马医生浓厚的人情味,村里人每次去就诊他都端茶倒水,让人心里暖暖的。
从马医生家的二层小楼可以看出他的收入还不错,他的儿子1998年从峨眉山市的一所卫生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外边打工边学技术,准备将来子承父业。
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
在马医生完成自己的角色转换时,许多卫生管理部门和机构也在摸索建立新型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峨眉山市有著名的佛教名山普贤菩萨的道场峨眉山,现存世界最大的乐山大佛。70%的山区,和近70%的人口为农业人口,使峨眉山市的农村医疗问题很突出。
合作医疗解体后,三分之一的村卫生机构垮台,三分之一负债经营,维持运营的村卫生室大多房屋破旧,医疗设施简陋,有的村卫生室医疗器材只有听诊器、体温表和血压仪。相当部分乡村医生年龄偏大,专业知识老化,难以满足农民健康的需求,居民们称村里卫生室是“一个牌子、一个房子、一个公章”。卫生管理部门曾尝试由农民自己出钱办合作医疗,但失败了。农村居民尤其是山村的居民就医十分困难,“小病拖,大病挨,不行才往医院抬”、“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一人得病,几代受穷”就是当地农村医疗状况的真实写照。
1998年开始,峨眉山市卫生管理部门开始乡镇卫生院的建设,对镇卫生院实行标准化管理,软件、硬件,小到床单都有统一的标准。随着乡镇卫生院设施和服务水平的提高,农民的一般疾患在卫生院就可以就诊,不需要到城里的大医院了。在地处偏远山区的龙池镇的卫生院,农民葛翠兰因做阑尾炎手术已住院10天了。33岁的她,一家四口靠2分地生存,每年收入三四千元(2002年峨眉山市农民人均收入3022元)。她说自己得了阑尾炎住院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过镇里卫生院的收费要比市里的便宜,手术费400元,床位费每天8元钱,不收陪护费,整个费用下来大约1000元,而在市里的大医院至少要两三千元。
乡镇卫生院的建设基本完成后,2002年卫生管理部门又开始进行村级卫生室建设。由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引入了市场运营的机制,实行行业准入制度,对卫生室的从业人员、设备、房屋进行认证。按照认证标准,乡村医生必须具有中专及以上的医学学历,赤脚医生的子女经过三年卫校的培训可以优先成为乡村医生。现在峨眉山市的253个村已有170个村卫生室,一般的头痛脑热,村民们走上一两里路就可以得到诊治,基本做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
峨眉山市卫生管理部门的负责人说,他们现在和许多基层卫生工作者一样,希望能够成为国家农村医疗改革的试点,这样峨眉山市的农民就可以和城里人一样看病报销了。“农民看病报销”,就是卫生部新近推出的针对农村的“大病统筹”医疗保险,即对医疗花费数额较大或者住院治疗的部分重大疾病给予一定医疗费用补偿的医疗保障制度。
何时农民将不为看病发愁?
中国的农村医疗问题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农民收入增长的幅度,远没有医疗费用增长得快,是造成农民缺医少药的经济因素。1990年到199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2.2倍,而同期人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分别增长了6.2倍和5.1倍,高昂的医疗费用使农民有病不去看的占到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
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也是一个重要因素,2000年中国农村卫生费用只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32.07%,占中国人口四分之三的农民只占用三分之一的医疗卫生费用。2000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正式启动了医疗保险体制改革,已有8500万人进入了医疗保险体制,但这一体制目前只惠及城镇人口,8.7亿农民还被排除在外。目前农民需要自己承担90%的医药费,而这一比例在城市为60%。但从收入上看,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可能已达6:1。
中国用只占全世界的1%的卫生资源保障着全世界22%人口的健康,要在此条件下,保障农村人口的医疗,就需要中央政府在政策上倾斜。新一届政府将解决农民的问题做为重中之重,因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无法实现中国的全面小康的施政目标。温家宝总理十分关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落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条件差的问题,他表示,从2003年开始新增的对科技、教育、文化和卫生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农村。
卫生部也出台了农村医疗的有关政策,在保证卫生事业经费增长幅度不低于同期财政经常性支出增长幅度的前提下,对卫生事业经费投入进行结构性调整。从2003年起到2010年,中央及各级人民政府每年增加的卫生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发展农村卫生事业,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2003年卫生工作的中心任务。
在此次抗击“非典”疫情的斗争中,防止“非典”在农村蔓延考验着农村的医疗体系,也直接关系全国疫病防治的成败。为了阻止疫情向广大农村蔓延,中国政府决定健全县乡村三级结合、以村为基础的疫情检测体系,并建立救治机制,对农民患者一律实行免费医疗,从留验、隔离到治疗的全过程一律实行免费,包括免费提供住院和伙食。目前许多农村的医疗基础设施薄弱,技术力量不足,疫病监测体系不健全,农民普遍缺乏必要的卫生防疫知识,防范疫病的意识差,农村存在着非典疫情扩散的渠道和隐患。因此,提高农村的医疗水平,建立健全农村医疗体系已迫在眉睫。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一种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改变过去风险和费用完全由农民承担的办法,由中央财政出10元,地方财政出10元,农民自己出10元,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一旦生病住院,就可以得到比例不一,全年最高额度为2万元的医药费报销。一年下来如果未动用合作医疗基金还可以进行一次全面体检。这样就打破了农民认为交了钱不得病,钱给别人看病用了,而宁可“谁生病,谁自认倒霉”的不平衡心理。目前农民每年的税收为人均30元,今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将为每个农民每年拨20元的医疗费用,农民还是划得来。这一制度还要求农民以户为单位加入,体现了“今天为明天储蓄,年轻人为老年人做贡献”的原则,使这一合作医疗制度,具有可持续的操作性。此外,新兴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体制和监督方面都有新意。
卫生部将在各省选择2到3个县开展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试点,并以此为突破口,全面推进农村卫生工作。据卫生部介绍,新的政策将使60%到70%的农村人口受益,在2010年时覆盖全国农村居民,那将是几亿农民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