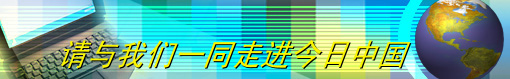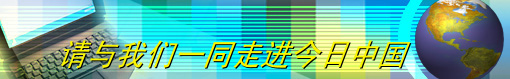城市拾荒者
李宇飞
拾荒者的生活
 |
| 正在拾荒的中年男子。 |
在城市中,活动着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整天与垃圾为伍,以捡破烂、收废品为生,在人们或忽视或鄙视的目光中艰难而又顽强地生存着。有人给他们起了个文雅的名字:拾荒者。大多数老百姓叫他们:捡垃圾的、收破烂儿的。当您看见他们在垃圾站、废品堆中出没时,会不会问: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什么选择这种生活?他们在城市里遭遇了什么,又从城市中得到了什么?
每天,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们都能听到这样的吆喝声:“收废品破烂,有旧家具旧电器的吗?有书本报纸吗?有酒瓶易拉罐吗?”人们的印象中他们大多是操着外地口音,衣着陈旧,推着平板车出入街头巷尾,收购一些旧报纸、饮料瓶、破家具等废品。除了收购废品,他们中的另一些人则出没在垃圾站、垃圾堆里靠捡垃圾维持生计。这是城市中一个特殊的群体,有人给他们起了个文雅的名字:拾荒者,也就是捡拾废弃物的人。
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据统计,在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230万名拾荒者。在北京,环卫工人2万多人,而拾荒者的数量却多达10万人。
现在,就请您跟随记者的脚步,走进他们的生活,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走进城市拾荒部落。
位于北京北郊的朝阳区洼里西村有一大片低矮、简陋的民居,居住着数千名外地来京的城市拾荒者。当整个城市还在沉睡的时候,这里许多人家的窗户已经透出了灯光。
在这里拾荒的不下千人,有四川的,湖南的,山东的,什么地方的人都有。
在一户低矮的平房里住着从湖北省巴东县来北京的拾荒者侯正宣一家三口。房间很小,不到10平方米,一张用木板拼起来的床占据了大半的面积,靠门口处放着一个做饭兼取暖的煤炉,房屋的一角摆放着几个木箱,上面是一台很有些年头的12英寸黑白电视,别的就再也没什么了。屋子里很冷,记者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在房间里坐了很久还是感不到一丝暖意。早上四点钟,一家人就全起来了,侯正宣的妻子贺贵华正在做早饭,他们两岁的女儿明明光着脚在地上玩。
侯的妻子三点多就起来做早饭。一家人吃过饭后,侯正宣接过妻子递给他的一杯水,把几片药片送进嘴里。感冒也不能阻止侯正宣外出捡垃圾。凌晨四点半,他辞别妻子和女儿,推上三轮车出门了。
凛冽的寒风中,侯正宣吃力地蹬着三轮车向城里赶去。一个小时之后,侯正宣来到离他家20里的工作地点,北京西城区某居民小区的垃圾回收站。这种垃圾回收站,看上去像一个车库,有两扇上锁的铁门封闭,里边是二三十平方米的空地,空地上挖了两个一米多深的垃圾池。据了解,在北京像这样的垃圾回收站有近千个,每个回收站收集一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城市生活垃圾。而像侯正宣这样的拾荒者就每天在垃圾池里捡垃圾。一般是两三个拾荒者“承包”一座垃圾回收站。
侯正宣换上黑乎乎的工作服,麻利地跳进齐腰深的垃圾池,手里拿着一只三爪的耙子,迅速地翻捡起来。池子里是满满的生活垃圾,烂菜叶、腐烂的食品混合着包装袋、碎玻璃、小动物尸体以及一些辨认不出模样的物品,弥漫着难闻的气味。侯正宣把塑料袋、饮料瓶、破布头一一捡出、分类,放到事先准备好的几个麻袋里。一天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捡拾的物品,价钱不一,像碎玻璃碴,一毛钱一公斤。破布也是一毛钱一公斤。
到下午两点,侯正宣已一刻不停地干了整整8个小时,准备收工。此时,他已经捡了满满四五麻袋的东西,分别装着餐盒、塑料袋和饮料瓶,足有100多公斤。
侯正宣把一天的收获装上三轮车,赶往位于北京北郊的洼里西村废品回收市场。
一个多小时之后,侯正宣来到废品回收市场。这里由铁丝网、围墙圈起了一平方公里的一大片场地。场地里一片泥泞,杂乱无章地拥挤着上百家经营废品回收的个体摊点。每个摊点都堆着小山一样高的各种废品。住在附近的几千名拾荒者大都把捡来的垃圾送到这来交易。个体摊点把废品回收后,再用车运送到河北、河南等地销售。
就这样,侯正宣从凌晨四点半出门到下午四点多收工,捡垃圾用了8个小时,来回在路上蹬三轮用去两个多小时,再加上卖废品的时间,一口饭也没吃连续工作了十一二个小时,换来30多元钱。侯正宣把钱一张张叠好,小心翼翼地放进贴身衣服的口袋里,点上一支烟,跨上三轮车,悠然地向家里蹬去。此时,他的妻子已经做上热腾腾的饭菜,女儿明明正张开笑脸等着爸爸的归来。拾荒者一天的工作就这样结束了。
30多元钱在很多人眼里不算什么,对侯正宣来说是一家三口一天的全部经济来源,而对收废品的郑启学来说,挣到这个数目的钱要花上他两三天的时间。
郑启学,残疾人,40岁,老家在河南信阳农村,一年多以前经老乡介绍来到北京靠收废品谋生。一天下来,能挣个十块八块,一个月就三四百块钱。好在老板不收他的房钱。
因为腿脚有残疾,老郑40岁了也没能成上家,他领养了一个小男孩,现在已经在老家上小学了。老郑还有一位80岁的老母亲,为了养活这一老一小,他每天工作得很辛苦。但是他又感到很踏实,他为自己一个残疾人能养活一家老小而感到自豪。最近,他让自己的三个姐妹都来到北京收废品,他说只要踏踏实实干下去,再困难的日子也会慢慢好起来。
拾荒者的遭遇
 |
| 从孩子纯真的笑脸中看不出大人们生活的艰辛。 |
拾荒者大多来自经济不发达的偏远农村,他们是怎样走上拾荒道路的?来到城市,除了破烂垃圾,他们还面对着什么?
在北京的东北郊,有一处大型垃圾处理厂--高安屯垃圾填埋处理中心,城市里的生活垃圾先是被收集到垃圾回收站,再运送到垃圾转运站,最后送到这里进行填埋处理。据了解,在北京郊外有6个这样规模的填埋场。
一个寒冬的早晨,记者来到这家垃圾填埋场。这是一片方圆几公里的场地,完全被厚厚的垃圾覆盖着。运输垃圾的封闭式卡车穿梭不停,几辆推土机轰鸣着把一座座小山样的垃圾推平。虽然是在冬天,这里仍然弥漫着腐烂的气息。
一走进垃圾场,记者就看到几百名拾荒者分布在四周,这些人衣衫破烂,上面满是污渍、灰尘,遮住了衣服本来的颜色。每个人的头上、脸上也都灰蒙蒙的覆盖着尘土,几乎辨别不出男女老幼。他们表情专注,埋着头一声不响地捡垃圾。
一位捡玻璃的拾荒者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他把一些酒瓶、饮料瓶翻捡出来,发现完好无缺的就小心地放在一边,堆成堆;破了口的就把它砸碎,再把碎碴收起来。忽然间,一块玻璃碴划破了他的手指,鲜血立刻流了出来,这位拾荒者只是用块纸随意擦了擦伤口,就又若无其事地继续干活了。
这300多名拾荒者就住在垃圾场周围,他们用捡来的旧木头、碎砖头、破布搭起一座座小棚子,作为栖身之所。这样每天都工作在垃圾场、吃住在垃圾场,形成靠垃圾场为生的拾荒部落。拾荒人早晨六点开始工作,晚上六点多收工,卖掉一天捡来的东西,赶回家已经是晚上九十点钟了。就这样起早贪黑地与垃圾打交道,他们每天可以换来二三十块钱的收入。
记者结束这里采访的时候,已经到了晚上。运垃圾的汽车开走了,推土机也离开了这片垃圾场,拾荒人却没有要走的意思,他们还要继续工作很长时间,垃圾场里一片繁忙。
天慢慢地暗了下来,远处的城区华灯初上,城市绚丽的夜晚对拾荒者来说是那么模糊、那么遥远。
城市里的拾荒者大多来自经济不发达、偏远地区的农村。他们是怎样走上整日与垃圾、破烂为伍的道路呢?
许济才,上世纪80年代末来到北京,是最早进京的一批拾荒者中的一员。最初他的想法是在北京找份活干,打工挣钱。他先是找到一处建筑工地当民工,没想到做了几个月的苦力,到拿钱的时候,包工头却把钱卷跑了。老许干不下去了,兜里也只剩下几毛钱,饭都吃不上,晚上只能睡在桥洞下面。
在老乡的怂恿下,许济才走上了拾荒的道路,一干就是十几年。十几年来,他饱尝了辛苦、受尽了肮脏。如今,他已经不再亲自早出晚归捡垃圾了,而是到处承包垃圾场、居民小区垃圾楼,指挥着手下几十人干活,成了名副其实的“破烂王”。
拾荒者为了谋生付出了太多的代价,有辛苦,有健康,也有作为人的尊严。因为整天与垃圾、破烂打交道,常常受到城里人的歧视,是拾荒者们的普遍心理感受。最早来到北京拾荒的许济才告诉记者,他捡破烂靠的是劳动挣钱,但却经常被人喊作叫花子。
许济才说:“刚开始来的时候周边的人很看不起,租房都不租,说你是下九流,叫讨口子,叫花子。”
为此,有的拾荒者感到很自卑,觉得自己在城里人面前矮了半截,平时除了出入垃圾堆、废品站,就呆在家,不愿意出门,不愿意和其他人打交道。
收废品的老蔡不这么看,他说自己靠劳动挣钱,不偷不抢,凭什么被人看不起?他说:虽然我捡破烂,但我的心不破烂。
说这句话的时候,老蔡的腰板挺得很直。他的话虽然简单,但是掷地有声,令记者心头一震。的确,人们的心是平等的。在物欲膨胀的城市里,处在城市边缘、处在生活底层的老蔡坚守着做人的尊严。
还有的拾荒者说,自己的工作不但不该受歧视,还应该赢得人们的尊重。因为多收点废品多捡些垃圾,城市里的生活垃圾就减少一些,政府也就少花些处理垃圾的钱,同时不管是捡垃圾还是收废品,都是废物回收利用,都为国家节省了资源,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侯正宣认为他们的工作也是为北京市出了微薄之力。
拾荒者除了遭歧视、白眼外,还面临着更直接、更严重的恐惧。那就是各种名目的收费、罚款。采访中记者看到,几乎每个拾荒者的兜里都揣着一大把收费和罚款的收据。
除了治安队、联防员收取各种名目的费用外,拾荒者们到居民垃圾楼、郊外垃圾场捡垃圾,还要按月给当地政府的环卫部门交费,一个月要交几百元。这令他们很不理解,因为拾荒者们捡垃圾的过程中要做许多运送垃圾、打扫卫生、清理场地的工作,为什么环卫部门不但不给工资,反倒还要收钱呢?
全靠勤快才能挣到钱,要不生活都生活不了,小区收你300,400块钱,小区让你去捡垃圾算是承包给你,不光一年要交三四百元钱,还要受他约束,受他管理。
贡献与问题
生活在城市边缘的拾荒者是城市发展的产物,也是城市日新月异发展的独特见证者。
北京市政管理委员会高级工程师、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兼职教授王维平,常年关注拾荒者群体。
王维平说:“我们做了一个调查,在北京市,1998年捡荒的约8.2万人,这8.2万人的构成是这样的:来自四川的4.6万人,来自河南的1.7万人,来自河北的有1万人,剩下的有江苏的,安徽的,山东的,等等,人数比较少了。2000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回顾调查,发现这个人群已经增加到10万人。我们通过函调的方式,发现在全国668座城市中,这个阶层的人大约有230万人。”
王维平认为,这些拾荒人群以捡拾垃圾的形式给社会也做出了很多贡献。他以北京市为例,1998年这8.2万人从垃圾里捡出来的垃圾直接收入是11.2亿人民币。北京一年的垃圾是400万吨,而他们一年就减少了100万到200万吨垃圾。减少垃圾的同时就减少了政府的开支。北京市政府1998年一年为处理这些垃圾耗资7.2亿元,如果没有这些拾荒者的劳动,支出还要增加。同时还减少了垃圾的污染,垃圾少了就可以少污染。
王维平说,通过北京10万拾荒者的劳动,每年就直接为政府减少处理垃圾费数亿元。从全国范围来看,节约的费用就更多了。而拾荒者的工作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我国是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特别是在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当今时代,通过拾荒人的双手可以为社会节约大量资源。
我们国家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建立起国营的废品回收系统。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国营废品收购人员队伍逐渐萎缩。以北京为例,上世纪60年代城区里有2000多家国营废品回收站,到90年代末,只剩下5家,还难以生存。目前城市里的拾荒大军恰恰填补了这个空缺,完善了废品回收系统。
清华大学环境系教授王伟说:“我们国家从上世纪50年代建立的废品回收系统在早期还是很管事的,对废物的回收利用还是很有用的,但80年代以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一般人不愿意从事这个职业了,这样就造成国营废品回收系统逐步瓦解,然而废品则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加,这对拾荒者来讲,或者对偏远地区的农民来讲,这正好给他们创造一个能够就业,收取利润的机会。他们进来了,这对维系国营回收系统逐步衰退以后补偿它的功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无论回收的量和收集服务的范围都比以前国营的回收服务的范围扩大了。应该说城市捡荒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尽管拾荒者用自己的方式为城市发展、为资源回收利用做出了贡献,但是不能否认,由于拾荒者从业人员成分复杂,且多为个体劳作,分散经营,难于管理再加上疏于管理,也带来了不少诸如二次污染,破坏环境;衍生假货,危害社会;传播疾病,损害健康等社会问题。
拾荒者既做出了贡献,又带来种种难以回避的问题。据了解,目前这一群体的人数还在扩充膨胀,无序发展的态势依旧在蔓延。如果不对这些问题加以认真研究,不对这一群体加强管理,必将使这一系列问题继续凸显放大,甚至会影响到整个城市化进程。
拾荒部落还能生存多久?
 |
| 捡垃圾成了拾荒者惟一的生存方式。 |
城市拾荒部落人数庞大,成分复杂,管理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际上,目前拾荒者一般是通过地缘关系、亲属关系组成一个松散的帮派系统,互相照应。
北京市政管理委员会高级工程师王维平认为,拾荒者已形成了组织,有了一定的规模,如果没有约束的力量,在一小部分人法律意识淡薄的情况下,一旦铤而走险,就是一股威胁社会稳定的不安全因素。怎样才能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呢?王维平建议让拾荒者建立公司,实行公司化的管理,有一个体制性的约束体系,不仅能做到有效的治安防范,还能取得很好的效益。他说:“让他们成立公司,组织行业协会,帮他们解决困难,规范他们对社会不利的行为,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甚至在行规建立以后还可以立法。”
清华大学环境系教授王伟对此持不同看法,他认为,在目前的垃圾回收模式下,让拾荒者成立公司,建立规范的组织就意味着成本的增加,而拾荒者群体的存在恰恰就在于低成本,以及在低成本的基础上得到回报,成本提高后,虽然避免了很多社会问题,但没有利润,这个群体就会逐渐消亡。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环卫工程设计研究所副所长徐海云高级工程师认为,如果从经济角度出发建立公司、进行管理,取得的效果会适得其反。他提出解决拾荒者问题应该由政府部门建立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资源回收体系,他说:“我们目前的废品回收还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比如什么东西值钱,什么东西可以卖,什么东西可以通过回收卖更多的钱就回收什么,所以它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不是建立在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从这个角度来讲,建立在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资源回收体系才是我们的发展目标。但目前的现状,随着环境保护水平的提高,我们向规范化发展的过程中,它的经济利益,他回收的利润是在缩小,如果我们不能够从产品源头给予回补,补贴,那么规范化管理增加成本,发展空间也是有限的。”
让拾荒者组织起来成立公司,进行规范化管理,就会提高成本,降低利润,最终导致拾荒者群体消亡;而不加强管理,又会继续拾荒者群体的无序蔓延,问题得不到解决。究竟该怎么办呢?
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市容管理处处长卢英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目前拾荒者缺乏规范管理以个体劳作为主的状况必须改变,而解决规范管理和拾荒者经济利润两者间矛盾的根本办法是:政府加大投入,同时推行垃圾收费制,保证垃圾处理行业的经济利益,促进垃圾回收体系的发展完善。
他透露,本着“污染者付费”的原则和确立“环境消费”的意识,我国将全面推行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促进垃圾处理的产业化。“一个是加强垃圾处理的规划工作和建设的计划工作,第二方面就是要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体的多元化14∶39体制,第三推进垃圾收费制度,第四是事业单位在转制改革,要把环卫单位这个事业单位转制成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第五是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市场准入和特许经营的制度。”
2002年下半年,国家环保总局公布了《城市垃圾填埋气体收集利用国家行动方案》。在这个方案中,明确鼓励民间资本和私营企业以及国际商业机构进入中国城市垃圾处理领域。国家已经把垃圾综合利用项目,列入了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目录清单中。可以预见,当城市垃圾处理产业化体系建立起来,实现了市场化运作,城市拾荒部落会以一个截然不同的形象走进人们的视野,而城市拾荒部落也将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链接
来自有关管理部门的数字表明,目前在全国668座城市里,正规的环卫职工人数有65万人,而遍布这些城市里的拾荒者人数大约是230万,两相对比,正规军和游击队人数相差悬殊,可见拾荒者在处理城市生活垃圾、进行资源回收利用方面发挥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替代的。那么怎样减少甚至消除拾荒者给城市带来的种种问题呢?
专家建议之一
拾荒人群的工作性质主要是跟生活垃圾接触,而城市的垃圾里面含有很多种对人体有害的物质,一方面是生物性的,比如细菌、病毒,都可能引发疾病,另外随着现在城市的发展,垃圾成分越来越复杂,含有很多对人体有害的高分子的有机物,比如一些生活日用品和残留的东西,到目前为止,人们还不是很清楚它们的毒性,还有垃圾废物中可能含有一些放射性的物质,这些拾荒人群接触这些垃圾就可能得各种各样的疾病,进而传播给其他人群。
面对这一接触特殊工作环境的群体,中华预防医学会专家、北京大学环境医学研究所潘小川教授建议,拾荒者在捡拾垃圾中应该佩带一些劳保用品,自觉注意卫生。
潘教授说,我想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从他们自己的角度讲,他们在做这些垃圾的捡拾或者分类的时候,因为工作环境比较危险,他们应该有个人防护,比如工作的时候要穿上工作服,操作的时候要戴上手套,这时候就防护了,细菌病毒不接触他了,也不传染,最好能戴上口罩,这是个人的防护。
潘小川教授还提醒拾荒者,应该主动与卫生防疫部门联系,建立预防疾病的意识。
专家建议之二
在目前拾荒者对垃圾无序化的回收中,由于一些利欲熏心的不法分子追逐低成本,很多没有利用价值、应该焚烧或填埋处理的废品作为原料制成假冒伪劣产品,凭着低价格的优势进入市场流通,不仅破坏了市场的正常秩序,更为严重的是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诸如地沟油、垃圾猪、黑芯棉等等危害人民健康的垃圾衍生物,应该如何从源头上加以遏制呢?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环卫工程设计研究所副所长徐海云高级工程师说:“这方面我想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府在垃圾回收方面,包括回收产品产业上做规范化,要从环境保护,从可持续发展这个角度要加强规范和管理。另一方面在城市垃圾收集这一块儿政府要加大投入,包括教育和宣传,逐步建立一个从源头进行分类收集的体系来适应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需要。
清华大学环境系教授王伟也强调了加强管理的重要性:“我们所谓的管理是加强环境的管理,从地沟做油,我逮住你就罚,从这个方面,我不让他用这里面有害的东西去危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