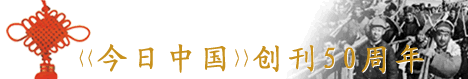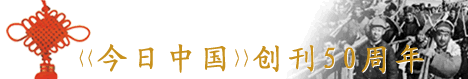陈翰笙:具有国际影响的学者、活动家和办刊人

陈翰笙(中)与专题研究他的生活经历的美国教授麦金农(左一)及夫人在家中合影。
|
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陈翰笙如今已走过了105个人生春秋。日前,记者来到105岁高龄的陈翰老家中,看望了这位跨越了三个世纪,曾经在国际运动中呼风唤雨,为新中国默默奉献,而又与本刊有过一段奇缘的世纪老人。尽管今天陈翰老已经没有视力,听力也在减退,但他对往昔经历的记忆却依然清晰,精神依然健朗。
投身国际运动
美国亚利桑纳州立大学教授史蒂份·R·麦金农夫妇1976年结识了陈翰笙,当时他们正在研究和撰写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传记,并就此事与陈教授交换意见。此后,他们作为外国专家在北京工作,几乎每星期都到东华门大街陈教授家叙谈。80年代初,麦金农开始比较系统地研究陈教授的生活经历,也收集到了大批有关他国际交往的资料和著作。麦金农认为陈教授是真正具有国际视野和从事国际活动的杰出的早期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通过参加2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斗争,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民主价值观和世界新秩序的看法,并通过自己的国际活动对这些新认识进行了实践。
青年时期的陈教授就至少能讲英语、俄语、日语、德语和汉语等五种语言,而且用这些语言发表了许多著作,这些著作至今为国际理论界所公认。比如美国太平洋学会出版了他写的一套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状况的系列丛书与论文,这套书记载了陈教授早年对中国无锡、广东和东北地区所作的农村调查研究,至今该书仍是西方社会研究解放前中国农村经济状况的原始材料。
陈翰笙除了在学术方面具有国际影响之外,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他在20世纪30年代也颇具国际影响。1936年—1939年他在纽约太平洋学会工作,同美国知识界接触广泛而深入。由于陈教授的影响,这个从不触犯现行社会秩序的教会机构,出版了许多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关注社会问题的有关中国的出版物。
与此同时,陈教授在纽约和华盛顿的外交界也发挥着影响,经常批驳国民党大使胡适的言论。由于陈教授在30年代初的上海与国际进步知识分子史沫特莱等人建立了联系,因此纽约也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与陈教授相识,许多人都承认受到过他的影响,其中曾与陈教授一同办过《太平洋季刊》的欧文·拉铁摩尔自认为受陈的影响最大。
1939年陈翰笙移居香港,在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工作。帮助组织建立了“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宋庆龄是名誉主席,陈翰笙是执行秘书,那时所有从海外来的捐款都通过“工合”分发到抗战后方和解放区。此时,陈翰笙以太平洋学会驻港代表的身份,在埃尔西·邱茉莉协助下办了《远东通讯》,这本对外宣传的英文半月刊在当时颇具影响力,那时在纽约,许多人都曾认真地阅读和利用这本刊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陈教授回到纽约市,他对西方的影响达到顶峰。当时,陈教授是中国留美学生的高级顾问,又是共产党的代表和同美国党派联系的联络员,此外,他还被公认是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的最高学术权威。陈教授那时非常活跃,他在美国所有的重要大学,包括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8所著名大学里任进教,讲过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没有一个国民党人能在学术上同他相比。他还向当时报道有关中国情况的美国新闻记者提供大量资料。这期间,陈教授在美国国务院和其他政府部门都有许多朋友,他经常前往华盛顿。麦金农认为,陈翰笙在1946年—1949年所起的作用犹如日后中国的民间大使。
回国参与《中国建设》的创办
1949年全国解放后,陈翰笙奉周总理的指示于1951年初绕道欧洲回国。那年,他已经50多岁,但思想感情、精神风貌就像血气方刚的革命青年。回国后,他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当时陈翰笙在外交部、《中国建设》、国际关系研究所等部门任职。
由于陈翰老与本刊创办人宋庆龄在香港有过成功合作,因此在酝酿创办本刊时,陈翰老积极参与意见,曾就刊名及出版日期等事宜多次与宋庆龄进行书面沟通。创刊后,陈翰老任本刊第一任编委会副主任。他亲自制定了本刊的编辑方针,即要使世界各国最广泛的阶层,了解新中国建设的进展,以及人民为此所作的努力。
本刊创办初期,条件很差,连个相样的办公室都没有,工作人员也只有6名,但是在陈翰笙的领导下,大家干劲十足。后来经过不断补充新生力量,本刊的工作才逐渐走上轨道。那时,陈翰笙总是上班时间未到就来到办公室开始工作,他承诺写的稿子无不准时、甚至提前交稿,而且绝不超过编辑计划要求的字数。他对下属工作人员要求也十分严格,强调稿件要通俗易懂,精益求精,不行就得重写。
陈翰老是一个很讲效率的人,要求大家珍惜一分一秒。一次,他约一个同志谈工作,那人晚去了15分钟,只见门上贴着一张黄条,写着:“时间宝贵,恕不久候。”陈翰笙早已人去房空。此后,谁也不敢再迟到了。
陈翰笙十分善于运用他的广泛的社会关系,为刚问世的《中国建设》争取各界的大力支持。每当人大、政协开会,金仲华或陈翰笙就出面邀请各界知名人士举行座谈会,出谋划策。并组织专家、学者为杂志撰写专稿,名人写稿成了本刊一大特色。
当时本刊每期都必有几篇反映中国主流生活的重点文章,在早期,这多半是由陈翰笙亲自策划的。而且常常是由他自己亲自执笔。自1952年到1963年,他在杂志上发表的署名文章共有26篇之多,而且多半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陈翰老的文章受读者欢迎,不外两个原因。一是他常识渊博,对中国国情了如指掌,因此能够娓娓道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另一个原因是他深知外因读者心中存在的疑问,因而能够有的放矢地去解疑释惑。既不过高估计他们对中国这个东方古国已有的知识,时时注意交待背景材料。又不过低估计人家的辨别能力,绝不强加于人,让读者就事实自己做出判断。而且这些文章都是直接用英文写的,符合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
热心助人 不求闻达

20世纪80年代后期,陈翰笙在家开设英语班。 |
回国后,陈翰笙夫妇长年住在东华门大街25号一个古老破旧的院子里。他们住在朝西的三间东厢房里,冬天相当寒冷,陈翰笙经常穿着棉袄在家里工作。夏天,东屋西晒,非常炎热,陈翰笙经常打着赤膊,汗流浃背地工作。陈翰笙虽是副部级领导干部,但他并未享受相应的待遇,也未曾想去争取这种待遇,他在东华门那间简陋的住所里一住就是25年,生活非常愉快。
陈翰笙性格朴实开朗,耿直坦诚,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他说:“我不会吹牛,也不会拍马,有人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吹牛拍马的人。”可是如果他的朋友、学生有什么困难,求助于他,却是有求必应,尽其所能地热情帮助。
1971年下半年,70多岁的陈翰笙从干校回到北京,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北京大学名誉教授,《外国历史小丛书》主编……他还要指导各种研究工作,指导研究生、指导编书……工作十分繁忙。这种情况下,他还利用晚上和周末在家里办起了英文学习班。在那没有上学机会的年月里,来向姨父学英语的人越来越多,有中学生、大学生,还有干部,由于程度不齐,开设了初级班、中级班和高级班。他亲自到王府井外文书店去买英文报刊作为教材发给学生读,每堂课都同学生讨论怎样把中文报刊上的某一段报道译成英文。陈翰笙都英文十分投入学生学得也十分来劲,东华门后院的一间小平房成了一所生气勃勃的英文学校。
陈翰笙80多岁时,患上了严重的青光眼病,视力极差,但他工作热情却很高,精力过人。他说:“我像一部汽车,发动机是好的,虽然两个车灯不亮了,只要是熟门熟路,我这部汽车还是能走的。”在东华门院子里,他常从有着三层石阶的走廊上跳下去,以证明他的“发动机”还很好。每有客人来,临走时他都要把客人送到院子外面马路边。冬天寒风凛冽,家人劝他戴个帽子,他笑着说:“我从来不喜欢戴帽子,‘四人帮’要给我戴那么多顶帽子都没有戴上,现在我更不用戴帽子了。”
陈翰笙热心助人,不论什么人,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到家里来向他请教问题,一般都是来者不拒的。他喜欢实干,视工作为生命,从不浪费时间。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周有一张时间计划表,每一格代表一个小时,表上总是填得密密麻麻的。可是近几年,他的记忆力减退,双眼几近失明,他已不能那样紧张工作了,为此他感到苦恼。他说:“我拿了工资不干工作,活着干嘛?”所以他总是向人们要求工作,他常对人说:“我还可以教英文,可以讲世界历史,谁来跟我学都行,可以随时来找我,白天来,晚上来,星期天来都行,我尽义务教,不收学费,不要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