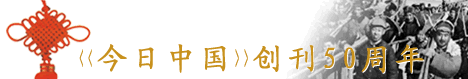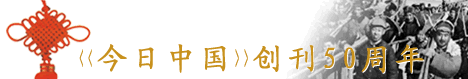爱泼斯坦:以传播中国为己任的特别中国公民
1951年的盛夏时节,正在筹备中的《中国建设》杂志编委会副主任陈翰笙先生和张彦一起,去北京前门火车站迎接爱泼斯坦和邱茉莉夫妇。他们是受宋庆龄之邀,从美国回中国参加《中国建设》工作的。
当时,中美关系十分紧张,爱泼斯坦夫妇克服了重重阻力,绕道波兰等国,几经周折才回到中国。
没想到,此后的半个多世纪,爱泼斯坦再也没有离开过他所热爱的中国,并成为一位专向世界传播中国的特别中国公民。
为一本外宣刊物,数十年呕心沥血
爱泼斯坦自幼随父母来中国定居,中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1938年在广州结识了宋庆龄,并参加了她创办的“保卫中国同盟”,负责编辑《保盟新闻通讯》英文版,1944年参加中外记者团赴延安采访,会见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写下了许多文章在国外发表。
1951年爱泼斯坦夫妇一到北京,就投入了《中国建设》繁忙的创刊工作。创业伊始,条件相当艰苦,北京编辑部仅有六个人,甚至连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第一期稿件,就是在公园的长椅上讨论、编辑而成的。爱泼斯坦夫妇作为执行编辑和工作人员,日夜奔忙,为了保证外文的排印质量,他们夫妇每月还要不辞劳苦,在火车上来回颠簸四天四夜,亲自赶去上海看杂志的清样和付排督印。为这本传播中国的刊物的初创付出了诸多辛劳。
后来,爱泼斯坦担任了《中国建设》的总编辑,几十年呕心沥血地工作,不仅为塑造这本中国一流的外宣杂志的性格和特色奠定了基础,而且培养了一大批对外宣传的人才。
在《中国建设》,爱泼斯坦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一定要为读者着想。他说“我们的读者是外国人,他们和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历史背景不同,习惯和经历不同,关键是,我们要设身处地替外国读者着想,下决心使我们的报道能使外国读者明了。要明确一点,编辑、记者写稿时脑子里要有读者的观念,而不是为了取悦于发稿人,以便稿子通过。
在数十年的编刊过程中,爱泼斯坦常常能比较清醒地把握方向,坚持实事求是,真实报道,避免走左、右极端,既正面报道中国,也决不回避中国的缺点、问题,使读者信服。这与他本人深厚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中外历史知识,以及能站在历史的高度和用全球的眼光来分析和观察中国现实问题是分不开的。
爱泼斯坦还有一个“职业病”,或者说是他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即有错必改,有问题必究。任何稿子,只要经过他的手,没有不改动的,有时甚至改成了一张“大花脸”以至《中国建设》的英文版校对同志最怕爱泼斯坦看付印前的清样,因为这时的改动会引起印厂的麻烦和意见。然而,谁都不能不佩服他的改动有道理,有时甚至是避免了一个被忽视的重要错误。
作为经验丰富的对外传播专家,爱泼斯坦非常重视对年轻外宣人才的培养,经常将自己宝贵的独到的外宣经验广为传播,爱泼斯坦告诉年轻记者们,“报道第一应该准确,第二应该使读者喜欢看。”“要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经历,要有语言的新鲜感,而避免讲套话。要积累深厚的基本功,这就是丰富的知识。”“记者在接触事物中,要把自己的眼睛、耳朵、脑子都放开,然后把你吸收的东西,以及你对历史和有关知识的了解,对读者的了解融会贯通,这样写出的东西才会有吸引力,有价值。”
对外传播一个真实、可信的中国

1951年,爱泼斯坦和夫人邱茉莉从美国回到中国参加《中国建设》的工作。
|
爱泼斯坦有一颗热爱中国的心,在北京居住了数十年,直至今天。并在1957年加入了中国国籍。他深情地说,“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在中国的数十年中,爱泼斯坦的目光早已远远超出了一本外宣杂志本身,他更时刻关注着中国在世界的形象,以及如何向世界传播一个真实、令人可信的中国。几十年来,他为不断改进中国的外宣工作,发挥着“高级顾问”的作用,参加过诸如《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等重要著作的英文稿审定,成为这方面令人信服的专家权威。为中国的对外传播做出了卓著贡献。
在大量编译和主编杂志工作之余,爱泼斯坦还以一颗热爱中国的心,以自己独特的视角,亲笔书写中国,对外宣传。
在《从鸦片战争到解放》这本书里,他站在历史的高度,把中国放在世界大环境中加以考察和分析,体现了他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研究达到了相当水平。正如他在书中所说,“每个人都在他自己的国家里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从全球的观点看,大家都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共有的历史。”
爱泼斯坦的另一本著作是《西藏的转变》,这是一部集历史研究与现实考察于一体的巨著。为了写这本书,他曾经不顾高山反应,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由陆路和空中4次进藏,先后采访了七八百人,记了近百万字笔记,同时又大量研究了几十种有关西藏的著作,特别是西方企图分裂西藏的论说,使得这本书的针对性更强,以至《西藏的转变》这本著作一问世,就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被视为一部研究西藏问题的重要著作。
而在宋庆龄诞辰100周年之际,爱泼斯坦又出版了一部50万字的宋庆龄传记《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这是宋庆龄生前的嘱托,他前后花费了10年心血写成的一部力作,受到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和极高的评价,并获得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最高荣誉“国家图书奖”。
为收集、印证资料和访问有关人物,他不知跑了海内外多少地方,他把自己对宋庆龄的爱,对中国的爱都溶注于书中。

唯一健在的原保盟中央委员爱泼斯坦(左一)与其他中央委员后代在一起。(从右至左,廖承志之女廖娟,廖梦醒之女李湄、邓文钊之子邓广殷)
|
为了一个真实,他这本书做到了,无一处无来历,无一处无根据。“凡是宋庆龄的直接引语,没有一句不是出自她的口或笔。”如果某些地方材料不足,他本着对传主一生的信实,宁可留下事实的空隙,不去主观虚构。如必须做些推测和解释,也如实说明。
比如宋庆龄第二次流亡德国的情况,和她在西安事变中发挥的作用等,目前尚缺乏第一手资料,爱泼斯坦没有在此去主观臆断,而是如实声明留下空白,待以后的发现研究再作补充。这看来似乎成为传记的一个缺陷,实际却是使它更令人信服。
为了一个生动,爱泼斯坦还从日常生活的细节来塑造美丽文雅,又富有个性的活生生的宋庆龄。如他写道,一次,宋庆龄请好友马海德到家中吃饭,见马海德系了一条颜色很旧的红领带,就说:“看来
应该送你一条领带了。”马海德说;“我带着它来看你,就因为它是你从前送给我的。”宋庆龄则笑着说:“那我一定要买一条新的送给你。”
正像他在书的总序里所说“我已尽了我最大努力,使宋庆龄真实生动地出现在所有读这部书的人的面前。”
可以说,爱泼斯坦的这部宋庆龄传记本身,就是一部对外宣传的范本,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