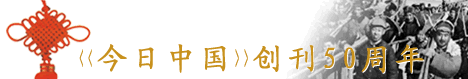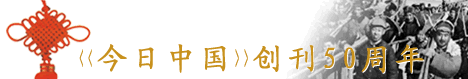金仲华:新中国对外传播事业的开拓者
为亿万人民敬仰和爱戴的伟大女性,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生前曾给她的老朋友爱泼斯坦写信说,她现在正病住医院,医生不让她动笔,可她总是惦记着一件事,就是要写一篇文章,来纪念她在“文革”中已故的朋友金仲华。
不久后的1981年2月,一篇署名文章在《中国建设》杂志上发表,题为《怀念金仲华――中国建设创始人之一》。
宋庆龄以饱沾深情的笔在文章中写道;金仲华,是我们杂志社的第一任社长,他是我一直非常尊敬的人。在过去爱国和进步事业中,他不遗余力地帮助了我和我的同志们。……金仲华秉性正直,他对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抱着良好的愿望和乐观的态度。他从未料到有那样恶毒的诽谤,他无法容忍那样残酷的折磨。1968年4月3日,他在被迫交代“罪行”时含恨而死。
在宋庆龄深切的怀念中,我们把追忆的目光聚集50年前,那万象更新,令人热情澎湃的日日夜夜。
孙夫人最信任和最可靠的人
就在共和国诞生不久的日子里,周恩来考虑到为了让国外了解新中国的真实情况,需要创办一个对外宣传的刊物。一天傍晚,周恩来亲自到北京方巾巷的宋庆龄住处同她共进晚餐,并向她提出了办刊的建议。商议中,宋庆龄非常赞赏周总理的主张,也认为办个英文刊物,让世界了解中国,很有必要。
就这样,在两位中国世纪伟人的不谋而合之中,一本新中国具有开创意义,影响重大的对外传播刊物开始孕育而生了。
宋庆龄受周总理之托,积极为这本英文刊物的诞生奔走筹划。在考虑办刊的负责人选时,宋庆龄首先想到了她最为信任的金仲华。到上海时,她将此事告与金仲华商议,希望他能一如既往地予以帮助。对于宋庆龄的要求,金仲华依然如从前一样,没有二话地答应下来。
宋庆龄之所以将这本周总理寄予厚望,反映新中国风貌和形象的重要刊物托付给了金仲华,自然是有原因的。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金仲华就在主编《妇女生活》《世界知识》《救亡情报》《东方》和《大众生活》等进步、救亡报刊中与宋庆龄来往结识了。1938年,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后,金仲华担任了“保盟”的执行委员,负责起草文件和编辑《保盟通讯》中文刊,直接与宋庆龄密切合作,成为她得力的助手。宋庆龄对金仲华的工作才能和无私品德非常器重和赞赏,说“他为此而呕心沥血。他在那时及其以后,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争取到同情和支持,其中包括许多外国朋友的赞助。”
同时金仲华的中英文功底俱佳,文笔流畅,思想观点、热忱和充分的说服力均可用中英文表达出来,所以常常能自如地将宋庆龄所习惯的用英文撰写的原稿,翻译成具有宋庆龄特有风格、文风,文辞优美的文章,深为宋庆龄满意,以至宋庆龄常请金仲华为她翻译或修饰文章。现在流传下来的不少宋庆龄的重要文章,都是经金仲华之手从英文翻译而成的。
在长期的合作中,金仲华日益成为宋庆龄最得力的助手和可信赖的同志。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宋庆龄前往八路军办事处与毛泽东、周恩来会晤,以及后来在寓所设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陪同者都是金仲华。
1949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电宋庆龄,邀请她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设新中国大计。周恩来特地亲笔指示:“电文望由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意。”周恩来的指示,无疑也印证了宋庆龄对金仲华的信任度和密切关系。
为《中国建设》倾注心力

金仲华与宋庆龄和外国少年儿童在一起 |
《中国建设》创刊时,曾组成了一个阵容强大,集各界名人的编委会,委员有教授钱端升、卫生部长李德全、实业家刘鸿生、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和基督教领袖吴耀宗。而金仲华和陈翰笙分别为编委会的正副主任。
1952年元月,由宋庆龄亲自确定刊名的英文双月刊《中国建设》创刊号,终于正式出版了。当第一本样书送到宋庆龄手上时,她非常高兴。立即写信给金仲华,对他和陈翰笙以及所有工作人员为筹办杂志所作的努力,表示“最深的感谢”。创刊号上,宋庆龄亲自撰文《福利工作和世界和平》。
作为《中国建设》第一任社长的金仲华,虽然身处上海,还肩任着上海《新闻日报》和英文《上海新闻》的总编辑,后又任上海市副市长,各项工作千头万绪,非常忙碌,但他对宋庆龄交付的《中国建设》杂志的责任,始终放在重要位置,为它的创建和成长付出了大量心血。
正如他在致宋庆龄的信中所说:“《中国建设》的政治影响,无疑远远不止中国福利会的一个机构,尤其它是与你的伟大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世界各地的许多人都会把这本期刊看作是新中国代表。”
出于这样的认识,金仲华总是时刻思考着如何把这本新生的对外传播刊物办好。他一面直接关注和指导《中国建设》在上海的出版、发行工作,一面利用频繁到北京开会的机会,经常来《中国建设》编辑部工作,特别是每年春天全国人大、政协在京开会的较长时间里,金仲华便利用会余,召开《中国建设》的编委会,认真研究杂志的编辑方针和各项业务。他还特别热心于帮助杂志的编辑记者,经常鼓励他们深入各种社会活动采访,积极组织专家学者撰写稿件。
金仲华在主持《中国建设》工作的过程中,经常写信给宋庆龄,向他汇报和请示。每期的清样都送宋庆龄审阅,征求她的意见。宋庆龄非常重视和关心《中国建设》的出版,经常在百忙之中写信给金仲华,发表她的看法,有时还作具体指示。仅从金仲华收藏的信件中看,在1952年《中国建设》创刊的第一年,宋庆龄给金仲华的信件就有17封之多。至今,宋庆龄和金仲华的部分信件,依然被视为“传家宝”,保存在《中国建设》(1990年改为《今日中国》)的历史档案里。
《中国建设》在宋庆龄的亲切关怀,金仲华等人的辛勤努力下,健康地成长着,逐渐形成了自己“真实报道”的风格与特色。这也是宋庆龄自保盟成立以来一直坚持的优良传统。
在1958年的政治形势下,编辑部曾提出拟多刊些政治斗争的内容,宋庆龄复信说:“我完全同意和支持,但必须表现我们自己的风格。”后来周恩来知道此事又指示:“《中国建设》报道中国目前经济文化方面的情况,就已经具有了政治的内容了,不要‘政治化’过多,改变它原有的风格。”陈毅也肯定了《中国建设》报道真实的传统,他说:“事实胜于雄辩,唯真理可以说服人。《中国建设》为世界各国朋友介绍真实情况,这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特别是 1958年,毛泽东在武汉阅读了《中国建设》杂志后说:“《中国建设》用事实说话,对外宣传就应该这样做。”对金仲华和《中国建设》的方向特色给予了充分肯定。
要使国外读者喜闻乐见
作为一位拥有丰富对外传播工作经验的专家,金仲华还以自己的文章在《中国建设》杂志上作出生动的范例。
从早期的《中国建设》杂志上可看到,金仲华所写的文章,大都反映了新中国的发展,同时又是为外国读者所关心的重大题材。例如1952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为工业化准备条件》的文章,从正面阐述了举世注目的“三反五反运动”的内容和意义,论说合情合理,深入浅出,有效驳斥了西方舆论的各种歪曲。
金仲华还是一位善于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向不了解中国国情、甚至有误解的外国读者介绍中国基本知识的高手。如他亲笔写的《人民政协怎样帮助政府工作》、《全世界最大规模的选举》、《节约就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等文章,就是非常好的范例。
当时的金仲华,还是一位出色的国际民间文化交流使者,他频繁出访世界各国,回来后即经常以轻松随意的笔调,在杂志上发表出访见闻随感。这类文章颇为贴近国外读者,又有思想深度,成为当时《中国建设》杂志的特色之一。
建国初期,金仲华除担任《中国建设》第一任社长外,还兼任中国第一张英文日报《上海新闻》和一本英文杂志的总编辑,1952年9月又出任中国新闻社第一任社长。成为中国对外宣传事业的创建人之一。
他结合对外宣传工作实际,提出了许多饱含自己丰富经验的真知灼见。
他经常说,“最好的宣传是使人看不出是在宣传。新闻宣传工作是一种艺术,它通过事实讲话,而不是跟人家针锋相对开辩论会,也不是板起面孔宣传。”
他还说过:“写文章,最重要的是让人读得下去。”“写文章像做人,也要平易近人”。具体讲“ 报道时要多讲事实,要有故事性,要多一点人物的活动,有时要用第一人称,要能引人入胜。”
“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不同对象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新闻报道的方式,要有高度的报道技巧――要稳,要灵活,要避免主观。“稿件不能穿着干部服、穿军装出去。不能教训人,不能强加于人更不能张牙舞爪,,要使广大国外读者喜闻乐见。”这些经验之谈,对于今天的对外传媒工作来说,仍是非常宝贵和适用的。
金仲华,一位功绩卓著的新中国对外传播事业的开拓者,历史不会忘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