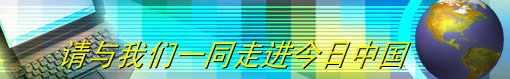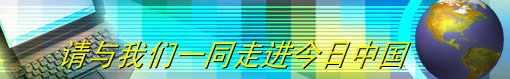一辈子的战役
文/本刊记者 张娟
簋街是北京很有名的一条特色餐饮街,北京戒酒互助会(Alcoholics Anonymous简称AA)的双语分会就设在离这条街不远的一个小旅馆里,与簋街的灯红酒绿比起来,这里显得要清静得多。走进地下室的楼道没几步,对面游荡似地走过一个目光涣散的小伙子,我知道自己要找的地方到了。
 |
| 嗜酒者互助会配合药物治疗的心理治疗方式是许多“酒鬼”从中受益。 |
“我是酒鬼”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酒鬼”,陈然的坦率让我吃惊——此前我一直犯愁用一个怎样的词来称呼才会不伤他的自尊。陈然说这是面对现实:只有承认自己是酒鬼,才能有戒断的勇气。
陈然刚从新疆、青海返回北京,他此行是自费去帮助那里的酒依赖者建立AA——尽管已有三年半滴酒未沾,陈然依然不敢说自己已戒酒。因为作为酒依赖者,他说自己对酒精没有丝毫的抵御和控制能力,一旦哪天控制不住自己喝一杯酒,他立刻就会重新回复到过去不堪回首的生活中。
陈然从16岁开始饮酒,有32年的酒龄。在他看来,一个男人,喝酒是理所当然的事!不喝酒算什么男子汉?何况家中爷爷、哥哥都很爱喝酒。
1978年毕业于国内一所著名财经学院的陈然,被分配到国家某部担任团委书记,曾作为团委委员参加国家机关的团代会。用当时一位部领导的话讲,他是被作为“苗子”和培养对象放在这个位置上。由于经常组织活动,陈然感觉自己“有酒量,能应付一些场合,人家认为我活动能力强、讲义气”,飘飘然中,喝酒的“潜能”被开发了出来,而且一发不可收拾。陈然说随着酒量的增加,他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由于受酒精刺激,他的思维已不是很正常,固执得任何人的意见都听不进去,先是一门心思承包单位食堂,承包失败后辞去公职下海经商,每天醉熏熏地经商,结果自然不难想像。接连失败后他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自卑得不敢见人,于是更频繁地用酒精来麻醉自己,喝酒不分场合、地点,只要酒喝到一定程度就变成另一个人,谁也不怕,打人、咬人、大小便失禁等酒后失态对他来讲习以为常。
“我都恨死自己了,恨自己没出息、没德行,我发誓要戒酒,我不想再过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陈然说戒酒经历同样痛苦,“有一次为了戒酒,我坚持吃中药,一个多月没沾酒。可就是在去医院复诊后回家的路上,突然产生一个想法,已经坚持一个月不喝酒了,身体恢复得也不错,少喝一点啤酒应该没问题,自己保证就喝一瓶啤酒。当这瓶啤酒喝完觉得自己还能控制,就要了第二瓶、第三瓶。就这样一直喝到不省人事,那次是连续三天一共喝了37瓶啤酒。当醒过来的时候我80多岁的父亲,76岁的母亲守在我的身旁,我不知道为何住了医院,我开的汽车停在什么地方。我父母为我和我哥哥喝酒的问题操碎了心,我爱人跟着我丢尽了脸,经常在深夜敲开邻居家的门求人家帮忙把我抬回家里——要知道我们住的是单位的房子,那些邻居同时就是她的同事。我再一次发誓就是打死我也不喝酒了。结果一星期后,我又醉倒在一家酒馆里……”
2000年5月,陈然在停止饮酒时出现幻听、幻视,当时不清楚这是突然断酒的综合症状。“我有一种可怕的想法:我离死不远了,因为我的表哥46岁时就是因为酒精中毒而死亡的,想到这些,我有一种恐惧感,我知道死亡的方法很多,我选择了喝酒,喝死不受罪,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狂饮,但每一次都能醒过来,真是求死都不成!”
一个偶然的机会,陈然的家人在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中看到安定医院医生介绍有关酒依赖疾病的知识讲座,大家才知道陈然实际上已是一个酒依赖患者,于是送他到医院进行治疗。经过系统的药物治疗后,陈然又加入安定医院的AA配合心理治疗——当时这种国际流行的治疗方式刚被引入中国。陈然永远也忘不了,他是在第四次参加AA活动时,鼓足勇气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我承认自己是个酒鬼,对酒精无能为力,我的生活不可收拾,只能向互助会求助了。”他说,就是从那一刻起,他的心情平静了下来,有一种轻松的感觉,“那种特殊的感觉是真正的酒鬼才会有的,是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酒依赖患者,而不是自己和人们眼中的那个没出息、没德行的人后的轻松。”现在的陈然已恢复到与正常人没什么两样,但他说,对酒依赖者来讲,戒酒是一辈子的事,就像糖尿病不能沾糖一样,酒依赖者也比正常人要耐得住无酒的日子。
曹大川是几个采访对象中最“挂相”的酒鬼,他自嘲说自己喝酒把脑子喝坏了不说,还把胆都喝没了——因酗酒引起胆囊炎被摘除。他很认真地说,他经过住院戒酒后,很快就复饮,喝得不行了,又重新住院,这样的经历已有4次了。他说脑子里总有一幅图景出现,一个醉汉趴在马路上被车轧死!如果再喝酒,这很可能就是他自己的结局。30岁的他曾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是一个级别很高的国家单位的高级厨师。小曹说最初喝酒是为了跟师傅搞好关系,但慢慢从酒精中找到一种感觉,干活累了喝酒可以解乏,遇到不顺心的事喝酒可以解愁,喝到最后离不开了。“嗜酒的人为了喝酒可以想尽一切办法”,小曹指着桌上的大号暖瓶说。利用工作之便,他每天至少会到餐厅的扎啤机打这样一暖瓶啤酒;他的工资基本上用来买酒喝,单位分的房子他租出去,租金也用来喝酒。小曹说,清醒时会恨自己,为什么这么不长进、没志气,也曾一遍遍地发誓不再喝了,但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痛苦得无法自拔,而且越来越自卑,觉得没脸见人,后来索性放开喝,想哪天喝死算了。“就这样,我把青春都泡在酒精里了,也把一切都喝没了。”小曹说这次戒酒时间已长达9个多月,戒酒、过正常人的日子现在是他最渴求的。他说每天对自己的要求是:我要保证在今天的24小时内不沾酒。
喝酒曾是很有诗意的事情
对曾敏的采访,始终进行得磕磕巴巴。这个女孩从一开始就吸引了我:略显疲惫的年轻面庞、沙哑的嗓音、一口流利的英语,自述酗酒经历时羞涩、躲闪的眼神,如果不是这个特定场合,我决不会把她与“酒鬼”联系在一起。
对于是否接受采访,曾敏告诉我是经过一番斗争的。“我不想让同事从你的文章里看到我的影子,但同时又希望更多像我一样的人了解酒依赖是一种病,应该正视它。”她要求我关掉采访机,并问我看她像不像个酒鬼——看得出来,她是个敏感的女孩,很在意别人的感觉。从她断断续续、多次欲言又止的叙述中,我得知她与酒的故事。
与陈然不同,曾敏说父母及家族中没有嗜酒者,她的酒瘾完全是自己培养起来的,由少而多,最后发展到离不开酒,“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喝酒。”曾敏说她是越来越体会到酒的妙处,“生活中无论有什么烦心事,一喝起酒来就全忘了,所以喝酒几乎成为我解决问题的惟一方法,因为这种方法最直接也最奏效。”
最先喝酒带给曾敏的多是快乐,她说现在只能把呼朋唤友在三里屯泡吧的情景封存在记忆中,“那种快乐我这辈子再也无法体会了”,曾敏不无遗憾。那时的曾敏已经有酒依赖的苗头,“但我还清楚自己能喝多少,而且要保持形象,喝得脚下觉得飘了,我就不再当众喝了。但回家的路上,我会买一瓶酒带回去,这样一是自己要喝舒服,另一个醉了也没人看得见。”在曾敏的讲述中,喝酒同时是一种很诗意的事情:“特别是到周末,自己呆在小屋里,躺在沙发上,一本书,一瓶酒,边喝边看,我能完全融入书中,现实中的那些烦心事可以统统忘记,那种境界,你真的无法体会它的美妙。”不过,随着酒量的增加,这种“美妙”被失落、痛苦替代了。每次醒来之后,她无论如何都回忆不起来自己看过的书是什么内容,倒是现实中那些自己想逃避的东西还真真切切地存在——而要解决这些问题,最简单的方法是喝酒,于是就又开始喝。
曾敏说她当时不知道自己已是一个酒依赖患者,只是认为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而已。曾敏大学时学的是对外贸易专业,毕业后在一家公司做管理工作,尽管她自己感觉“挺能胡噜”,但嗜酒使她越来越力不从心,“幸好还没丢掉工作。”她说从二十几岁喝到三十几岁,她的血压升到100-150,肾也出了问题,腰疼得几乎走不了路。“我突然有了一种对死的恐惧:我还有那么多美好的事情没有做。”曾敏说,不饮酒的人不知道喝酒的乐趣,也同样体会不到酒依赖者想戒酒又戒不掉的痛苦,曾敏说这种依赖是一种生理、心理的双重依赖,跟吸毒差不多,但它的危害又没有像毒品那样被人广泛认识。“我的医生曾告诉我,酒依赖者就如同被判了死缓,不复饮就没事,几次反复就是死路一条。”
曾敏说酒依赖者为了喝酒什么办法都想得出来,但为了戒酒,也是什么办法都想了,现在除药物治疗外,她还通过参加“戒酒互会”进行心理治疗,并搬回家中与父母同住,“为防止自己克制不住买酒喝,我每天上班只带两块钱,够坐公共汽车就行。”曾敏告诉我,她至今戒酒有半年多的时间了,“我很明白,如果复饮,又会回到从前的生活,而且有过去的基础打底,喝得会更狂。我在医院亲眼看到喝酒抢救不过来死掉的。与我一同住院戒酒的病友,我知道复饮的有好几个。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知道眼前是坑,但还是管不住自己跳下去……”
请让我来帮助你
2002年12月在上海举办的“中国第一届饮酒与健康国际研讨会”上,上海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合作中心公布:中国每年耗酒量相当于一个西湖的水量。近十年,中国酒依赖患者患病率上升3.7倍。中国成人饮酒中的5%为酗酒者,10%为问题饮酒。2673万酗酒者已成为社会公害、家庭灾难。
 |
| 李冰大夫(左)被嗜酒成瘾者称为中国的“比尔”。 |
“如果对喝酒有瘾,这说明在精神上和身体上对酒这种物质就有了依赖,这就是医学上所说的物质依赖。”刚到泰国参加完一个关于物质依赖国际会议返回北京的李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她说物质依赖现象目前在中国和国际上都处于不断增加的趋势,酒精、安眠药、毒品等精神活性物质的依赖,能引起人们的精神障碍,酒依赖是物质依赖中的一种。李冰介绍说,酒依赖患者分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受遗传因素影响,如家族成员有嗜酒者,这样的人患酒依赖的可能性比较大;另一种则是最初喝着玩或者好奇,慢慢上了瘾。李冰说,与适度饮酒不同,酒依赖者对酒除了他们的身体有需要外,他们的心理也对酒形成了渴求,也就是“心瘾”。“心瘾”才是戒酒的最大敌人。当他们形成依赖后,他们可以放弃一切,包括自己的事业、家庭和尊严,仅仅为了酒而活着。酗酒可使人逐渐对酒精成瘾,发生意想不到的意外伤害、人格和人性的改变以及思维的紊乱。
李冰告诉记者,酒依赖患者需要住院治疗,一般疗程为三个月。治疗方法很多,有药物脱瘾、行为疗法、心理疗法和家庭治疗等。李冰认为,对待酒依赖疾病应该像对待感冒一样,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世界上没有哪个人对此有免疫能力。不要把酒依赖简单地理解为人品、公德问题,这是一种需要关爱的心理疾病和心理障碍。因为太多的人不了解酒依赖疾病,不知道自己处在心理障碍的关口,也就无从谈及治疗;还有一些人,则担心提到精神病,别人会给自己扣上“疯子”的帽子,因此不肯就医,殊不知这样也许会使自己终生陷在酒依赖中不能自拔。当然,她也指出,酒依赖是一种顽症,复饮率高达
90% ,有的患者前脚从医院走出,后脚就进了酒馆,她的病人中,最多的一个至今已14次出入医院,李冰说他们为攻克这个顽疾在进行不断的探索,如过去对住院戒酒的病人在出院后无法监控,只能等下次复饮时再予以治疗,现在则可通过推荐其参加AA进行干预,而且效果不错。不过这毕竟是新生事物,因此人们接受起来也很不容易,“十个出院病人中,能有一个加入AA我们就很满足。”李冰说他们同时在做一项更有意义的工作:对处于“危险地带”但尚未形成酒依赖的病人进行早期的干预治疗,“防患于未然”。
李冰和郭崧是我在采访时听到最多的名字,“酒鬼”称他们为“中国的比尔”。2000年,他们将国际上流行的一种治疗酒依赖方式——嗜酒者互助协会(简称AA)引入中国。“AA”是由美国人比尔创造的,它是通过戒酒的12个步骤,以嗜酒成瘾者自愿的方式帮助那些愿意戒酒的人戒酒。是一种配合药物治疗的心理治疗方式。三年多来,已有不少中国“酒鬼”从中受益,他们出院后能够长时间不喝酒,同时在个人的行为、待人接物及工作能力上都有了长进。
“2000年联合国公布的危害人类健康的十大因素中,酒被列为第五位。”郭崧是北京安定医院药物依赖科的大夫,谈到酒依赖问题显得忧心忡忡:“在中国由于酒属于合法饮料,所以对酒的滥用根本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其实酒也是一种软性毒品。有很多人有一种误解,认为只有高度白酒导致酒依赖,但对喝酒上瘾的人来说,就是啤酒也会导致依赖。”郭崧说随着近年来喝酒的人数和人们喝酒次数的逐渐增多,酒依赖患者数量明显上升。“酒依赖”目前已被正式列入精神病的一大类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和安定医院每个病房里都住进了酒依赖引起的精神障碍患者,这类精神病人已占到住院患者总数的近10%。
最让人们担忧的是“低龄酒鬼”的出现,“虽然酒依赖的发生与个体素质有关,但青少年更容易形成酒依赖。”郭崧不无忧虑地谈到,他们医院收治的病人中,最小的酒依赖患者仅有17岁,“这种情况在以前是少有的。这些小酒友的酒龄虽然只有短短的四五年,但是酒瘾与几十年酒龄的老酒友不相上下,为搞到酒钱,这些孩子欺骗所有的亲朋好友。有的孩子喝到辍学。”郭崧说这些孩子一部分是出于好奇心驱使,还有的是单亲家庭的孩子,由于承受不了父母离婚的打击,借酒消愁,不断加大酒量寻求刺激,结果染上酒瘾。由于不能控制饮酒量,最终导致各种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疾病。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疗,饮酒后造成的各脏器的疾病将伴随终身。“千万别小看这问题,这可是个社会问题。青少年的饮酒问题特别应该引起重视,这重视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比如电视中铺天盖地的酒广告,对孩子的影响会怎样?再比如我们经常看到几岁的孩子拎着瓶子替父亲换啤酒,我想告诉这些家长:这是在害孩子,是在犯罪。”
(注:文中酒依赖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