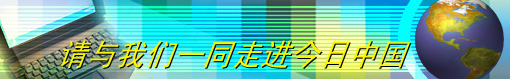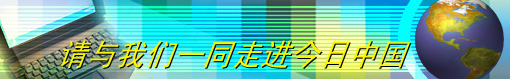“绿袋子”在行动
文/尔思 程 海
 |
| 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为"绿袋子行动"设计的海报以保护自然资源、实现循环经济为主题。 |
SARS在北京暴发后,普通百姓对公共卫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5月1日,北京安贞西里几十名市民上书市政府,要求封闭住宅楼垃圾通道,阻断疾病的传播途径,市政府也以超常的速度在一个星期内下发了《关于封闭居民楼垃圾道实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密闭贮运》的紧急通知,要求全市在一个月内封闭所有居民楼垃圾道。
6月9日,《北京晚报》的一篇“把厨余垃圾放入绿袋子”的报道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该文提出了用绿色有标识的塑料袋分装厨余垃圾(主要是剩饭、剩菜、鸡鸭鱼骨、择剩的各类蔬菜叶根、果皮等)、实行分类处理的解决办法。这就是从1996年就开始倡导垃圾分类的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提出的“绿袋子工程”。
地球村的八年“抗战”
1996年,一位美国的环保专家曾劝告涉足环保事业不久的廖晓义不要去碰垃圾分类。根据他的经验,垃圾分类是最难的,美国搞20多年的垃圾分类,还没有达到50%的分类率。如今,八年过去了,廖晓义仍在坚持,当年的归国学者和制片人,如今已成了“垃圾大嫂”,不知不觉,白发也爬上了鬓角。
廖晓义至今还记得,当年在中关村一条主要街道的公共汽车站旁边,那座大大的垃圾堆已经够刺眼的了,更刺痛她的心的是,那些熟视无睹的目光。在垃圾堆旁等车的人、来来往往的行人,似乎都没有看到这堆垃圾的存在,人们对此没有行动,甚至没有抱怨。
另一件让廖晓义大受刺激的事是“洋垃圾事件”。1996年洋垃圾冒充进口废纸闯入北京,激起了国人的义愤,然而廖晓义心中更多的是羞愧。我们为什么要进口废纸?中国人均森林资源匮乏,需要用废纸作为造纸原料。可是中国的废纸回收率很低,不得不大量进口废纸。仅1994年中国就进口废纸7万余吨,花去外汇近1亿美元。不光是废纸,中国每年都在进口其他种类的垃圾作原料,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尚未建立起自己的垃圾分类和循环经济系统。她和她的伙伴们通过调查了解发现,仅1995年北京市的垃圾清运量就达300多万吨,如果全堆在一起可以超过两座景山。这成千上万吨的垃圾山,都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有良知的中国人,不仅会为洋垃圾而义愤,也该为土垃圾而痛心。
廖晓义也因此找到了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之外的环保事业的第三领域:将环保引入大众生活的,倡导绿色生活。廖晓义和几位也是从国外回来的同伴们一起回忆中国垃圾分类的历史,分析国外垃圾分类的机制,呼吁国人“把垃圾分类的老传统捡回来”。“绿色生活,从垃圾分类开始”。
廖晓义志愿放弃了美国绿卡,因为她要留在中国搞环保,1996年,她创办了非营利性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从此,地球村与垃圾分类结下了不解之缘,地球村的“村史”和“大事记”也就与中国的垃圾分类进程紧紧连在了一起。这是八年的抗战,八年的坚守,每一个脚印,都伴着一个难忘的故事。没有进行垃圾分类的经费,廖晓义和她的同伴们就想办法从制片费中省下钱来印刷宣传资料,缺少专业人士,就发动志愿者们来工作。
“煞费苦心”的一段经历是在1998年,地球村在中国农业大学附近租赁了1.2亩的菜地种植有机蔬菜,为的是配合当时北京宣武区环卫局的生物垃圾处理。用来自垃圾分类试点社区所提供的生物肥料种植蔬菜,再把这些有机蔬菜送到提供有机肥的社区,让居民们真切地理解“循环再生”的意义。“我们种了好几种菜:黄瓜、西红柿、圆白菜……长得非常好,成熟后我们一起摘,然后送到槐柏树小区,也送到大乘巷,那时,我们特别有收获感。后来菜多得社区的居民吃不了,我们就用三轮车拉着菜上街去卖,成了‘非法小贩’。”每每谈起那段卖菜的经历,廖晓义都忍不住要笑,“当时我们地球村的工作人员都是漂亮腼腆的女大学生,站在街边上卖菜。也不会卖,一边卖菜一边向别人宣传环保,经常有人搞不清我们是干什么的,买完菜走出了好远还回头看我们。”
 |
| 廖晓义 |
最难的是在垃圾分类清运系统尚未建立健全的情况下,进行操作方面的沟通和推进,争取人们的理解。一次在首都师范大学做关于垃圾分类的演讲和倡议时,一位路人提出了质问:“你们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凭你们几个人能改变这件事吗?不要事情办不成反而耽误了这些大学生……”当时,廖晓义反问他:“假如你的母亲得了重病说无法医治了,你就不给她治了吗?不做事的人不要对做事的人妄下断言。”
廖晓义说:“虽然我们的力量是微弱的,但是一想到每天的垃圾量和污染都在增加,那么多有限的资源变成垃圾,那么珍贵的土地变成填埋场,我们就不能动摇,更无法放弃。"地球村不会放弃,还因为在垃圾分类的单行线上,地球村并不孤独,和他们一起坚守的,还有和他们一样的自然之子。
大乘巷的七年坚持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赵登禹路的大乘巷教师小区是一个在城市地图上很难找到的小社区,全区共有住户300余户,1000多口人。但它作为中国的“垃圾分类第一院”留在了中国公民环保的史册上。
经过一路打听,我们终于在一条小巷中找到了大乘巷教师家委会所在的那幢楼,陈淑芬老师一直在地下室的家委会等我们。去年陈老师已经从家委会主任任上退了下来,但在这里,陈老师永远都会被称为陈主任,因为陈老师自从1989年在西四中学退休后,就一直担任居委会主任,一干就是12年多,而且垃圾分类试点小区的建立和实施至今更是与陈老师分不开的。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国人经济水平的好转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生活垃圾的产量也增高了,尤其是一些白色垃圾,冬天大风一吹,塑料袋满天飞,废纸片什么的刮得到处都是,出去都睁不开眼。”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今年70岁的陈老师仍然记忆犹新。
但当时人们都觉得改善环境是政府的事,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可以参与进来。后来北京地球村在电视台上一个关于居民垃圾分类的节目引起了大乘巷居民的注意。小区一位叫王庭蕴的退休教师找到了地球村,找到了廖晓义,说她所在的社区家委会和居民愿意尝试垃圾分类处理,而此时地球村也正想寻找一个小区进行试点实施,于是廖晓义和她的同事便到大乘巷进行多次的演讲示范。经过十余天的准备,没有垃圾桶,家委会成员便拿出自己的年终奖购买了几个红色的塑料桶。1996年12月15日开始实行分类投放。三个红色的塑料桶矗立在小区内,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实施垃圾分类的居民小区。
刚开始,许多居民觉得太麻烦不愿分,参与率只有20%左右。陈淑芬和几位热心的大妈大婶逐家逐户进行发动,宣传实施垃圾分类的好处和意义。一段时间后,居民们从不习惯到习惯,再到习惯成自然了。居民们说:“垃圾分类确是举手之劳的事,而且这是利国利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之事,我们何乐而不为呢!”在这六年多的时间里,在小区家委会积极组织下,参与垃圾分类的住户越来越多,70%多的住户参与进来,他们共收集废塑料7000多公斤,废纸6000多公斤,减少垃圾量13吨左右。
现在,大乘巷的居民又面临新的问题,收集起来的废塑料如何利用,谁来运走。在开始的两年里,家委会自己想办法给废塑料找出路,塑料垃圾由于没有出路只好不分了,但其他垃圾,如废玻璃、废纸等的分类没有停止。现在他们又在琢磨着尝试社区堆肥,将厨余生物垃圾做成肥料,改善社区环境。西城区教委其他五个教师住宅小区1997年在大乘巷小区的倡议下都开展了垃圾分类,但由于收集起来的废塑料无人要,没有拉走只好暂停了,真是前功尽弃。
垃圾分类第一院,从1996年开始垃圾分类,如今已是第七个年头了。非典期间,廖晓义打电话询问社区情况,陈主任说是垃圾分类还分着呢,分类成了习惯,不分类反而不习惯了。“我很感动,大家为生命而忧虑恐惧的时候,他们仍然惦记着垃圾的分类处理。七年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坚守的其实是公共环境安全的防线,他们不也是坚守在一线的英雄吗?”廖晓义说。
中国第一各绿色社区
建功南里位于北京宣武区白纸坊,它在中国绿色社区的发展史上,算是个有功之臣。
1998年,地球村幸运地遇到了时任宣武区环卫局长的张鸿生。张局长选择了建功南里作为垃圾分类的试点,尝试性地引进了日本一台生物垃圾处理机,可以把居民生活中的厨余垃圾变成有机肥,同时还建立了垃圾分类站,将分类后的垃圾能够回收再造。
这是一个由政府、民间组织、物业公司多方合作的绿色社区试点小区,环卫局配置垃圾桶种类:厨余垃圾桶、废纸张、废塑料、废金属和玻璃、其他废弃物,共五个桶,全小区还设有一个废电池桶。环卫局还为小区每户配置两个分类垃圾篓。地球村组织了一系列的垃圾分类宣传教育活动,“让环保走进生活”、“让环保走进社区”的绿色社区理念,物业公司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专门的保洁员进行辅助性的二次分类。垃圾分类成了物业管理的内在部分。物业负责人戚主任在垃圾分类系统管理的基础上发展出社区环境管理体系,并获得了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标准的认证。
1999年4月,地球村、物业公司与宣武区政府有关部门共同建立了第一个绿色社区试点——建功南里绿色社区。绿色社区模式是指绿色建筑、节能、节水、垃圾分类、绿化的环保设施和公民参与机制,包括一个有政府部门、物业公司、民间组织和居委会及居民代表的联席会议、一支能起骨干先驱作用的志愿者大队;一系列持续性的环保活动和一定比例的绿色家庭。
2000年8月,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廖晓义向刘淇市长提交了“垃圾分类实施方案”和绿色社区推广建议,得到了市政府和奥申委的重视和采纳。9月,市政府召开绿色社区现场会,18个区县的近百位主管领导参观了建功南里绿色社区试点。
2003年7月12日,在北京申奥成功两周年的前夜,椿树园环境议事会成立,这是个在地球村帮助和街道办事处支持下成立的中国第一个居民环保团体。两年前,椿树园代表北京500个居民小区接受了国际奥委会评估团考察,受到评估团17位成员一致赞扬,为北京申奥做出了贡献,如今的居民议事会,又成为推动垃圾分类和绿色社区建设的新的希望。
七十六岁老人的艰难行走
垃圾分类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以居民社区的实施机制,一是清运系统的建立。当这两个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况下推行垃圾分类,其困难是可以想像的,然而,仍然有人在这样的困难中艰难行走。张志新,就是这样的一位志愿者。
 |
| 张志新说,其实居民家里进行分类并不复杂,像这样的小纸片统一收集起来就可以回收再利用了。 |
家住北京朝阳区樱花小区的张志新今年76岁。退休后,她非常关注环境问题,像水的污染、空气的污染、野生动物保护、沙化等环境问题都引起了老人的注意。她想为此做点什么,但又感到鞭长莫及。“看到长江江面上白沫子那么厚,野生动物被杀害,心里都很心焦,但是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又不能去保护野生动物,所以多数看过后也就这么过去了。”后来,在电视上看到介绍北京地球村做的“生活中的环保”和大乘巷垃圾分类的节目后,张志新心动了,心想:地球村多大呀?他们是怎么做的。但那时张志新不知道地球村在哪,也不知道大乘巷在哪个区,所以无法取得联系,但从此张志新就开始琢磨要在自己身边做一点对环保有利的事儿。
1997年的春节,在一次同学的聚会上,张志新认识了北京环保基金会会长江小珂。通过江小珂的介绍,张志新认识了从德国回来的环保专家李皓博士。正在为垃圾分类呼吁奔走的李皓给张志新提供了许多关于环保、垃圾问题的材料,使张志新认识到: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可以分类、可以回收进行资源再利用。从此,张志新找到了做环保事业的起点,并且把自己的目标锁定在“白色垃圾”上。
1998年3月份,张志新在电视上看到北京小学生“手拉手”行动(小学生把家里能卖钱的废品收集起来,卖了钱后捐给郊区贫困学校的帮扶工程)。张志新想,如果找到清运企业,能不能把小学生发动起来,让他们带动家庭收集白色垃圾,带到学校集中,找到清运统一清运,这样既好宣传发动,又好操作。有了这个想法,张志新找到住在小区内的北京化工大学附属小学的校长。这位校长听后立刻表示支持,这给了张志新极大的鼓舞。没隔多久,在李皓博士的帮助下,找到了愿意承当收运白色垃圾的北京蓝业公司。
有了“出口”之后,张志新在化工附小的支持下,以学校为点,家里有小学生的家庭,由学生每周一次带到学校;没有小学生的家庭就直接送到居委会,居委会再送到化工附小。在张志新的宣传倡导下,附近许多居委会也开展了收集白色垃圾,然后都送到化工附小来集中。就这样,从一个居委会逐渐发展到了六个居委会,她还发动了自己原来的工作单位--北京总工会,并通过自己的侄子发动了位于昌平区的中国电力科学院等多家单位参与进来。据粗略统计,张志新从1997年开始至今,仅在樱花小区就收集白色垃圾50余吨,不仅大大减少了环境污染,以70%的炼油率来算,为社会再生优质汽油30多吨。
白色污染显而易见,发动起来非常顺利,但由于中国目前没有完善的后期处理机制,环保企业发育不健全,所以为收集来的白色垃圾找到合适的出路成了张志新最头痛最艰辛的工作。
“蓝业公司下属有一个废旧塑料炼油厂,虽然用量较大,但居民点收集起来的废旧塑料毕竟有限,一次装一大车也没有多少重量,拉一次根本合不上成本,所以蓝业公司运了半年多后,就渐渐不怎么来了。小学校已经放满了不能再放,怎么办?”张志新又开始四处联系,“因为,我又不能欺骗小学生,把他们都发动起来了,最后说不做了也不行呀。我后来又找了一家新红欣保洁公司来负责清运,第一次来了一辆加长车,装得满满的,把积压的塑料全部给清运了,我的心又终于落下了,非常高兴,可第二天又有变化了。”
原来,第二天蓝业公司找来一辆大型压缩车,到学校一看没有了只好空车而返。当时张志新正在吃午饭,“听说后我赶紧放下筷子,想去他们公司给人解释一下,毕竟人家给拉了那么长时间。”但她并不知道蓝业公司的详细地址,只知道在安贞桥附近,电话是644开头,“我以为公司下面还有场,肯定是个很大的地方,很显眼,可走了一个多小时,找了好几条街也没有找到。”后来有人告诉她,附近有一写字楼,里面有几家公司。最后,张志新终于在写字楼里找到了蓝业公司,好个给人家赔不是,但最后蓝业公司还是停止了这项工作,只好靠新红欣负责清运。
然而,新红欣保洁公司没过多久也坚持不住了。“新红欣的经理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也非常热衷和看好环保事业,但干这件事大多都没什么利润,本来就是个小公司,资金有限,也渐渐撑不下去了。”在张志新等人的努力下,北京环保基金会先后资助新红欣保洁公司8000元,电视台一位做环保节目的主持人资助了5000元,张志新自己也给了5000元。就这样,靠大家的赞助新红欣又坚持了半年多,但靠资助继续清运也不是长久之计,解决不了公司的实际情况,1998年的夏天,新红欣保洁公司也撤出了。环保企业要想生存必须产业化。
由于无人清运,小学校内堆放白色垃圾的空地上不几天就满了,面对这些白色垃圾,张志新头痛不已,“我每天外出回来都到学校里去看看,那段时间愁得我经常睡不好觉。”张志新再一次四处求人,有的人碍于关系给拉一两次,但都干不长。后来,又相继找了四五家公司,每个公司都坚持半年左右,断断续续地坚持至今,其中的艰辛只能是当事者清楚。
“这些年我说的对不起呀、谢谢了、麻烦你们了,比我前几十年的总和说的都多,帮我清运垃圾的我天天都跟他们说谢谢,人家有了意见我又赶紧给人说对不起。有一家位于东四的公司,给我们清运了半年多。因为成本太高,他们没有用汽车,每次都是派三四个工人蹬着三轮车来拉。大夏天从东四蹬到这里,个个都满头大汗,我每次又给他们买饮料,又是一个劲地说谢谢,但最后他们还是不来了。”张志新微微抬着头,稍微停顿了一下:“其实我很理解他们,大家都不容易。干这个没什么利润,谁开公司都得吃饭吧。”
张志新再一次发出轻轻的、又是深深的叹息。这何尝不是所有参与垃圾分类的热心人士们的叹息。为此,地球村再次给北京市长写信,提出建立垃圾分类的多元化投资和市场运作机制的建议,建议政府制订对企业的支持、扶植和减免税费的政策(在服务区内,服务对象,每年每户交纳的垃圾保洁费、纳资和清运费划归企业使用,不得向企业征收管理费),以增加本领域的吸引力,并使现有企业不断壮大,迅速扩大分类垃圾正常回收、清运的覆盖面。非典之后,地球村又提出了“绿袋子计划”,希望这个话题能引起全社会更多的关注,为了中国的垃圾分类清运回收系统尽快建立,为了让张志新们不再叹息。
首倡“绿袋子”行动
 |
| 专家们提出:根治"白色污染"的根本,在于实现回收再利用。 |
2003年春天是难忘的,突如其来非典肆虐了京城,给人带来了恐慌的同时,也促使人们开始反思,更加关注公共卫生环境。北京地球村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进垃圾分类,地球村人经过一个多月的思考、准备、分析、走访专家商讨论证,到社区、市政管委、垃圾楼、垃圾转运站等地做了大量的调查采访,同时考虑到以往实施的垃圾分类存在分项复杂、标识不明和缺乏后期清运和回收体系等主要困难和不足,提出了“绿袋子行动”的设想。
绿袋子行动瞄准厨余垃圾,即以绿色有标识的塑料袋把占垃圾总量30%左右的厨余垃圾先分出来,因为这部分垃圾最容易孳生蚊蝇和病菌,污染环境。同时,彻底解决垃圾分类清运的问题,保证居民分类后得厨余垃圾变成有机肥和绿化土,而不是送往填埋场。绿色垃圾袋则可以成为一种进入千家万户的新的广告载体,鼓励企业的介入。
“绿袋子行动”提出后,得到了多家媒体和宣武区政府的关注。6月11日,由宣武区领导主持的“绿袋子工程”协调会在区政府会议室举行,并确定在宣武区12个居民社区共同实施。由政府各部门、企业、居民代表和民间组织组成的垃圾分类联席会,正在建立和完善。
埃克森美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已表示愿为试点社区的前期三个月的绿袋子和宣传资料“买单”。
作为奥组委环境顾问的廖晓义,希望绿袋子成为未来中国绿色奥运的一个亮点。垃圾分类“八年抗战”的同行们对于这项由民间倡导、政府支持、居民参与、企业配合的绿袋子工程,有了信心。只有携手,才能成功。只要携手,就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