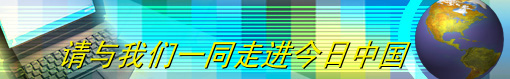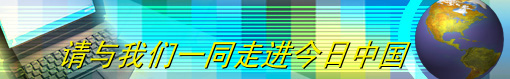周光召:曾为中国科学当家
文/李
妍
威震杜布纳
 周光召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54年研究生毕业后任北京大学物理系讲师。1957年,28岁的周光召被选派到苏联莫斯科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粒子物理的基础研究。
周光召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54年研究生毕业后任北京大学物理系讲师。1957年,28岁的周光召被选派到苏联莫斯科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粒子物理的基础研究。
周光召在杜布纳工作了4年,在这里,他展现出了杰出的物理才华:两次获得联合研究所的科研奖金,并发表了33篇论文,其中有不少成果引起了国际物理学界的高度重视。当时的国外报道称“周光召的成果震动了杜布纳”。
他自己后来回忆说:“那时确实是我非常努力的一个时期。一是那里的环境更好一点,另外也不能让苏联人看不起,所以必须努力。”
两弹元勋
1961年2月,周光召回到祖国。他担任了二机部九院理论部的第一副主任。与邓稼先、彭桓武等人一起,全心投入于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之中。从此也开始了他长达19年隐姓埋名的国防科研生涯。而此时的国际学术界则流传着他“因飞机爆炸去世”的消息。
在两弹的研制过程中,周光召再次显示出了他杰出的物理才华。
在原子弹设计初期,有一份苏联总顾问临行前口授的简要记录,其中的数据引起了中国科学家很多的争议,周光召花了大量的精力,进行了“最大功”的计算,修正了苏联专家的重大错误,也结束了一场争论。
1964年10月15日,在罗布泊高高的铁架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已经安装就绪,等待起爆。就在此时,在北京留守的周光召却突然接到前方的指示,要求他把一些重要的过程重新计算一遍。而当时大多数技术数据已经被送到了试验基地,于是周光召就凭着记忆对早期工作进行了重新演算,并在回复有关领导的备忘录上签字“建议按原计划试爆”。
随着原子弹的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也试验成功,成为继美、苏、英之后第4个掌握热核武器的国家。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周光召也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后来在谈及自己在研制两弹中的作用时,周先生的态度却极为淡然。他说:“我一直认为,原子弹也好,氢弹也好,远远不是几个人的事情,是十万人以上的共同的工作。而且它是不能出一点差错的,一个螺丝钉不对了都要出问题的,所以在这里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贡献,而且每一种贡献在我看来,都很难分得出它是重要还是不重要。没有出问题,就表示我们都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重返理论研究领域
 |
| 1983年,周光召在美国访问讲学时与李政道、杨振宁合影。 |
1979年8月,周光召重新回到理论研究领域。1980年他应邀到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和加州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当时他被美国物理学界视为中国理论物理学界的代表人物,美国物理学会主席专门为他举办了学术会议,许多国际知名物理学家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如此隆重地接待一位外国科学家,在当时的美国物理学界也是罕见的。
周光召在后来谈到自己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重返理论物理研究前沿的时候,曾把自己比作是小学生,他说:“在那个期间,就是利用美国信息比较畅通的条件,就像一个小学生那样再从头学起。”
在美国的那些岁月里,周光召不仅使自己的研究水平重新回到了世界前沿,而且他还为中国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促成了中国学者赴美学术交流;二是帮助中国物理学会恢复了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
在美国完成教学和研究以后,周光召来到西欧原子核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这个中心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经邀请他去做研究工作,在隐姓埋名了近20年后,周光召才来到了这里。钟情于学术的周光召在理论研究领域好像又回到了生机勃勃的青年时期。他回忆说,当时最主要的想法就是想带一批学生,把这个“科学前沿”能在中国搞上去。
但是就在他开始学术征程之时,从国内连续来了多次电报召他回国。起初他还以访问尚未结束为由,希望延期,但后来大使馆的参赞也催他早日回国。后来他说,这十二道金牌把他后半生的道路完全改写了。
回国后,周光召才知道自己被选为了中共十二大的代表,同时被任命为中科院理论物理所所长,他回忆说:“那个时候我才真正感觉到,又发生了一个人生的大转折。我本想像小学生那样努力学习,从1983年开始花了三四年的时间学到一个程度,又可以做一些论文在杂志上发表了,但又遇到了这样一个情况。那时候钱三强动员我,科学院其他一些领导也来动员,我就到科学院来了。”
中科院十年
从1987年开始,周光召担任了十年的中国科学院院院长。在这十年中,他领导了中国科学院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把主要科技力量动员和组织到为国民经济服务的主战场,同时,保留一支精干的队伍进行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创新。”
在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问题上,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院两制的方针,这是中国科学院在打破僵化封闭的旧体制道路上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
他积极倡导中国科学院与高校科研之间的联合,成立了不少联合实验室。为加速改变高校与科研单位脱离的现状做出了创造性的工作。
但是在一开始,工作的难度却远远超出了想像。
他在回忆那段经历时说:“当时最困难的是观念的转变,因为要改变原来的体制和原有的观念是非常之困难的。再有就是要跟企业相结合,当时这种结合相当困难,他们不需要,也没有积极性。所以我们只好组织一批科学家从小到大来发展这个高技术产业。那里候国外已经有了很成熟的经验,像硅谷什么的,所以在北京的中关村和全国各个地区都有一批科学家站起来,但这个时候立刻又产生了很多观念上的冲突,比如说做基础研究的或是做比较正规研究的这批人,瞧不起出来办产业这批人,觉得他们做研究不行所以才去办企业……”
“另外,确实做高技术产业开始时非常困难。他们几乎要从学做买卖开始。那个时候总共就有50万块钱,要自己扛这么多东西到外头去卖,加上没有经验,还上当受骗,这种情况都有。这十年我不知道挨了多少骂了……而且那些做企业的人,他们非常辛苦,还被人看不起,所以要经常给他们打气,鼓励他们做一番事业……”
当年被周光召逼下海的王震西和柳传志,今天已经是中国著名高科技企业的老总了,回想起当年的情景时,他们表达得最多的是对周院长的一份感激之情。
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思考
 |
| 周光召接受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栏目主持人曾涛采访。 |
今天的周光召在中国科协主席的任上,继续思考着中国科技发展的长远战略。
作为经历过两弹一星时代和改革开放时期的科学家,周光召对中国科学体制的下一步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我想中国的科研体制中一个最佳的状态是:企业的科研力量要大发展,它必须要成为产业自主知识产权的最主要的根据地;然后是大学,在大学里面要大量发展基础的研究,同时要把最新的科研成果交给学生。那么不管大学也好,研究所也好,它都应该不断地向社会、向企业输送掌握最新科技成果的人才。其中除了直接输送到大企业中间的一部分之外,要有相当一部分促使他们出来创业,从小规模的最新的高新技术开始,逐渐地发展壮大,这也是国际的一个规律。那么这种人员的流动,才促使这样的研究所、大学有更多的活力,也会腾出更多的位置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进入……
风雨几十年后,周光召先生在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时,用三个字做了概括:平常心。 “我从来没有去后悔什么事情,也没有因为安排我做另外一件事情就使我非常不安。我想应该有一种平常心。有些事情要我来做时,就尽自己的力量来做好……”
(文章及图片由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栏目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