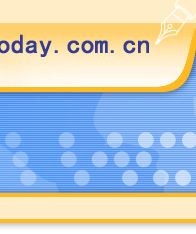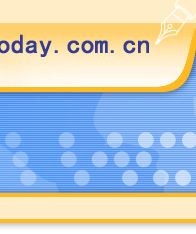杨宪益的翻译人生
文图/本刊记者 李国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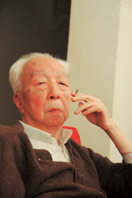
《离骚》、《资治通鉴》、《红楼梦》、《鲁迅选集》……这些著作的英译本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而率先将它们介绍给世界的中国人便是杨宪益。
杨宪益,翻译界的大师,熟悉这个中国人名字的外国人远多于中国人。一个让金发碧眼的痴男怨女们读懂中国爱情故事的人。
北京什刹海的银锭桥上游人如织,人声鼎沸。几百米开外,杨宪益独院的老式木门一关,就隔开了万丈红尘、市井喧嚣。
执着于文学翻译
不得“对我来说,翻译就是一种职业。我要翻译我更喜欢的东西”,杨宪益说。
杨宪益上世纪30年代在牛津留学时就认识了钱钟书。解放初期,钱钟书被调来北京主持《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翻译工作。杨宪益当时还在南京,大约在1950年或1951年,南京统战部通知他,说北京的钱钟书也推荐了他去,共同翻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杨宪益当时认为自己翻译政治性文章很外行,担心做不好。所以他婉言拒绝了,说自己更喜欢翻译文学作品。
不久之后的1952年底,杨宪益被调到北京参加刚成立的外文出版社工作。
杨宪益来到了外文出版社,是因为社长刘尊棋准备有系统地向外国介绍中国文学,从《诗经》开始拉了一个单子,一共有100多种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这正是杨宪益兴趣、爱好所在。在杨宪益主持的《中国文学》翻译了很大一部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有的出了单行本。《中国文学》杂志对全世界发行,那时每一期发1万多份。主要在巴基斯坦、印度和美国、英国。
不过《中国文学》的翻译计划并没有完成,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翻译工作几乎停滞不前。"很可惜呀,"杨宪益吐着一口烟,缓缓地说:“如果有机会多翻译一点鲁迅我还是很高兴的,《坟》就没有翻。”
“文革”结束以后,西方社会对中国形势非常关注,杨宪益建议出版英文版的中国文学丛书----“熊猫丛书”,专门介绍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作品。该丛书出版了近百本,既有《聊斋志异》《老残游记》等古典文学作品,也有《边城》、《芙蓉镇》等“五四”后到20世纪70、80年代的作品。这些薄薄的小册子,价格便宜、容易翻阅,在当时的西方社会非常畅销。
曾经有段时间,组织上想起杨老会希腊和拉丁文,把他调去译荷马史诗,后来为了翻译《红楼梦》,出版社又将他拉回来。《红楼梦》至今也只有两个全译本,一个是英国人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一个是杨宪益的。
夫妻合作 翻译人生
在翻译界,做中文外译工作的人很少,像杨宪益、戴乃迭这样夫妻合作的,更是绝无仅有。他们不仅翻译了《红楼梦》,还将《鲁迅文集》、《史记选》等上百部中国文学作品译成了英文。作为主要译者和多年主编,杨宪益、戴乃迭共同支撑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数十年,自1951年创刊以来,这份刊物一度是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的惟一窗口。
杨老是在牛津认识了他的爱人Gladys Margaret Tayler,中文名字戴乃迭,她的父亲是一名英国传教士,出于北京的戴乃迭,6岁才回英国,是牛津大学历史上第一个学中文专业的。
“那时我们常一起玩,一起划船,牛津和剑桥每年都要举行划船比赛,她还参加过。”杨老陷入了无尽的回忆中,“她是个很单纯的人,说话很直率,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也很爱国。”后来他们夫妻经常开玩笑说,戴乃迭喜欢的不是杨宪益,是中国传统文化。戴乃迭汉语讲的不是很好,她经常把“这”怪罪于杨老英语讲得太好了,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讲英语。
老先生坐在沙发里,他缓慢而认真地回忆,声音、目光和神情都很柔软,像一壶陈年花雕,醇厚而温婉。
杨宪益夫妇40年代回国初期,不断地在中国西南的各个城市之间奔波,生活非常辛苦,戴乃迭的工作也一直不顺心。直到1943年,一位朋友推荐他们去了梁实秋领导的国立编译馆,当时的国立编译馆只有从事将西方经典翻译成中文的工作,还没有人进行中文外译的工作。事实上,自19世纪末以来,与外文中译的繁盛景观形成鲜明对比,中文外译一直就显得势单力薄,直到20世纪四十年代,西方人对中国史学经典还几乎一无所知。梁实秋希望杨宪益夫妇能去领导一个部门,专门从事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的工作。
这样,杨宪益成了将中国传统文化系统向世界推介的第一人。在当时的国立编译馆,杨老选择了从难度较大的《资治通鉴》开始。很多外国人根本都还没看到过《资治通鉴》。那时总共译了近40卷,从战国到西汉那一段。
杨老考虑去国立编译馆,重要有原因就是,虽然戴乃迭也懂中文,但教书到底吃力,一起作翻译对她比较好一点,比较轻松。 数十年来,所有的翻译都是杨老跟爱人合作。“我拿着书直接口译,她打字,打得飞快,然后再修改。”在大跃进时期,什么都要快,他们的翻译也不例外。最快的时候,翻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要求越快越好,结果我们一个礼拜就译完了,像这种情况完全得益于杨老直接口头翻译,戴乃迭打字后再修改。杨老说花的比较长去翻译的是《宋明平话小说》,还有就是《史记》。
译事和逸事
刚解放那一阵,毛泽东曾邀请文化界人一起坐坐。一次在怀仁堂,有几十个人,周恩来很客气地向毛泽东介绍说杨宪益是翻译《离骚》的,翻译得很好。毛主席一边跟他握手一边问,《离骚》也能翻译吗?杨老当时很简单,就回答说:“主席,什么都能翻译。”
1968年,杨宪益夫妇被怀疑是英国特务,进了监狱。被抓进去的当天晚上,杨宪益在家里喝了半瓶曲酒,所以一进半步桥监狱,他就要别人挪个地出来睡觉,旁边的犯人闻到他身上有酒味,说好香啊,问杨宪益是不是喝醉酒闹事被抓的,他说不是,然后就睡了。老朋友黄苗子后来写了首《咏酒呈宪益》的打油诗,有两句是:十年浩劫风流甚,半步桥边卧醉囚。
出狱后,杨宪益夫妇就又一心扑在中国文学的翻译上,一天十几小时。实在太累了,戴乃迭就把笔搁一搁,往外走,跳一会儿绳,杨老自己就会拿个烟在那儿抽,看着戴乃迭在那儿跳。
杨老与钱钟书之交淡如水。有一次《中国文学》英文版突然要杨老翻译司空图的《诗品》。译完之后,决定送去请钱钟书审定一下。钱钟书看了送来的译稿,提了点意见,两人也没有见上一面。1989年杨老曾写过两句打油诗,是“有烟有酒吾愿足,无官无党一身轻”。钱钟书不知道在哪里看到了或听人说起,忽然给杨宪益写了一封信,说很欣赏他的句子,但觉得“吾愿足”和“一身轻”对得不够工稳,建议改为“万事足”和“一身轻”,问杨老如何。
杨老轻轻地吸上一小口烟,缓缓地吐出一圈烟雾,像是在述说着别人的点滴,……
杨宪益,1914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泗县。1936年进入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研习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英国文学,获希腊拉丁文及英国文学荣誉学士、硕士学位。1940年毕业回国后历任重庆、贵阳、成都等地大学教师,1943年起供职于重庆北碚国立编译馆,开始翻译生涯。1952年调北京外文出版社,后任《中国文学》主编,并兼中国作协理事、名誉顾问和中国文联委员等多项社会职务。主要译著:包括《史记》、《资治通鉴》、《楚辞》、《长生殿》、《牡丹亭》、《宋元话本选》、《唐宋诗歌散文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十五贯》、《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老残游记》、《鲁迅全集》等百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