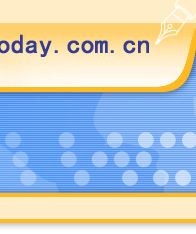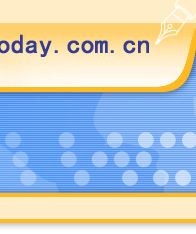和平的使者 平和的大家
--追思爱泼斯坦老人
文\张子扬
 爱泼斯坦老人辞世前的绝笔之文,也许是应我之特别请求,为我的一本名曰《江南问水》的集子所作的跋:《和平的祝福》。记得那是2004年8月1日,他还在北戴河休养,竟不嫌弃我的打扰,为我的一本集子作跋;这里我还要说,尽管他是按照序写给我的,而我事先就说好用于书后的跋,是跋而不是序,他知道了以后,实在是不在乎这一点,还很快同意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主管主办的《中国红十字报》发表了。
爱泼斯坦老人辞世前的绝笔之文,也许是应我之特别请求,为我的一本名曰《江南问水》的集子所作的跋:《和平的祝福》。记得那是2004年8月1日,他还在北戴河休养,竟不嫌弃我的打扰,为我的一本集子作跋;这里我还要说,尽管他是按照序写给我的,而我事先就说好用于书后的跋,是跋而不是序,他知道了以后,实在是不在乎这一点,还很快同意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主管主办的《中国红十字报》发表了。
老人90岁大寿的前几天,我们曾参加了《今日中国》杂志社在“和苑”举办的一个笔会;正因为事先知道了这些情况,老人才在《和平的祝福--序张子扬〈江南问水〉》文尾写道:“欣闻最近在北京朝阳一别墅区内的绿草坪上,众多国家使节纷纷以本国文字和汉语译文作出了精道而别致的祝福语,由金属牌镶嵌在一个个石敦上,共同以双语发出对于和平的企盼,使这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人文景观,名曰:‘`和苑’
。张子扬乃《和苑赋》之执笔者。”
坐着轮椅,老人高兴地在“和苑”度过了快乐的时光;他的夫浣碧阿姨在一旁笑着评论道:“看,你们这两个一老一小,一个太腼腆,一个太能说。”当时我俩呢,腼腆的仍旧腼腆着,能说的却不知该如何说了。老人为我的书作推荐,那才叫能说呢:“这本书叫《江南问水》,这一切都表明,电视文艺,文如其人,艺无止境。愿我这位小朋友笔健,为国家和人民--多著文、多导戏,更加勤勉地多出上品!”
老人不会也没有忘记,我们相识在世界和平年,即1986年。全人类对于世界和平的祈求与向往,促成了实在太多的历史性机遇。老人那年触了一次“电”,与此同时结识了作为青年导演--CCTV的我。电视艺术,主要依靠戏剧和晚会架构起引人入胜的广阔舞台。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的我,那个时期似乎正热心于中央电视台的大型文艺晚会。当电视文艺导演伊始,竟弄了两台风格别致的晚会。第一台CCTV·英语元旦晚会和第一台CCTV·法语春节晚会。
使老人进一步了解我的契机还在于,我与他的挚友坤净齐啸云为忘年交--我写报告文学《角儿涅磐》披露了戏剧怪才李保田之后,又写报告文学《啸傲菊坛》,披露了女包公齐啸云的人生坎坷和艺术风采,其中还揭示了老人与齐啸云的多年友谊。我没有问过老人对这两篇报告文学印象如何,但他曾说--“我更知道,这许多年,张子扬出了几大本诗文集,从跨文化国际交流、固守与拓展文化版图、后戏剧到报告文学、诗和理论札记,足足有洋洋上百万言,将影视理论与实践浓缩在了如诗一般的
‘行’与‘思’--这两个字上。”他鼓励我。
那时候北京昆仑饭店尚未完全竣工,我所执导的CCTV·英语元旦晚会拍摄现场设在那里。后来老人回忆说:“看似平常的‘Yer’和‘No’经电视文艺工作者之手,缤纷的舞台,和平的主题至今仍萦绕于我的心怀,对张子扬的印象和与他的交往,也极自然平和的开始了。我是那个晚会的三个特邀嘉宾之一,另两位,一个是英国驻华大使希思,一个是中国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我们在时任CCTV主持人彭文兰的问话中,抢答‘Yes’和‘No’,颇为有趣。”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此刻,我写这篇诔文的时候,离我们相识足有20年,离他辞世整整一年。那时候30岁的我,如今已50岁,古人都已知天命之年,我却总有经验不足、有待成熟的感觉。而我的成熟的偶像之一就是这位文科的白求恩--爱泼斯坦。
在这20年的时间里,我们保持联系的方法是,他和夫人婉碧阿姨,每年过年都寄贺卡给我;而我,也把精心设计甚至手绘的贺卡寄给他们。我从这淡如水交往中感受到,像他一样从战争背景中走过来的国际主义者,超乎寻常地喜欢现代人对于和平的深刻领悟与认同。他的汉语表达并不娴熟,却已世界公民的态度叮嘱过我,要以电视文艺作品和电视文艺理论,全方位地诠释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明晰地阐述和平“Yes”和“No”。他甚至强调说,电视文艺的有关理论当然不仅仅是哲学与美学的问题,还关涉在互联时代,电视这一艺术门类的大覆盖与大走向。
现在说来也真是的,既然他可以幽默地叫我“小老”朋友,我是否也可以将他的文章称为“序跋”呢?我的确是他老朋友中的小朋友、小朋友中的老朋友;他呢,一生,充满矛盾又始终不渝,一个犹太人,入了中国籍,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贡献了自己奋斗的一生!假如他的一生好比是一本书,那么,也正所谓,他微笑,他腼腆,他包容,他厚重,他有怎样的跋就有怎样的序,他有怎样的序就有怎样的跋,他是:和平的使者,平和的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