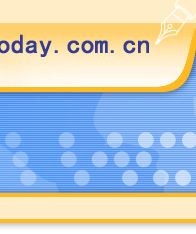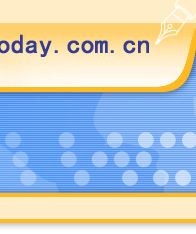“天路”从我家门前穿过
特约撰稿 冯建华
铁路修进被称为“世界屋脊”的西藏,这是人类铁路建设史上的伟大创举。美国现代火车旅行家保罗·泰鲁在《游历中国》一书中写道,“有昆仑山脉在,铁路就永远到不了拉萨”。
青藏铁路终于要全线通车了!从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提出最初设想,到历经新中国几代领导人的几番沉浮决策,前后花费了近百年时间。它的全线贯通,必然具有跨世纪意义。
对于这条“钢铁动脉”,人们赋予了它一个美丽的名字--天路。
7月1日,青藏铁路通车前夕,记者驱车对青藏铁路进行了一次全程实地采访,行程2000多公里,历时12天。了解沿途老百姓怎么看待青藏铁路,这条铁路又给老百姓带来了哪些影响,是我们此行目的之一。
好奇、模糊、兴奋……
沿途百姓对这条宏伟铁路充满了复杂的感情。
“坐火车应该像飞一样!”
说起家门口即将开通的青藏铁路,说话比较腼腆羞涩的藏族中学生平措顿丹,眼神里立刻充满了兴奋的光彩。
“坐火车应该像飞一样!”平措顿丹脱口而出,语气里听不出任何夸张的成分。
16岁的平措顿丹,是西藏自治区堆龙德庆县嘎龙乡一个普通牧民家庭的孩子,他的家离西藏首府拉萨市只有30公里,这是他去过的最远地方。平措顿丹从来没有看过火车,在他眼里,“那么长那么快”的火车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平措顿丹的这种经历和想法,在他所在的村庄很有代表性。当记者与平措顿丹交谈时,他周边围了一二十个年龄相仿的孩子,他们都没有亲眼看过火车,更没有坐过火车,但对火车通往的外面世界充满了向往。因此,当得知青藏铁路已修到家门口时,平措顿丹与村庄里的几乎所有男女老少,怀着朝圣般的心理迅速“涌”向了铁路修建现场,只希望能亲眼目睹火车这个神奇的庞然大物。
平措顿丹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穿着打扮比较时髦,显得活泼可爱,如果不是说着一口纯正的藏话,实在难以把他与藏族牧民孩子的形象等同起来。他周边的孩子也大多如此。长期以来,藏族牧民的孩子往往如他们的父母一样,整天穿着油渍斑驳的藏袍,憨厚中带有几份木纳。显然,这一形象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火车没通的时候,我们走出西藏很困难。现在火车通了,我希望坐火车去外面上大学,看更大的世界。”显然,伴随着火车的开通,平措顿丹的梦想也奔向了“远方”。
可是,与平措顿丹相比,他45岁的叔叔四珠却显得心情复杂。
“修铁路凿洞把我们的山脉破坏了,这也许给我们带来不幸。而且,铁路通车后,我们的房屋也会被震坏。” 四珠神情认真地说。这位以游牧为生的藏族汉子,有着藏族牧民典型的黝黑皮肤,满脸沧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很多。不过,在他看来,对于整个西藏而言,修铁路应该是件好事,因为“西藏经济太落后了,修铁路可以带动经济发展。”当问到具体原因时,这位从来没有见过火车,也没走出过自己牧区的牧民嘿嘿一笑,低声说,“我不知道,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铁路姻缘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是分两个阶段修建完成的。从青海省首府西宁至昆仑山口格尔木的前段铁路早于1979年9月铺通,并于1984年5月1日正式运营。由于资金、技术等方面因素的制约,从青海省格尔木至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的后一段铁路在时隔22年之后的2001年6月才得以正式开工兴建。在这段时期内,格尔木逐渐成为进出西藏的交通枢纽,大量物资正是经此地中转运往西藏。
格尔木,蒙古语意为“河流密集的地方”。这里矿产资源非常丰富,面积5600多平方公里的察尔汗盐湖就位于格尔木境内,是中国最大的钾肥基地,年产量超过400万吨。铁路修到格尔木后,丰富的矿产资源通过火车运往全国各地。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地处青藏高原腹地的格尔木,从当初一个牧民放羊的戈壁滩迅速成长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城市。
“格尔木完全是在铁路通了以后发展起来的,以前我们吃的是腌菜,住的是大棚,火车通了以后,生活用品丰富多了,现在内地城市有的,我们这儿基本也有。”蒙古籍大姐乌兰深有感慨地回忆说。
在格尔木土生土长的乌兰,对铁路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1983年10月,格尔木火车刚刚修通不久,十几岁的乌兰就坐上了火车,去往格尔木所在的海西自治州首府德令哈市。她至今清楚地记得,当时火车
还是由铁道兵负责运营,车上的椅子全是木头的,300公里的路程跑了12个小时。不过,待两个月之后返回格尔木时,火车已交给地方政府接管,火车条件也改善多了,用乌兰的话来说,就是“和现在的火车差不多”。
乌兰是牧民的孩子,祖辈世世代代以游牧为生。与其他牧民孩子一样,乌兰在10岁的时候,就离家去寄宿学校上学,从此开始了独立生活。父母以游牧为生,行踪不定,一年很少有机会去学校看望年幼的孩子。乌兰说,对于牧民孩子来说,这一切太正常了。
在乌兰幼小的心灵里,很早就萌发了一个强烈的念头,就是一定要考上学校,走出牧区,脱离祖辈那种艰苦的游牧生活。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乌兰终于如愿考上了德令哈市的一所卫校。在当时,这对于一个以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来讲,是相当来之不易的。据乌兰讲,当时在卫校60多人的班级里面,只有4个是少数民族学生。3年后的1986年,乌兰卫校毕业,进入格尔木市人民医院当上了一名护士。
在上学3年时间里,乌兰大多是坐火车往返,对铁路自然是感情深厚。发展到后来,她还结下了一段铁路姻缘。初中毕业时,乌兰的初中同学后来成为其丈夫的红英并没有考上学校,只能回家待业。不久,火车修到了格尔木,当地政府面向全社会招考火车站工作人员,经过竞争激烈的考试,红英被录用了。
与乌兰一样,红英也是蒙古族牧民的孩子,被铁路部门录用后,他的命运同样发生了较大的转变。而对于身处“爱情海洋”的乌兰而言,坐火车去上学,自然感觉到更加幸福和亲切。可以说,这条铁路见证了当时这两个年轻人的爱情,并最终促使他们走向婚姻的殿堂。
铁路上的工作经历,使红英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他意识到,火车通了之后,格尔木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但与此同时,由于高原地区的生态十分脆弱,环保在当地日趋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红英认为这里面蕴藏着一个潜在的商机。于是,在铁道部门工作了近20年之后,红英决定停薪留职“下海”经商,从事荒滩种草工程,如今一干就是10多年。2005年,由于社会信誉好和工程质量较高,红英被授予青海省“五四青年奖”,这是当地政府对青年才俊的最高褒奖。
丈夫经商后,家庭日渐富裕起来,乌兰干脆回家当起了“专职太太”,现在她的首要职责是教育孩子。“越来越多的火车来了之后,内外交流的机会更多了,各行各业的竞争也会越来越厉害,我希望孩子比我们更有出息,走得越远越好。”乌兰坦言。
火车是未来生活的希望
巴尔登,37岁,蒙族牧民,他的15平米大小的蒙古包安扎在离青藏铁路大约200米的一条小溪旁,距离格尔木市大约100公里。时,坐在“家”里,巴尔登能看见火车疾驶而过。对于这条铁路,见过一些世面的巴尔登可以说是既“爱”又“恨”。
巴尔登是今年2月份游牧到此地的,5个月之后又要搬走。他目前养了300多只羊,而火车铁路正好从他的牧区横穿而过。“铁路正好挡住了我的羊,虽然铁路给羊留了通道,但它们一时间很难适应,前些时候还经常乱蹿到铁路上,搞得我提心掉胆。”巴尔登说。
巴尔登有着一个很特殊的家庭。他的母亲是蒙古族,父亲是汉族,他随母亲登记的是蒙古族,可他娶的是一个藏族老婆,而他的哥哥娶的又是一个汉族姑娘。“我们家是民族大团结的最好体现。”巴尔登半开玩笑地说。
巴尔登现在与哥哥嫂子3个人一起在外放牧,他的老婆则带着自己两个孩子以及哥哥的两个孩子在106公里外的定居点上学。他们在定居点盖了4间砖木结构的瓦房,生活条件还不错。“今年国家免掉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全部学费,孩子上学没什么负担。”巴尔登说。
巴尔登的生活十分简单,早晨六点起床后,给小羊羔喂奶,9点左右吃完早饭出去放羊,下午6点左右回来,一天大多吃两顿饭。在外放养时,最大的娱乐就是收听广播。巴尔登说,由于茫茫戈壁滩上接受到的频道有限,能收到的节目他都爱听,其中听得最多的是经济类的节目。巴尔登在蒙古包里装了一个简易太阳能发电机,但只能够提供基本的照明,无法带动电视。因此,到了晚上,巴尔登只能用睡觉来打发漫漫长夜。
“其实现在牧民完全可以装高压电,晚上能收看电视,可我们懒得装,因为经常搬家太麻烦了,一不小心就把电视磕坏了。”巴尔登解释说。
巴尔登一家的年纯收入达到了2万多元,这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种地农民的收入。与过去相比,巴尔登的生活好多了:以前放牧大多是徒步或者骑马,现在改用摩托了;以前放牧与外界几乎隔绝,现在普及的手机电话,让巴尔登随时能与远在上百公里之外的家人联系;以前搬家大多用马车,现在用上了小型拖拉机,所有家什一个车足够了,随时都能搬走这个“家”。
“现在生活条件是好多了,但说实在的,我并不愿过这种单调的游牧生活。”巴尔登坦言。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外在的压力。这就是铁路通了之后,国家会更加注重保护青藏高原的生态,从而加大退耕还林的力度,会采用建定居点的方式,逐渐减少游牧的范围。
“我们必须要有长远打算,可以这么说,现在就是我们积累资本的过程。”巴尔登说,经过仔细盘算,他把未来的生活与火车联系在了一起,因为只要火车通了,运输成本就会下来,到时做的生意应该很多。巴尔登透露,近几年牧民盖房定居的会越来越多,他初步打算利用火车做些空心砖等建材生意。
“火车通了,我想谋生的机会肯定会多起来,只要人肯动脑筋,找碗饭吃应该不难。”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巴尔登颇有自信地说。
铁路给传统产业带来的冲击
青藏铁路开始修建后,马正强便来到青藏铁路沿线做起了运输生意,专门跑格尔木到拉萨这段路程,开始做货运,后来做客运,如今已5年有余。
“修铁路的时候,别提生意有多好,有时一天跑好几趟,说实话,钱是赚了不少。”马正强笑眯眯地说。
34岁的马正强,来自于与青海省临界的甘肃省,东乡族人,如今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由于忙于做生意,马正强很少回老家看望老婆和孩子。只要每天有钱赚,马正强很少感受到与家人的分离之苦。
但是,这一切随着青藏铁路的即将通车而发发生了改变。“铁路通车后,很多人进藏会选择坐火车,那时生意肯定会差很多。” 马正强叹口气说。不过,他对此已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到那时真不行,大不了回老家重谋生路。”
与马正强相比,回族餐馆老板马从德对青藏铁路即将通车更是充满了满腔“怨气”。
马从德的餐馆位于青藏铁路沿线著名风景点玉珠峰的对面,修铁路的时候,这里人气很旺,于是,很多餐馆便应运而生。据马从德讲,最高峰的时候,这块“巴掌大”的地方冒出了40多家大大小小的餐馆,可生意还是依然红火。
发财心切的马从德当然不想放过这个机会。一个多月前,他迅速开起了一家餐馆,还附带一个汽车修理场。可是,他没有考虑到的是,火车即将开通,很多工程技术人员已撤走,这里又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因而,在马从德开饭馆的这短短一个月时间里,这里的40多家餐馆迅速锐减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也大多只能勉强维持度日。
现在马从德还抱有一丝幻想,就是作为铁路沿线一个主要风景点,餐馆对面的玉珠峰下面设了一个观景台,18公里外还设了一个客运站,马从德现在指望火车通了以后,能吸引一些游人来到此地。
“这只是一种假想,谁知道事实会怎样,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戴着墨镜透出几分滑稽的马从德耸了耸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