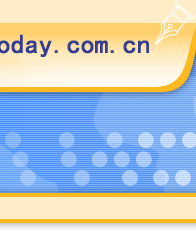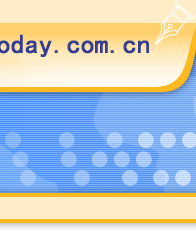新旧时代下的自主招生
文/思故门
“‘庄周化蝶’反映了庄子怎样的价值观念”、“你看到交通事故或者斗殴会怎么做?离开还是留下帮助解决?”你可能不会相信这是大学招生的测考试题。日前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人民大学等高校的自主招生测试颇引人注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自主招生程序》规定,高校应组织专家组对考生材料进行审查,并在进行面试等相关测评、考核后,提出候选人,并由试点学校招生领导小组审核后确定入选考生名单,考生在高考结束后可降低分数线录取。近年来参与自主招生的学校范围逐渐扩大,至今已达53所。如复旦大学已在筹建一个由150位专家组成的面试组,每名学生将分别接受5位专家的面试,专家组的意见将左右学生是否被录取。
自主招生正在成为热门话题,但从历史上来看,这种招考形式并不新鲜,中国大学建立伊始即采取此种形式,并施行数十年之久。自京师大学堂建立以来,高等教育体系内部就国立、省立、私立、教会大学并存,因此直至1932年高校的入学考试均由各校自己进行--学生自由报考学校,校方组织招生委员各自行考试并分别录取。这种招生竞争极为激烈,如1922年北京大学投考者2488人,录取只有163人。而清华自1911到1921年十年间,只招收约1500名学生,肄业及开除者均各在三百人以上,最终毕业的只有636人。
各校因专业布局、治学理念及教学风格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考试方式。以1929年国立大学本科生入学考试科目为例,当年北京大学科目为国文、外语、化学、中国历史、外国历史五种,而报考中山大学则需考国文、算学、物理、伦理学等十门科目。同一科目之内出题体例也不一致,如北京大学、北洋大学国文科目只需做一篇命题作文即可,武汉大学还要考察填空、造句并将一首诗歌改写为散文。即使题型一致的部分,考试内容也大相径庭,鲜明地展示了各个学校不同的风格。北京大学甲部国文试题是“清季曾李诸人提倡西学,设江南制造局,翻译科学书籍甚多,其中不乏精深之作,何以对于当时社会影响甚微?试言其故”。乙部的题目是“清儒治学方法,较诸前代,有何异同?试略言之。”而同年北洋大学国文试题则是“青年切实读书即是社会繁荣之基础说”,颇有工科大学的务实风范。
纵观数十年的入学试题,大都出自各学校的著名教授之手,各人性情不同,固然中规中矩的题目居多,但时时能见到其“出格”之处。1932年淸华大学新生入学考试时,时任国文系主任的刘文典请陈寅恪先生出题,作文题目是《梦游淸华园记》,还出了一个罕见的对子题,上联是“孙行者”,求下联。据陈先生的弟子卞僧慧回忆,标准答案是“王引之”,因为“王”有“祖”义,故祖父又称“王父”,而“引”与“行”、“者”与“之”则对仗工整。当年考生中能对出此联的凤毛麟角,后世著名的语言学家周祖谟曾对以“胡适之”,得到陈先生击节赞赏。但周祖谟本人经过权衡比较之后却选择北大,很能体现高校和学生双向选择的特点。
目前自主招生约占学校招生总额的5%,如何用好这5%的名额,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是家长和教育界关注的中心。就此而言,上个世纪20年代的高校招生也有可引为借鉴之处。彼时各学校招生自由度较大,在选择标准上极为灵活。1929年钱钟书报考清华时国文优秀,英文满分,但数学只考了15分,堪称“怪才”。尽管总成绩并未达标,但校方认为他人才特殊,决定破格录取,一时传为佳话。不仅钱钟书,钱伟长入清华大学,臧克家入青岛大学,卢冀野入东南大学时都是偏科的专才,在整齐划一的高考制度下未必能通过独木桥,但是在自主招生的大背景下均能顺利过关,并在各自领域内作出重大贡献,这恐怕也是当下主持自主招生的高校管理层所应注意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