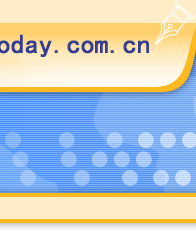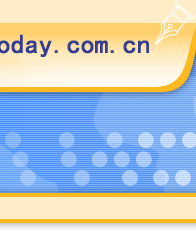迟到的器官移植立法
文/冯建华
推进脑死亡立法、规范供体市场、拓宽供体渠道,是中国规范器官移植行业面临的三道难题。
“要花多少钱?”
“你给20多万吧”
“太贵了吧?不能便宜点儿?”
“价钱好说,有空见面聊聊。”
"为啥要卖这个啊?”
“等钱呗!”
……
这是一位记者在作隐性采访时与一位自称“捐肾者”之间的对话。它并非电影里的对白,而是发生在中国的真实一幕。而且,这种交易在中国一些地方早已不是一种秘密。
提及中国器官移植市场,业内曾有一个流传甚广的形象比喻:急剧膨胀的中国器官移植市场,就像一条新建的高速公路,很多车突然涌了上来,可是却长时间没有红绿灯,也没有车道。
3月16日,国家卫生部发布《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下简称《暂行规定》)。在这部行政规章中,中国首次明确规定“人体器官不得买卖”,同时规定医疗机构临床用于移植的器官必须经捐赠者书面同意,捐赠者有权在器官移植前拒绝捐赠器官。
这项自2006年7月1日起实施的行政规章,填补了中国器官移植行业的立法空白,也使得该行业首次有了指明发展方向的“红绿灯”。
“这项规章出台不能说非常及时,但也到了不得不发布的时候了。如果再不发布,问题将变得不可收拾。”北京市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陈大志博士对记者说。
“遍地开花”结下的苦果
器官移植曾是人类长久的梦想,被誉为“21世纪医学之巅”。这项技术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已有临床尝试,进入90年代后期,中国器官移植行业发展迅速,目前已开展了国际上所有的临床和实验性器官移植类型。
中国卫生部的数据显示,上世纪90年代,大陆器官移植手术以每年超过1000例的速度增加。如今,中国全年器官移植手术已近万例,在临床数量上的排名,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市场”。
可是,在很长时间里,中国医院从事器官移植可以不需要卫生行政部门审批,也不需要在专业协会备案,以至于很多不具备条件的医院,也竞相开展器官移植手术业务,这种现状被业界称为“遍地开花”。
“中国器官移植行业一度非常混乱。现在中国虽然开始规范这个行业,但期间确实走了很多弯路。” 陈大志神情严肃地说。
据不完全统计,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国可以开展肾移植的医院达到368家,肝移植的有200多家。而在医学技术最发达的美国,能够做肝移植手术的只有约100家医院,有资格从事肾移植的不过200家。
据陈大志了解,目前北京至少有30多家医院开展过肝移植手术,但实际上,有五、六家医院就足够了。如果按照卫生部此次规定的市场准入条件(硬条件是三级甲等医院),北京市目前从事肝移植手术的医院
“至少有一大半不合格。”
那么,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医院热衷于器官移植?陈大志分析认为,一些中小医院开设器官移植业务,主要是为了显示综合实力,直接经济利益考虑的相对较少。而一些大医院争相开展器官移植手术,则两个目的都有,除了显示综合实力,更主要的是为了增加创收。
“由于技术条件不过硬,一些医院做了器官移植手术,到后来也只能强行摘除器官,这多不应该啊!” 陈大志痛心地说,更重要的是,一旦得不到很好的术后管理,患者很容易出现并发症甚至死亡。事实上,由此产生的医疗纠纷和事故已在中国出现不少。
此外,在混乱市场的催生下,“器官黑市”在中国一些地方出现,这导致医院取得器官供体的费用迅速提高,进而导致器官移植手术费用也“水涨船高”,其最终损害的还是患者的利益。
“因这样提高手术费用,我们也是深恶痛绝,我认为这个责任在社会,而不在医生,因为这是我们控制不了的。”陈大志说。
而且,由于供体市场非常紧缺,又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制约,这也导致有人利用各种关系“插队”来获取供体器官,而那些急需移植的患者却只好等待,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教授、知名伦理学家王延光认为,在器官供体非常紧缺的情况下,按什么标准来确定哪些人应该最先接受器官移植,是一个至今仍存在很大争议的伦理学难题,例如,有的专家认为应该按年龄大小,有的认为按排队先后,有的认为按病情轻重,有的认为按社会贡献大小,等等。
“我认为这(“插队”获取供体器官--编者注)关系到一个社会的道德风尚,是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 作为国家卫生部医学伦理学专家委员会委员,王延光通过本刊呼吁。
立法只是个“最基本的措施”
其实,中国一些专家很早就在为器官移植立法奔走呼吁。
“全国立法已到了非做不可的时候。” 作为一位知名器官移植专家,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直言不讳地表示。正是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全国行政立法工作加快了步伐。经几易其稿,反复斟酌,《暂行规定》才得以最终出台。
这部行政法规给王延光教授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每个开展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从此必须成立一个特殊机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器官移植前,医疗结构必须将人体器官移植病例提交该委员会进行充分讨论,并说明人体器官来源合法性及配型情况,经同意后方可为患者实施人体器官移植。
“设立一个专门的伦理委员会,是以前绝大多数医院所没有过的,这说明中国政府把器官移植纳入了伦理规范之内,这是一种认识提高的表现。”王延光教授说。
可是,陈大志教授却认为,这部行政法规初步明确了监管机构和市场准入标准,这一点固然非常重要,但也只是规范器官移植行业一个“最基本的措施”。
“该行政法规能不能起到真正的规范作用,还需要拭目以待。就我个人而言,我内心存有一定的疑虑。”陈大志表示。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器官移植问题专家陈忠华也认为,这一行政规定虽然填补了中国器官移植行业立法的空缺,但是离法制化还有很大的距离。
中国还应该做什么
行政立法只是中国政府为规范器官移植行业而迈出的首要一步,前面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逐步加以细化解决。
“脑死亡立法不通过,中国再大力提倡自愿捐献器官,也没实际意义。”陈大志对记者说。
中国目前还是普遍执行传统的死亡判断标准,即心跳、呼吸停止。可是,从临床表现来看,从脑死亡到心脏停止跳动,还需要一段时间。而如果等到心脏停止跳动再摘取器官,大多已失去移植的价值。
在《暂行规定》还在征求意见的2005年,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透露,对于以往争议颇多的死亡判断标准,该条例将采取心跳停止和脑死亡两种死亡标准并存、选择自主的方针。此后一段时间里,有关中国即将出台脑死亡法的报道不断见诸于媒体。
可是,在此次颁布的行政法规中,并没有提到死亡判断标准,更没有提到“脑死亡”的字样。“《脑死亡判定标准》肯定要出台,但最近不可能出台。”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孙东东最近对媒体明确表示,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卫生部脑死亡立法起草小组成员之一。至于原因,他认为“最大的困难来自人们的传统观念。”
陈大志也认为,中国人接受脑死亡,“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他的判断依据是,日本、韩国等一些亚洲国家通过脑死亡法已有好些年头了,但实际上自愿捐献器官的还是寥寥无几。
“供体市场是器官移植行业的源头,只有规范了源头,后面的问题才好解决。” 陈大志强调说。可是,在目前出台的行政法规中,对这一点却没有提到,例如支援者捐赠器官的程序、医院获取捐献器官的程序,以及有关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等等。
对于此次颁布的行政法规为何没有涉及到供体市场?王延光教授有着不同的看法。她认为,规范供体市场不是靠卫生部颁布一个部门行政法规所能解决的,它需要卫生部与司法部等多个政府部门联手合作,例如,如何打击贩卖人体器官的犯罪行为,需要公安部门的介入;如何打击人体器官的国际走私行为,需要海关总署的介入等。
如何开拓供体来源渠道,是中国器官移植行业必须面临的另外一道难题。 “在供体来源这个问题上,当然渠道越多越好,但我们只有一条途径,而且这一途径受政府的左右。”陈大志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除深圳外,包括全国红十字会在内的中国所有红十字机构,目前均没有设立接受器官捐献的机构,而深圳市开展的此项工作,也只是局限于身后捐献。当记者就这种情况致电全国红十字会有关机构询问其中原因时,对方工作人员给出的答复是“事情比较敏感,又没有法律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