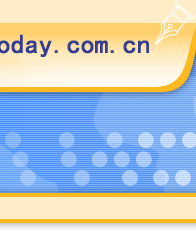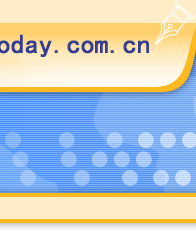有光一百岁 拼音五十年
张 彦
 周有光出生在清朝的光绪三十二年、即1906年的1月13日,他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多的漫长旅程。
周有光出生在清朝的光绪三十二年、即1906年的1月13日,他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多的漫长旅程。
长寿人人向往,但更重要的是要健康长寿。在这方面,周老堪称典范。现在,除了耳朵有点背和因伤风感冒上医院以外,别的还没有发现什么大问题。特别值得庆幸的是,他的头脑依然那么敏锐,每天必读书看报,经常发表具有独到见解的文章。而且,他思考问题之广、之深,令人肃然起敬。
半路出家,成就拼音方案
周有光1923年就学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的是经济。至1955年来北京以前,他一直在国内外大学讲授经济学或从事银行工作,语言文字研究只是他的业余爱好。没想到,自从那年应邀来北京参加中国文字改革会议以后,被周总理坚决留下来专门从事语言文字改革的工作,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诞生时,有56个民族,80多种方言,并且大多数人都是文盲。要建设这样一个国家,没有统一的、能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文字语言,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文字改革问题很早就被置于国家工作日程的重要位置,并从全国范围内召集了许多专家学者来从事这项开创性工作。半路出家的文字研究爱好者周有光,就是其中之一。半个多世纪以来,周有光在语言文字学领域辛勤耕耘、开拓创新,先后发表了专著30多部、论文300多篇,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已经被联合国通过在全世界普遍使用的《汉语拼音方案》,今年已届50周年,周有光就是它的主要设计者。
中国语言文字学界普遍认为,在周有光广泛的研究领域里,最重大的贡献是他对中国语文现代化的理论做了全面的科学的阐释。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中国语文的现代化,还是依旧方言加文言、实行繁难的汉字、大多数人仍属文盲,教育如何能够得到发展?如何还谈得上国家的现代化?现在回过头来看,不正是因为实行普通话加现代白话文,汉字有了规范化和汉语拼音的辅助,有了这些中国语文现代化的措施才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就更加显得突出了。一个多民族的大国,不仅需要国家共同语,而且需要国际共同语,才能游韧于全球互联的世界。与汉语拼音同样使用26个拉丁字母的英语已成为事实上的国际共同语,是一条大家都可以走的世界公路。网络化离不开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又是电脑与中文的接口。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在从各方面与世界接轨,汉语拼音正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交流的重要桥梁。面对中国正在现代化进程上阔步前进的现实,如果没有语文现代化先行一步,这可能吗!为了让中国语言文字的管理走上法治轨道,全国人大常委甚至专门通过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在选编《周有光语言学论文集》时,北大教授、语言学家苏培成在《序言》中特别指出:周老“在学术思想上一直走在时代的前面,不断提出新思想,引导语文工作前进。”他认为,周老之所以能这样,“重要的原因是他有世界的眼光,他从世界来看中国。他研究语文问题,从来不把中国和世界分隔开来,而是把中国放在世界的范围内、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再加上他博学多识、学贯中西,所以能高屋建瓴、洞悉事物的本质,提出具有指导意义的意见。”
自我教育,百岁自学
事实的确如此,我从自己与周有光先生的长期接触中也深有体会。我和他的相识,始于六十年代初期。那时,我是本刊的前身《中国建设》担任教外国人学汉语的《中文月课》专栏责任编辑,周有光是这个专栏的特约作者。每月,我去他家商谈稿件归来,都有满载而归的感觉。因为,他放眼世界的渊博知识,每次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视野为之开阔。从此,我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忘年之交。
在随后的岁月中,中国和世界,包括我们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21世纪后,让我吃惊地发现,接近百岁高龄的周有光依然红光满面,精神抖擞,高谈阔论涉及的方方面面更广更深了。近几年来,去拜访周老,尽管要从西到东跨越寥廓的北京城,却在我和我的老伴思想上视为去上一堂必修的“大课”。久而久之,只要一段时间未去,周老就来电话了:“欢迎你们来聊天!”我们听了,受宠若惊。能够经常亲聆百岁智者的教诲,茅塞为之顿开,岂非三生有幸!
周老书桌上总是堆着许多书,凡是看过的大都划满了红线或者批了字。一次,我发现都是有关中国、美国、前苏联的书籍。果然,据他说,他正在集中研究与我们有着最直接关系的三个国家的历史。他发现“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因为历代帝王歪曲历史,掩盖真相。考古不易,考今更难。”通过长期的读书,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先知是自封的,预言是骗人的,如果事后不知道反思,那就是真正愚蠢了。聪明是从反思中得来的。近来,有些老年人说,他们年轻时天真盲从,年老时才开始探索真理,这叫做‘两头真’。‘两头真’是我国过去一代知识分子的宝贵经历。”他还告诉我们,读书还使他悟出一个道理:“老来回想过去,才明白什么叫做今是而昨非。老来读书,才体会到什么叫做温故而知新、学然后知不足、老然后觉无知。这就是老来读书的快乐。”
周老的谈话,不仅往往给人以启示,还常常富于幽默感。为了让人明白汉语改革的必要性,他总爱说这样一个小故事:很久以前,三个中国人在英国相遇,一个广东人,一个上海人,一个福建人,谁也听不懂谁的方言,只有都用英语才能沟通。如今,有了汉语改革,这种笑话才不至于再发生。周老还常对人说,他的“命大”,并举事实为证:抗日战争时,他在重庆逃难,一次日本飞机的炸弹正好落在他的附近,一股风把他刮得好远。醒来却吃惊地发现,周围的人都死了,他却连伤都没有。1957年,全国轰轰烈烈开展“反右”运动,上海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几乎都成了斗争对象,有的因为受不了这种政治迫害而自杀。他却因为已移居北京,并改行文字改革,躲过了这一劫。否则,他的历史需要重写。至今想起来,既庆幸,又后怕。
“清朝老头与白发才女”,是朋友们送给周有光夫妇的美誉。他的夫人张允和是出自江南名门的才女,擅长昆曲,并出版过多种书籍。他们二人相爱、相敬、相伴70年。直到三年前,张允和不幸因病去逝,时年93岁。可以想象,这个晴天霹雳的挫折在周老心里会有多么沉重。但是,对人生已具有高层次豁达态度的周老,却能泰然处之。他曾经在其夫人著作《浪花集》里的出版后记中这样写道:“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一时透不过气来。后来我忽然想起有一位哲学家说过:‘个体的死亡是群体发展的必要条件’;‘人如果都不死,人类就不能进化’。多么残酷的进化论!但是,我只有服从自然规律!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经过半年的自我调整,本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知识的渴望,他又开始了对学术和世界的不断探索。他说过,生活不仅是吃饭穿衣,还必须与文化结合起来,要与艺术结合起来,才能丰富多彩。看来,在那非常简朴的公寓楼里,他很喜欢他那间窗明矶净的小书房,经常举着放大镜在仔仔细细地读书看报。累了,就站起来扶着书桌做他自己发明“象鼻子操”,活动活动筋骨。前来探访求教的客人,无不为老人的热情接待而深受感动。精心照料他的小阿姨,不仅能做可口而健康的饭菜,还可以使用电脑为他当秘书。已经70多岁的儿子虽然不住在一起,但经常前来看望百岁老爸,尽享其乐融融的天伦之乐。
对于这样一位度过漫长阳光岁月的老人,不知道已经有多少人曾经问过他:“您一生百岁,有点什么经验留给后人?”他的回答总是:“如果说有,那就是坚持终身自我教育,百岁自学。”
三联书店不久前将周有光百岁以前十年所写部分杂文,汇集起来出版了一本《百岁新稿》。作者在《自序》里特别表示:“希望《百岁新稿》不是我最后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