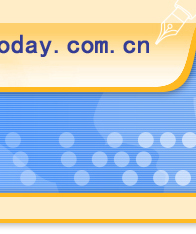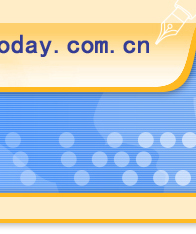音乐剧的中国化
重颜
2006年3月3日,上海大剧院与国际音乐剧界最富盛名的制作人卡麦隆?麦金托什,在备忘录上郑重签字,正式确认将长演不衰的《悲惨世界》改编成中文版,拟在2008年初上演,而双方合作的中外和资音乐剧公司有望成立。
卡麦隆?麦金托什有限公司在世界音乐剧界大名鼎鼎,先后制作过《猫》、《悲惨世界》、《歌剧魅影》、《西贡小姐》等一系列经久不衰的音乐剧。该公司仅在伦敦就有7座剧场。
人口众多的中国市场至今仍是一片音乐剧的处女地,自然成为该公司努力开拓的地区。麦金托什先生对中国市场的考察则可以追溯到7年之前。当时他发现中国确实存在着喜欢音乐剧并愿意到纽约和伦敦观看原版音乐剧的观众,但这一比例甚小。然而到了2002年,当他将原版的《悲惨世界》带到了上海时,成功的公演让他惊喜地发现中国市场还存在着相当多的一批观众愿意在国内看音乐剧。而此后《猫》和《剧院魅影》等音乐剧在中国推广中所显示出来的市场潜力和合作经验,令麦金托什对上海的信心和合作意向越来越强。
通过中文诠释经典的音乐剧作品,培养本土音乐剧专业人才,最终借此力量实现“中国制造”的本土音乐剧产业,则是上海大剧院这几年欲实现的蓝图。于是双方一拍即合。2005年11月,麦金托什来到中国,他说改编《悲惨世界》的主要目的除了帮助中国拓展音乐剧市场之外,就是想让更多的中国老百姓在家门口看得起音乐剧。
接着上海大剧院从市场培育、到根据市场判断选择合适的剧本、再到融资、引进国际音乐剧龙头制作机构的专业理念与合作,遵循高投入、大制作、长线投资以获得高回报的国际音乐剧产业化运作道路,按部就班地徐徐前行。
然而,在进入接下来的实质性操作阶段以后,汉化的问题就随之面来了。首当其冲遭遇瓶颈的就是:把《悲惨世界》的经典唱段完美地翻译成中文,这个重任谁能够承担?
“《悲惨世界》的本土化其实已经谈了两年”,负责音乐剧本土化工作的大剧院副总经理钱世锦说, “最大的问题就是《悲惨世界》用中文怎么唱?原版按英文的起伏谱曲,中文版既要体现音乐的韵致,又要使文字表达原曲的意境,谈何容易?我们的基本想法是多方面发掘专门人才,按照流行歌曲的模式来重新创作。”
上海大剧院首先接受了来自一位旅居伦敦的热心华侨的毛遂自荐,将其主动提供的自己翻译的《悲惨世界》中的4首曲目中文译文提交给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剧系的学生试唱,然而结果不尽如人意,甚至有试唱者直呼“非常别扭”。“拿到中文译文,我们的第一感觉是词很诗化,很多唱段翻得像中国古典诗词,看起来美是美,但唱起来却非常吃力,不上口。”这几乎成了试唱学生的共识。毕竟汉语的四声,与英文发音差别甚大,西方音乐剧的旋律,配合译文的古雅,因此,不仅歌者“别扭”,即使是在场的听到“原汁原味”的中文词的台下中国听众,都没听懂。“难道用中文唱的《悲惨世界》,到头来还要用打字幕的方式告诉中国观众唱了什么”?
此前,有一种声音认为,在音乐剧本土化进程中,既然要“中国化”,那就干脆将中国诗词融入其中。但是经过那次试唱,证明了这种中文译文标准存在偏差。曾经翻译过《剧院魅影》剧本的费元洪说:“不能为了‘中国味’而片面‘古典化’,因为,“通俗易懂”正是音乐剧作为流行艺术形式的最明显标志。”这也是圈内对“中文译本”标准大讨论最终达成的共识。
为了爬过翻译这道坎,大剧院又力邀俄罗斯歌曲翻译专家薛范,他曾尝试着翻译过《猫》和《剧院魅影》各自两首曲目。但薛范本人一直坚持《悲惨世界》非自己所专长,力荐好友,专门从事《悲惨世界》翻译的专家,四川师范大学的沈承宙老师。看过译文后,费元洪表示:“相对白话,通俗易懂、易唱。一看便知,他是懂音乐的。”大剧院方面也表示:“沈老师的译文,目前是最出色的。”这一外交辞令隐示着背后的众多不确定性。
让大剧院头疼的还有音乐剧专业演员匮乏,这其实也是戴在上海众多音乐剧制作单位头顶的紧箍咒。尽管目前国内已有不少音乐学院开设了专门的音乐剧系,但是,从学院到剧场的专业人才,显然不是短短几年的距离。这也是国产的一些音乐剧干脆放弃明星策略,将赌注押在新人身上的原因。按照国际惯例,音乐剧一个礼拜要演出8场,而国内现在演员一周唱两场并且还要隔日进行,出于对演员演出能力的考虑,大剧院预计《悲剧世界》中文版起码得准备4套以上的阵容。
翻译和演员问题不仅让大剧院犯难,还让一部分原版《悲惨世界》的忠实拥趸信心不足。对于热爱原版作品尤其是“一见钟情”的观众来说,任何翻译和翻演“都是蹩脚”的。观众对于中文的无法预估的态度也让大剧院有点心虚。不过正如一位资深音乐剧迷所说:“想想我们在没有接触原声外语片的年代,对译制片的痴狂和对配音演员的崇拜!”对于绝大多数无缘和没有能力欣赏原作,从而没
有“先入为主”机会的观众来说,让他们与汉化的剧场和人作产生共鸣大有可能。”
此外,还有一些观众疑虑的认为:中国人来演法国人很滑稽,但大剧院的负责人表示,看看百老汇或西区,也没观众对西方人扮演日本蝴蝶夫人感到滑稽过。亚裔的Lea
Salonga(李萨隆加,菲律宾籍演员)还被公认为最成功的Eponine(爱潘妮)之一。而在百老汇《悲惨世界》中,扮演Fatine(芳汀)和Eponine
的演员有白、黑、黄种人,西区的Jarvert (贾维)和Enjolras(安灼拉)还由黑人演员担任A角。他们化妆时,也没有用丝毫努力去掩盖亚裔特征或黑人皮肤。所以,我们也完全不必对前景过分悲观。汉化?不汉化?基本上已不存在该不该的问题,而是更应关注于接下来翻译、表演、以及开拓国内市场,这一切落到实处,才是更应该考虑的问题。
大剧院副总经理钱世锦认为,除了听取那些“原装粉丝”的意见,还应理多预测那些对音乐剧《悲惨世界》不甚了解的潜在粉丝的接受心理,因为后者更大程度上才是主宰音乐剧本土化的市场主要决定力量。
谈及音乐剧本土化的市场问题,最无法忽视的是票价问题。推出由本土演职员、用中文演出的、但是制作水平与国际接轨的高质量音乐剧,最实质的好处就是能够降低成本,如果能够通过推行低价,就能够吸引真正而以往没有能力时入剧场的音乐爱好者,以及潜在的消费者,尤其是音乐剧应该大力扶植的学生观众。如果票价信用依然太贵,又如何能够培育良性的市场氛围,去实现本土音乐剧像百老汇、像西区那些经典名剧一样长演不衰的梦想呢?众所周知,音乐剧可观的商业回报并非来自高票价,而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演出,以及世界不同地区原版复制后的长期演出,他们的票价许多比现在中国虚高的舞台演出得更便宜。如果在票价上不真正实现突破,音乐剧本土化的意义也不复存在了。
让观众欣慰的是,上海大剧院的钱世锦表示,他们将确保观众能看到一个同百老汇和伦敦西区一样精彩的《悲惨世界》,中文版《悲惨世界》的票价还将大幅下降。
看来,上海大剧院将音乐剧本土化到底的决心和彻底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