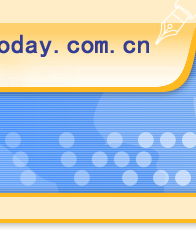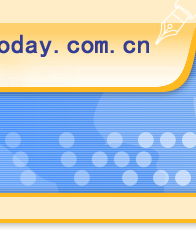徐流口村:在原始农村形态上翻新
本刊记者 张洪 图 曾平
中国农村惯常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广袤的土地,贫瘠的乡村,一代一代人在上面流汗播种,辛勤收获。徐流口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中国原始乡村。
有女不嫁徐流口
老式黑边塑料眼镜,一身洗得褪色的深兰中山制服,60岁的老管家董春林坐在村长办公室破旧的办公桌前,在临窗射入的阳光下,正在为徐流口村一笔一笔算帐。
这样的算帐场景在中国农村不算少见,但董春林笔下的帐目却是徐流口村独家一份——它们包含着这个村庄过去和现在的全部支出和收入,那一五一十的帐目细化到了小数点后两位数。一提起过去,徐流口人只有摇头。
徐流口地处燕山山脉迁安境内的最东端,万里长城在这里断了个空口,一代英豪戚继光给这里起了这个不知何意的名字。
“有女不嫁徐流口,穷富好说路难走”,地处偏隅,交通闭塞,徐流口如同匣子一样锁在没有人烟的地方,谁也无心开启它,除了盛产光棍这里几乎一无所有。过去,村里三四十岁的光棍有七八十个,平均不到七户就有一户这辈子永远贴不上喜字的人家。
据当地人说,早年的徐流口人习惯穿掌子鞋——一种用汽车轮胎当底,用尼龙绳纳的厚底布鞋,村里一脚石头一脚泥,出村就是一座下雨就打滑的泥山,再结实的鞋也撑不了几天。
“修路咧,修路咧”
寻找出路,脱贫至富,这是中国农村,特别是贫困乡村世代的目标,徐流口村更是迫切。面对一个连路都难走通的地方,全村人夜思昼想做梦都想寻到一个领路人。
恰巧,徐流口村就有这样一个人,他的名字叫秦玉合。早年入伍时腿脚受伤,掌门人秦玉合至今走路还有些跛足。
一辆别人赞助的破旧桑塔那轿车,上山下山,爬坡进城,秦玉合就是靠着这样的“坐骑”为徐流口“卖命”。2003年,河北省首次发出创建社会主义文明生态村的号令,并把这一任务交给唐山,交给迁安,唐山首批有600多个村子被列入“文明生态村”创建试点,这些村庄除了有钱的就是靠近省国道的,各有优势,徐流口村因地处偏远,一穷二白,没有被入选。秦玉合当时急了,回到村即对村干部抱怨:“搞生态村没咱们的份儿,没个几十万下不来,咋办?”
回答的也是他:“那还咋办,不让整也得整!”秦玉合当即把1000元人民币拍到村集体帐户上。在这个吃尽了交通不便苦头的半山区村,“修路”的话题总是能引起共鸣。在秦玉合的鼓动下,以当时村里仅有的2000元起步,徐流口全村33名党员带头从掏心到掏钱,从老退伍军人到小学生,几天的时间一鼓作气把生态村的资金生生凑了出来。
那一年农历腊月十三,在徐流口人心中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那一天起,徐流口文明生态村“巷战”全面打响,盘山道工程开工。驴车马车牛车一时间全村车轮滚滚,千八百号人镐头挥舞,铁锨翻飞,锤声震耳,秦玉合是工程总指挥,他一会来到这头,一会奔到那里,在十个开山小分队里来回穿梭忙碌。
徐流口村家家户户的庭院大都依山坡地势坐落而成,街道凸凹不成,宽窄不一,最窄的地方连手推车都难以通行。像这样的“瓶颈”地段全村共有七处。路修到谁家门前,谁家就会送出冰棍、绿豆汤,最穷的也会送上一大桶凉开水,午饭时妇女们给工地送来炸好的豆片。父老乡亲咬着牙鏖战七天七夜,共清理路面7000多米,整理铺垫路基2500米。不到半个月,仅凭原始的开山工具,徐流口人就打通了4米多宽、6华里长的盘山道,开凿土石方1万多立方米。两条相距六七米左右的“长线”从山顶弯曲着一直甩到村头,一时间,连穿开裆裤的孩子都在村里蹦蹦跳跳地喊:“修路咧,修路咧。”
就这么疯狂大干了11天,搅拌机慢慢停了下来,最后一车混凝土卸下来,大人小孩到处跑着来看,“徐流口的金光大道修通啦!”
穷村有穷变法,盘山道开通后,秦玉合和他的村民不肯罢休,又一鼓作气拓宽了徐流口的南大门,铺设了4000多米柏油路,并与河北省长城旅游公路连通。仅仅11天,锹锄秃了,钎撬短了,锤镐轻了,扁担断了,衣衫破了,肩膀烂了,鞋底透了——徐流口祖辈无路的历史宣告结束。11天,徐流口人修筑了2.5公里的水泥路,创下了唐山市工期最短、成本最低的施工记录。
像城里人一样轧马路
如今,走在徐流口的水泥路上,抬头是城市惯有的路灯,你很难相信这就是当年的穷乡僻壤姑娘不来的地方。“现在二十四五岁没对象就已经算大龄青年。”妇联主任董艳红告诉记者。
修通了路,徐流口结婚的人连年增多,盛产光棍的恶名从此“摘帽”。走在徐流口平坦宽阔的4公里通村柏油路和2.5公里水泥路上,徐流口的光棍说:“忒好了,我们也可以像城里人一样轧马路了。”
谁都不会想到,徐流口新修马路上60盏路灯所用的电线杆,全是外地淘汰的旧电线杆,加上村民自己焊制的灯架,徐流口的路灯节省资金过万元。迁安市交通局的张印怀感慨道:“奇迹呀,了不起的人间奇迹。这路,是徐流口人用手扒出来的!”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有秦玉合这样的好干部,莫说是修条盘山道,就是修条通天大道,也是张飞盘子里的豆芽菜啊。”一同测量的交通局张股长也跟着说。
有了路,徐流口村又建起了文化广场、健身广场和娱乐广场。重新完善了图书室、阅览室和医疗室。小小乡村,甚至还建起了超市。
再后来,街道美了,班车通了,采购山货的老板来了,闭路电视有了,家家户户电话安上了……,现在的徐流口村,背依长城,胸揽温泉,迁安那边的姑娘忍不住来了,本村姑娘打死也不愿走了……
2004年4月,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来徐流口视察,款款登到平坦的山顶,望着脚下秀丽的山村,白克明情不自禁感叹:“搞到这份上,不易呀!的确不易呀!”
中国有个河北,河北有个唐山,唐山有个迁安,迁安有个徐流口。有像徐流口这样倔强的村庄,唐山有理由夸口,到2010年,全省20%左右的行政村进入文明生态村行列,到2020年,全省所有的村庄都将成为文明生态村。
寺后村:黄土地上种“企业”
靠着苦干、硬干,徐流口翻建出一个新式乡村,与它相距不远的迁安扣庄乡寺后村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模式——在大片土地上兴建厂房,种庄稼的同时也种“企业”,远远望去,与其说寺后是一个乡村,不如说它更像是一个微型城镇。
从徐流口村一路向南,在饱经了原始形态乡村巨变的观感后,我们又遭遇到另外一种乡村发展模式。
上下班的农民
初到寺后,一定会被两处情景打动:这里的农户家家养狗,但再也不是过去见人乱叫的看家狗,而一律变成了温柔可人的观赏犬。这些绕膝不去的宠物提示人寺后的富裕。
另一处情景是,这里的农民不再腿脚沾泥,脸上挂汗在地里劳作,而是在通向村外的柏油路上骑着自行车优游上下班。除了口音酷似中国家喻户晓的小品演员赵丽蓉,其他看起来都更像是城里的工人。
48岁的张千是寺后村的书记,一张略带黑红的脸,闪着精光的眼睛透出“掌门人”的干练。他整治村庄的方法很简单,也很“酷”,就是如同管理企业一样来管理它。在寺后,我们心目中固有的农村概念受到了冲击,看着那些干净整洁的院落,无处不在的水泥路,年轻时髦的年轻女郎,宽阔轰鸣的厂房,才发现,原来农村可以如此接近城市。
小小粉条做出国
来寺后前很难想象,小小的乡村竟然设有停车场。偌大的停车场被一块块整齐的长方形黑砖铺满,这些砖出自当地村民之手,是他们当年的“工分”。走进轰鸣的厂房,说话要高出好几个分贝,高摞的黑砖堆成一排一排等待晾干,这只是寺后众多企业中的一个。
都说,在迁安农村基本看不到土路,果然如此,我们大街小巷一阵穿过,“进村”的感觉基本没有。这里的道路已经全部“硬化”,村民家多数用上了沼气,与过去一身泥泞的形象完全不同,这里的猪妈妈和它们的孩子都生活在没有任何泥泞的水泥地上,而其粪便则是全家照明、取暖、做饭的能量来源。粪便是宝,果然如此。
寺后村是迁安地区小有名气的粉丝加工专业村。过去,因为粉条生产污染了周围环境,村里污水横流,街道泥泞不堪,所谓“屋内现代化,屋外脏乱差”。文明生态村创建以来,寺后把村内的40多户粉丝加工专业户统统“请”到了村外,出村不远,就是百亩粉条加工小区,华北地区最大的粉条加工企业——方生粉丝厂就座落在小区内。在一排气派的房子里,刚刚从台湾引进的生产线还没有投入使用,但寺后村的“家底”却一目了然。
这个小小的粉条“王国”真是藏龙卧虎,企业从北京聘请工程师专门研究粉条生产技术,工程师的父亲曾给国家领导人陈云做过厨师,深谙粉条制作之道,研制的粉条不但招徕了北京国家机关的“吃客”,甚至还跨洋过海,销售到泰国和越南。
谁都不会想到,这样富有的“企业”竟然卧在一个地图上名字都难找到小村子里,而这个村子一天生产的粉条制品,说出来真让人乍舌,是300吨。丰田、桑塔那、普桑等轿车都是村里的常用车,一个小村子,竟然有30多辆汽车出入。
生态文明村的夜生活
“原来环境不好,村民就是有钱盖房也没有心气儿。现在环境改善了,大家才争着、比着建新房。今年开春以来,全村就有20多户村民翻盖了新房。”书记张千说。
建设生态文明村靠的是全村的“心气儿”,寺后投资300多万元,把原来一条3米宽的土路改成长200多米的街心广场,用来召开全村大会、放电影、演歌舞、扭秧歌。甚至还建起了娱乐一条街。寺后的文体活动广场成了每天晚上村民聚会的好去处,2000多人在这里跳舞、娱乐、唠嗑、唱歌,孩子们也嬉戏其间。过去农村夜晚的死寂,天一黑就上炕的习惯被彻底打破,当地人夸口说:“没想到,如今我们也有了夜生活。”
利用现有的绿化林木、草坪、甬道等,寺后规划设计了一个占地21亩的街心公园,内设各种健身器材和乒乓球台、台球台以及灯光篮球场。早上天一亮,体育健身器材就开始“忙碌”起来,打球、练腰、舒展筋骨、呼吸新鲜空气,村民的业余生活已经趋近城市化。
今天,寺后人的餐桌告别了过去除了粉条还是粉条的日子,这一富庶的城镇甚至引来了蒙古人的生意——一组整齐的蒙古包落户寺后,高大俊美的蒙古姑娘为村民端茶送菜,烤羊腿、手抓羊肉成了寺后人“打牙祭”的理想选择。
过去的土路泥路,如今变成了宽阔的街道,两侧栽有柳树、火炬树、美人梅、黄刺梅。每天早上,寺后人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像曾国藩一样清扫庭院,各户院内自愿垒起垃圾池,由专人定期清运到村外垃圾添埋场。还专门在村外规划出放秸杆儿、柴草的区域,粪堆随起随出,那个柴草乱垛、粪便乱堆的乡村从此消失。
在寺后,我们看到了中国农村的另一面:它不再是桃花源式的男耕女织,也不再是人民公社化的强制性大锅饭。它是一个现代化的乡下小区,却有着浓厚的城镇气氛。城镇,乡村?农业,工业?农民,工人?一时结合在一起,让人领略到一个中国农村建设的崭新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