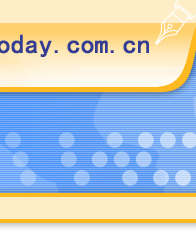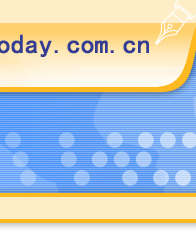我的父亲
文/於翔
封面故事
30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发端于农村,从调整土地政策入手,成为巨大的社会进步推动力量。2008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1978-2008
变化就在身边
变化,从1978年12月18日开始。这一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打那以后,经济建设成为中国人的中心工作。
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亿万百姓解决了温饱问题;在乡镇,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城市,各行各业都发生着剧烈变化。经济的发展,同时带来了社会的进步和思想观念的改变。
从1978年到2008年,30年的时光,在农村、乡镇和城市,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本期辑录了几个小故事,您读下来没准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子。
封面故事
我的家乡在浙江北部的湖州,地处杭嘉湖平原和上海、杭州、南京的中心地带,是自古的“丝绸之府,鱼米之乡”。我的家就坐落在湖州素有“桑林”之称的双林镇的农村,当地的农民家家户户种桑养蚕,种植水稻。我的父亲就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和他的祖辈们一样,起早贪黑种稻养蚕,吃苦勤劳是他们的秉性。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实行了改革开放,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这股春风吹到我们村的时候,已是1980年。父亲的命运也因此而彻底改变了。
从扫地工到供应科长
父亲感觉到改革开放这股春风的到来将意味着什么。经过一段时间的慎重考虑后,在1980年底,只有小学一年半学习经历的父亲毅然决定辞去生产队队长,于1981年初去乡里的集体企业丝织厂上班。
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集体企业,并不缺人,只答应给父亲一个别人不肯干的扫地工工作,父亲不假思索就答应了。他认为,只要能吃苦、肯干,就决不可能永远干扫地这个行当。
扫地其实不是很繁重的工作,只是拣拾机器上掉落的纸张和清理车间内的卫生。厂里都是清一色的青年女工,不少女工怀孕后坚持上班,机器的边上常有妊娠反应的呕吐物,父亲不厌其烦地打扫着辖区的卫生。他那个车间,每月都是卫生先进。终于,在1981年底,父亲等待到他的第一次机会。
父亲所在的丝织企业决定扩大生产规模,需要对外招工,而父亲因扫地工作勤恳,厂领导指定厂里最好的师傅教他。于是父亲由一个临时的扫地工变为正式的技术工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厂里的6个生产车间中,我父亲当班的车间是机器出现问题最少、解决问题时间最短的车间。父亲对待机器和对人一样,给它吃饱喂足,总是给机器清理、加油,自然毛病就出现少了。
1983年初,他又一次得到机会。厂领导决定破格提拔父亲为供应科科长,负责生产原料的采购供应工作,父亲没有推脱就上任了,他自信能够完成这个艰巨任务。
当时,丝织企业生产原料靠计划审批,父亲所在企业由湖州市纺织行业部门负责,为了争取到更多计划,父亲几乎将2/3的时间都泡在市里。为了节省开支,他向厂里申请在市里租了一个只能摆下两张单人床和一个办公桌的小房间住宿,另一张床给临时到市里出差的厂里同事住。
刚开始,父亲去和湖州市纺织行业部门领导接洽,他们从没有搭理过父亲。父亲则每天泡在他们单位等候,为他们扫地、打水,甚至看到办公室有人在剥毛豆,他也帮忙去剥。终于一个多星期过去了,部门负责人问父亲:你是来干什么的?父亲回答:我是某某丝织厂的,因生产原料不够,特来申请增加计划的。于是,父亲为企业争取到了足够多的生产原料,甚至还有富余。企业把富余的生产原料倒手,就能为厂里每个月净赚六七千元。在当时,这笔钱可并不是小数目。
拿到3万元承包奖
1985年初,命运再次垂青父亲。由于出色地完成生产原料的供应工作,引起乡工业委员会领导的注意,他们建议厂里提拔父亲为主管经营的副厂长,虽然主管厂长不大愿意。但对于上级的建议还是很重视,很快父亲就成为第七副厂长,其实是个什么都不管的空衔。
这是父亲度过的最“轻松”的一年半。这一年半里,父亲始终在第一线了解生产情况,积累大量第一手材料,对企业的所有情况都了然于胸。一年半后,主管厂长突然因胃癌晚期住进医院。当乡工业委员会领导问谁可以接他的班时,这位曾经和我父亲交情不深的主管厂长不假思索地回答,只有我的父亲能够胜任。于是父亲成为了一个400多人的企业的负责人。
当时乡所属4个丝织企业,数父亲的企业最大。由于无限地扩大生产规模,产品的销售问题已逐渐显露,往往4个企业的经销人员同时跟一个客户商洽,互相压价,最终导致整个乡的丝织企业年亏损达二百多万元。父亲上任后,向乡工业委员会打报告,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将全乡4个丝织企业联合,组建总厂,防止互相压价造成亏损,同时达到规模效应,以降低生产成本;二是充分利用税收政策,成立福利工厂(残疾人工厂),解决乡里残疾人生活困难和增加工厂利润。乡工业委员会同意了父亲的要求,同时要求父亲将组建成立的总厂和福利工厂承包,按年净利润的3%作为承包的奖励,如果继续亏损,只能拿50%的工资。父亲同意了承包的要求,我母亲知道这个消息后,天天以泪洗面。
自1985年盛夏开始,父亲组建了乡丝织总厂和福利工厂。之后,父亲撤消了各厂的经营部门,在总厂成立了新的经营班子,逐步理顺5个企业之间的关系。后来,又将5个企业整合成5个大生产车间,这样,父亲就管理着1300多人的企业。
很快,企业管理出效益了,但也得罪了一大批人。通过一年的运作,连续亏损的帽子摘掉了,还取得103万的净利润。那一年,我父亲按照承包协议的约定,拿到了3万多的奖金。这个数字,在那个年代的农村是不可想象的。1987年初,父亲还被评为湖州市“十大农民企业家”。
小学学历做起外贸生意
命运不会始终垂青一个人,父亲也不例外。1987年年中,在8分钱举报信可以压人一辈子的年代,父亲被人举报了。
当乡工业委员会领导拿着举报信,找到父亲说他存在贪污等违法乱纪的行为时,父亲心脏病突发,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在离开前,他对乡工业委员会领导说:“如果我贪污1分钱,可以把我处分、定罪。半年后,父亲终于康复出院。同时,清查半年的结果出来了:清清白白。
出院后,父亲却犯“倔”了,提出了辞呈。乡工业委员会领导苦苦挽留,父亲去意已决。直到区分管工业的副区长出面协调,挽留我的父亲。而父亲考虑到家人安全,坚决辞职,因为农村里打击报复常常会殃及家人。
于是,1988年初,父亲决定单干。他拿着自己积累的5万元和借遍了朋友得到的10万元,在村里一个破旧的大礼堂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开始,是一个只有10台织机和全套前导设备的小生产企业。经过一年的积累,1989年年初,扩大到20台;到1990年初,规模已扩张到近百台。那几年父亲的纺织产品是供不应求,甚至有几个客户都是提前把货款打进来,派专人在厂里等着,每天生产多少就发多少,以防止别的客户把货品拿走。这种情况维持1993年底。
1994年初,父亲根据市场情况,觉得化纤布料生产不具备太大利润了,只有生产传统真丝产品才有一定的利润,但是真丝产品的生产比化纤产品复杂得多,而销售也主要是向国外出口。父亲一方面将全部化纤织机改成真丝织机,并组织员工技能培训,另一方面和各省丝绸公司积极联系业务,北到北京,南到广州,最后定单也纷沓而来。最终,他稳定了新加坡、马来西亚两个客户,直接做出口贸易业务,并在海南洋浦开发区收购了一个拥有进出口许可证的公司。只有一年半小学学习经历的父亲,竟然也做起了出口生意,而且最高峰时一年的出口额达2000万美金,当时不敢想象的,父亲连26个英文字母都不认识呀。从1995年到1997年年底,每年都能稳定在这个出口数额,转折发生在1998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之时。
面对市场冲击
在1997年初,镇领导(已撤乡变镇)向父亲提出让他收购镇上3个丝织企业,最初父亲没有同意,最后镇里以党委的决议,要求父亲进行收购。父亲又一次犯“倔”,收购了镇里濒临破产的3个丝织厂,收购的条件是,将已负债130-150%的企业,除了发给拖欠的3个月工人工资200多万元,并负责偿还所有欠债。这纯粹是个赔本的买卖。
父亲当时是根据定单的情况,自己的企业已不能满足定单的要求,也需要扩大规模,才答应收购的。可是,亚洲金融危机的风险已向他靠近,并带来灭顶之灾。所有定单全部取消,也接不到任何新定单,真丝产品积压在仓库,上千万的库存摆在他的面前。此时,银行又催他还收购企业的贷款近200万元。资金链条瞬时崩塌,企业大批裁员,父亲进入了他一生之中最为黯淡的时期。他把司机也裁了,生产规模缩小到不能再小的程度。
到2002年年中,市场逐步趋于稳定,父亲逐步走出黑暗的时期。他将能出售的企业全部出售,保留了68台丝织机,并将企业搬迁到浙江绍兴(绍兴的税收比湖州低1%左右),终于又开始了他新的创业。但好景不长,2005年年初开始,真丝原材料价格波动很大,一年时间,真丝原材料价格从12万元/吨涨到最高36万元/吨,而后又跌至20万元/吨。由于原材料价格不稳定,给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几乎是赔一单挣一单。挨过了价格急剧波动的一年后,从2006年开始,人民币的持续升值,给出口业务带来了极大困难。父亲的所有利润,被外商利用美元结算,以远期信用证博取人民币升值差价的做法压榨干净,这种情况持续到现在。
我觉得我那操劳半辈子的父亲,是该收手的时候了。父亲这一生,赶上了改革开放的班车,有过辉煌也有过黯淡,拼搏过了,也失败过。
这就是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