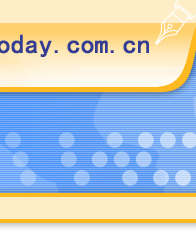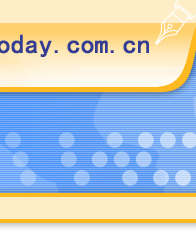家有聋儿
文图/本刊记者 张 桦
早上5点多,齐海涛、孙炳坤的妈妈就把熟睡的孩子从梦中叫醒,他们各自从北京的不同地方走向北京宣武培智学校。7点半,孩子们准时上课去了。当问及孩子们的事情时,她们都出乎意料地愿意袒露自己的心路历程。
辛永芝,齐海涛的妈妈:
希望孩子能上普通小学
我们家在北京房山区的一个小山沟里。孩子一周岁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听力有问题,我和孩子他爹带着他到中国聋儿康复中心检查。在等待结果的半个小时里,他闷头一口气抽了十几根烟。看到结果的时候,他比我哭得还痛。
听医生说,佩戴助听器能够补偿孩子的听力。我们看到了希望,心想,不管是打工挣钱,还是借债,一定要给孩子买上助听器。当时普通的助听器一副是6000多元。孩子爹就能先到单位借了3000元钱,让孩子先用上一只。
为了还债和给孩子早日买上另一只助听器,孩子爹到北京城里打工去了。我就向亲戚借钱买了六只绵羊,准备养大了好换钱。我们家住在山坡上,每天早上我在孩子没有醒的时候,悄悄地把屋里所有的电源拔掉,锁上门。然后把绵羊轰上山坡,下午再趁着孩子睡觉的时候,把羊追回来。每次当我快回家的时候,就远远地听到孩子“哇哇”的哭声
,看着孩子扒着门栓哭成泪人的样子,我的心揪的呀……以后,我干脆带着孩子一起放羊。常常是又追羊,又追孩子。 到了孩子两岁半的时候,我们终于给孩子佩上了另一个助听器。回到家,我们就敲锅敲碗,只要能发声的都敲,就是想试试孩子有没有听力。有一天,孩子有反应了,我们俩抱起孩子使劲地亲。
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我们觉得应该让孩子像正常人一样学说话。这样,我们在北京北四环的中国聋儿康复研究所附近租房子住下,为的就是让孩子接受这里的语言训练。但是每月800元的租金,我们只支撑了两个月,就坚持不下去了。
因为助听器能让孩子听到声音,所以,海涛对助听器特别小心。在外面玩,赶上下雨没有雨伞的时候,他就会紧紧捂着耳朵,或者用衣服盖着脑袋不让雨淋着它。
孩子5岁的时候,经人推荐来到了北京宣武培智学校。我们发现他变得越来越懂事了,不像以前在家的时候不给他喜欢的东西就打滚。
我特别喜欢家里多来人,因为孩子光看我的口型怎么行,来的人多,可以更多地看别人的口型。他眼里特别有活儿,我要干什么,他都知道。我择菜,他会拿凳子让我坐,我炒菜,他就递来盘子。来客人的时候帮着倒水、拿好吃的,以前抠门儿霸道,现在知道好东西大家共同分享。
我希望他语言康复得再好点,能上普通小学。一想到孩子的将来,我就犯愁,不知道他能干什么。我一直在观察他有什么特长,想让他上个绘画班什么的,将来能靠本事吃饭。但是那还远,现在,最重要的是能让他随班就读,多学点知识。
彭燕,孙炳坤的妈妈:
要挣钱给孩子装耳蜗
我刚开始知道孩子耳聋的时候,真是急得有病乱投医,听见谁说哪个地方能让孩子说话,我立马二话不说抱着孩子就去。北京各个地方的聋儿康复点我几乎跑遍了。我的老家是河南驻马店的,为了让孩子能够早日康复,我们才来到北京打工。
去年,我学会了上网,为的是看看网上有没有对聋儿有帮助的好消息,我看到一个叫王永庆的台湾人免费给北京600个孩子做25万的人工耳蜗,我马上就把孙炳坤的情况报上去,但是至今没有消息。
我觉得聋孩子必须让他自立,因为家长不能跟他一辈子啊。所以,孙炳坤在家的时候,我有空就教他学说话。但是他的听力太差,想说的话说不出来,我们说的话他也不能完全听懂。有时,他还问我为什么听不懂?抱着头蹲在地上不吭声。医生说,像他这样重度耳聋,最好是做人工耳蜗。但是这个费用对于我们这样收入的人来讲实在是太昂贵了。怎么办呢?眼看着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我很烦躁。我从网上查到北京有个陶然小学,老师是经过特殊教育训练的,聋儿在这里可以被安排到前排坐,便于他们的学习。
我妈说我30岁才出头怎么皱纹那么多,老得那么快。我说,能不老吗?因为心理压力大啊。有时回家不想让妈妈看到我内心的痛苦,我吃饭时和就故意跟妈妈抢着吃。为的是不让老人家看到我难受的样子。
孩子的奶奶劝我再要一个孩子,我说不要了,我把这个孩子好好带大就行了。我要负责他一辈子。你看有两个小狗,一个在地上趴着,一个在你跟前撒欢。你肯定喜欢撒欢的。但是,我不要那个撒欢的,我要那个趴在地上的,我一定要让那个趴在地上的站起来。让孩子长大、自立,我怕孩子长大了说我:“老妈,你怎么给我生得耳聋啊。”
给孩子做人工耳蜗是我坚持不懈的希望,医生说孩子的听力康复在3-7岁时是最佳时间,我的孩子已经快6岁了。我要挣钱,哪怕孩子长到十几岁、二十几岁,我才能挣到做人工耳蜗手术的钱,我也要坚持。
只要坚持,孩子就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