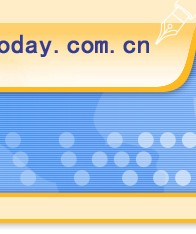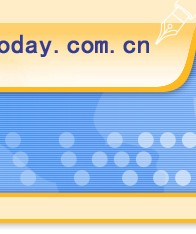李永波:笑对羽毛之“重”
文/唐 人
对于一年后就要举办的北京奥运会,李永波坦言“自己的压力很大”。
“国人把奥运会看得过重了,已经超出了体育运动的范畴。”他说,其实奥运会就是一次大聚会,一个给老百姓带来快乐的大party,给他们一个了解、欣赏和参与体育的机会,“我们把它想得太大了,自然压力就会大。”
在中国各个运动队当中,李永波任总教练的羽毛球队是世界冠军最多的。今年6月,这支队伍踏上卫冕苏迪曼杯征程时,17名选手中竟有16位世界冠军,惟一没有此头衔的朱琳也因本赛季一系列公开赛上的抢眼发挥而排名高居世界第三,仅次于张宁和谢杏芳两位师姐。
如此豪华的“梦之队”,无疑会把国人的“胃口”吊得高高的--即便是亚军,也算“滑铁卢”。
不过,虽然羽毛之“重”可想而知,但一贯乐于接受挑战的李永波有足够的“资本”在北京奥运会上大有作为。“包揽奥运会全部金牌是我自己,也是中国羽毛球队的梦想。”他一再这样公开表示。
实际上,他自己就是“资本”,经历与实践是最好的证明。1984年与田秉毅搭档取得世界锦标赛男子双打亚军以来,目前还不到45岁的李永波站在世界羽坛一线已有23年,其本人身为球员时,曾荣获1987年、1989年世界锦标赛冠军;1986年第14届汤姆斯杯决赛上,中国队与印尼队战成2比2平之后,他与田秉毅在关键战役中以2比0战胜强大的名将对手,帮助自己的军团夺得汤姆斯杯。他们还是1988年、1990年这一杯赛冠军队的主力成员之一。此外还获得过多次世界杯、世界大奖赛总决赛和全英羽毛球赛等的冠军。
随着“战场”从场内转移到场边,作为教练的李永波更加辉煌--率队陆续赢得过所有大赛的金牌。2005年5月15日,他的军团以3:0战胜印尼队,重新捧起了苏迪曼杯,使中国成为第一个同时拥有羽毛球3个团体项目奖杯的国家。“最难以忘怀的是2004年5月17日,中国男队如愿捧得久违了的汤姆斯杯,这个奖杯让我足足等了11年。”1992年,此前获得三连冠的中国队无缘汤姆斯杯,当时李永波还在队中与田秉义搭档双打,那届比赛之后,中国人五度冲击,总是在关键时刻与汤杯擦身而过。
李永波还是中国羽毛球队奥运历史的重要见证人与创造者之一,从参与奥运会的表演项目到正式比赛,再到如今成为中国代表团的夺牌“大户”。在他的指挥下,1996年葛菲/顾俊拿下亚特兰大奥运会女子双打金牌,实现“零”的突破,2000年悉尼拿下5块金牌中的4枚,2004年雅典再夺3金……惟一的遗憾是自己当队员时没有成为奥运冠军--只是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获得铜牌,正是这一年,他宣布了退役,不久便临危受命,从王文教、陈福寿等恩师与老教练手中接管了正处于低潮的国家羽毛球队的帅印,开始进行一次彻头彻尾的改造,组建了年轻化的教练员和运动员班子,并表面上看似乎是半开玩笑地“发誓”:要用培养100名世界冠军(包括更多奥运冠军)来作为自己“惟一遗憾”的“补偿”。目前目标距离已经过半。
与众多老教练一样,李永波也善于发现和培养新人,及时为队内输送了大量新鲜血液,而不断涌现的新人又使得中国羽毛球队形成持续不断的集团优势,但这也意味着他们将挤走那些曾经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并且实力犹存的老队员。
“其实,我的最大压力是在定奥运名单上,中国羽毛球队优秀选手早已有点儿‘人满为患’,水平相同的就好几位,不管最后谁能够有幸出现在明年8月北京的赛场上,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抉择。”李永波说得很无奈,也很“无辜”。
而先不涉及奥运会期间比赛如何打,光参赛资格就已很令李永波他们头疼的了。“奥运会是必须在世界排名前4名当中有3个人,你才可以参加3个,这个就太难了,竞争太激烈了!”李永波感慨道。
依据他的说法,国际羽毛球联合会为了生存而不断推出改革方案,“不少方案对此前在世界羽坛已有那么一点领先优势的中国队来说是不利的,而且,包括参加奥运会的资格、积分的累积、名额的限制、比分的变化,都会让我们队在对技术、规则的把握上消耗很大精力。”
比如,一个新的竞赛规则就又给中国队增添了新的麻烦。“就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运动员,不管有多少人取得参赛资格,不排除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你都可能自己碰,在抽签上没有特殊性,它不是说中国队去5个,应该在5个区,不到最后基本上不相遇……总而言之,最大限度地缩小中国队多名队员进入什么前8、前4的可能。”李永波说。
“‘麻烦’会对我们有影响,但不会影响到我们夺取冠军--包括奥运会金牌!”李永波举了实行“21分制”的例子。“这对我们队的损害确实是最大的,比赛的偶然性增大,强弱分明的对抗比分也打得比较接近,但是,2005年年末试行21分制的世界杯赛上,中国队时隔17年再次包揽全部冠军;去年我们的男女选手实现了双双卫冕,男队第6次夺得汤姆斯杯,女队更是第10次夺取尤伯杯。”
在李永波看来,中国队以往之所以能够在世界羽坛保持优势,主要是对传统的赛制、比赛形势的把握,尤其是比分僵持或落后时要采取的技战术打法等都已吃透,在专项训练等方面已摸索出一套成功的经验,但采用21分新赛制等之后,这些成功的经验就要大打折扣,优势被削减,回到了与其它队一样的起跑线。“所以我们必须重新认识,重新摸索规律,尽快适应,将新赛制带来的影响减至最低。”
“不管怎样,奥运会上囊括全部5块金牌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当然,我也很清楚,这仅仅是目标。”李永波表示,“我会为全队制订的目标去努力,我们的队员也会为这个荣誉去奋斗。”至于明年北京奥运会最终的成绩,以“心直口快”著称的他却有些“避重就轻”:“现在说什么都没用,都是‘纸上谈兵’,但只要了解自己存在的问题,摆正自己的位置,居安思危,然后一步一个脚印,把过程做得完美,届时的结果也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了,或许比预想的更好。”
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目标,中国羽毛球队进行了周密而精心的安排。首先,队内实行了激烈的公平竞争,继而,根据运动员各自不同的竞技特点,进行有的放矢的技术训练;在战术演练方面,根据对手的特点进行应对;确保运动员在一系列北京奥运积分赛上达到必要的积分,同时还要保证他们不过度疲劳。
离北京大赛只有一年时间了,但中国羽毛球队的“空气”却没有外人想象的那么紧张。队员“竟然”仍不时以“很阳光”的面目出现在媒体和公众面前,他们赢球,写博客,拍写真,唱歌跳舞,还有属于自己的联欢晚会。训练之余,一些男女队友甚至“公开”地谈起恋爱,“成双率”在各个国家队中几乎是最高的,已诞生了6-8对。
在别人的印象中,李永波是一个从严治军的教练,况且以前羽毛球队里也曾出现过因为谈恋爱而开除球员的“事件”。可是--“我不反对他们谈恋爱,也没有资格和权利干涉,但并不赞成把谈恋爱当成一件大事情来做。”李永波解释说,每个队有不同的管理模式,在他的队里,一个原则不能违背,就是恋爱与否都不能影响训练和比赛,“一切行为都不能跟自己的事业发生冲突,都得为它让步。”
应该说,“不反对、不提倡”这种的开明态度在中国体育界的教练当中并不多。采访的过程中,李永波还笑着为队员“开脱”:他们谈恋爱选择的一种主要方式是,下了课、晚上吃完饭,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约好了到场地“玩球”,发发球,搓搓网前,练些小的技术,“你说这不是好事吗?干嘛要干涉呢?”
21岁那年,李永波便与如今的夫人谢颖初识,当时两人都在辽宁体校当运动员(谢练的是艺术体操)。“真正有机会面对面说话,是因为谢颖她们宿舍灯泡坏了,一个女孩儿到羽毛球队找人去修,我情不自禁地跟着去了--借换灯泡之机,我就跟谢颖聊天,与她下军旗,说我那儿有很多从国外带回的录音带,这还是比较有诱惑力的……”自此,两人开始频繁接触,谢颖每周六回家,都会给李永波偷着带他爱吃的水饺。
“我之所以对球员谈恋情要求不是特别严格,是因为我始终认为恋爱这个东西,如果你把它处理得很好,双方是可以相互促进的--我们俩相恋以后,彼此的成绩不断提高,我是认识谢颖以后才成为世界冠军的。”李永波又自我“开脱”起来。
“我写给太太的信,最长一封有98页,将近1万多字,好像是谈我的理想。”李永波现在讲来都颇为自豪和得意。他们的爱情故事在队内广为流传。恋爱8年、结婚15年,俩人携手走过了23个春夏秋冬。起初,他们主要通过写信排解相思之苦。后来通讯方便了,工资基本上都用在了“熬电话粥”上。据悉,平日里爱“遛遛嗓子”的李永波曾经灌制一盘自己演唱的情歌录音带献给谢颖。有敏感的商人“眼前一亮”,但终未改变这盘很有价值的录音带“只是小范围发行非卖品”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