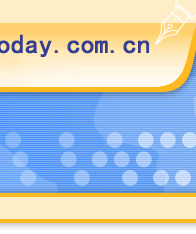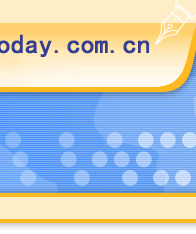一个人和他的《四季》
文/张 洪
本来约在前门的肯德基,后来改到旁边的“面爱面”,当好友把那个装着吕楠《四季》的纸袋儿递给我时,手下一沉,旋即掂出里面的分量。
对我来说,吕楠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熟悉,是因为旧日的同事老梁曾多次提到这个名字,陌生,是因为一直未曾谋面。只知他20余年,仅拍摄了三个题材,却都是“重磅”。虽然在艺术圈颇有人气,但吕楠从不“出镜”,许多影展邀他参加,几乎无一例外遭到拒绝。有一次,他从西藏回来,拎了两旅行包胶卷,这些胶卷日后只能出产有数的几张精品,即使是难得一见的美景,只要不是本次所需,也一概略去不要。而每次入藏,他都带上药物接济当地人。
面前这册摄影集--《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109张素净的黑白照,吕楠用掉了3500多个胶卷,时间是7年。
7年中,完整的秋收,他前后独自拍了4次,春播拍了两次。据中国艺术圈最具权威的评论家栗宪庭介绍,吕楠靠地图选择拍摄地,用比例尺来计算能够步行走到的村子,几乎每天下午,他都冒着沙尘暴,往返于海拔4000米以上的村庄和驻地。拍摄之余,每天还要花数小时研读柏拉图、歌德,并且听他喜欢的巴赫。
在大城市里讨生活的我们,7年能干些什么呢?有人会拿一些作品“说事儿”,我却扣齿不服。与这册“忘我”的大书相比,多数人的作品都有一个隐身或不隐身的自己等待推出,而我反复捧读吕楠,看到的却是他与镜头下所有人、事、物的恬然一体。那些山,那些牛,那些捻线、打茶的人,那些瞬间成就的永恒……摄影家藏身在这些之后,潜心融入,然后消失成现场的一部分。若用焦距、光圈、影调等生硬的技术词儿去套他,会让人觉得亵渎。尽管吕楠的镜头几乎自然到大象无形,好像“天意”在把着他的手按动快门,完全可以接受任何行家的挑剔。
“控制画面的情绪,也许是《四季》保持庄严感的重要方式。”栗宪庭如此评价吕楠。所谓“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四季》的每一幅作品,所以能始终统一在庄严、肃穆、大器、凝重的整体气氛中,控制力可能是吕楠最重要的语言方式。”
一个镜头可能要拍掉几个胶卷,而且所有的照片都不剪裁,《四季》能把普通变成不普通,把日常生活变成“经典”,在栗宪庭看来,在于吕楠体会到了西藏人的劳动是百之百地为着自己。他第一次看到把劳动变成了劳动本身。“凡高说强烈的阳光下就是庄严肃穆太对了。在西藏,没有面朝泥土背朝天苦的那一面,他们完全是为自己干,所以劳动终于变成劳动是快乐的。就跟艺术变成艺术本身一样才有可能出现伟大的东西。一旦有世俗就跟伟大没有关系了。”
几年前,同事老梁去世时,吕楠用好看的手写体引用《圣经》中保罗的话来概括他:“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那段时间,我的脑子里像放了张碟一样反复回响这几句话,几乎成了我心目中吕楠这个人的声音版。而这册大书的扉页上则郑重写着献给梁京生先生。
后来才知道,吕楠是最早被法国“马格南图片社”选中的中国摄影家,且是美国《光圈》杂志介绍过的惟一一位中国当代影人。这些殊荣可以是简历中重重的一笔,但从不“出镜”的他,连简历也不曾炮制,他惟一的简历就是20多年成就的3部作品。这样一个“对为了引起轰动的记录与华丽的表现方法不感兴趣”的人,有足够的理由和底气说出这样的话:“好东西是在沉默中完成的”。
《国史十六讲》 作者:樊树志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6-4
作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近年来,樊树志开设的中国古代史课程颇受学生好评。该课程的讲稿结集成此书出版发行,没有出版社的刻意宣传,更没有媒体的炒作,作者也不是央视《百家讲坛》精心打造的“学术明星”,这本普通的高校教材甫一问世,迅即成为了畅销书,在出版后的数月里始终位居学术类图书销售排行榜的前列。一般来说,一部书能够畅销,既要“好看”,也要让人感到“值得看”,《国史十六讲》一书就做到了这两点。
《佐贺的超级阿嬷》 作者:(日)岛田洋七 译者:陈宝莲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7年3月第1版
因为无力扶养,母亲只好将年仅八岁的昭广寄养到佐贺乡下的外婆家。在物质匮乏的日子里,乐观的外婆却总有神奇的办法,让艰苦的生活快乐地过下去……
“我”把成绩单拿给外婆,小声说:“对不起,都是1分或2分。”“不要紧,不要紧,这些加起来就有5分了。”“啊?成绩也可以加起来吗?”外婆断然回答:“人生就是总和力!”
2006年台湾金石堂年度畅销书排行第一名,2006年博客来年度畅销书排行第一名,香港各大书店畅销书排行第一名。连续三年位居日本各大畅销书排行榜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