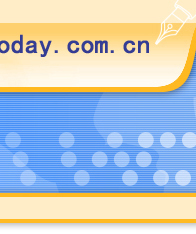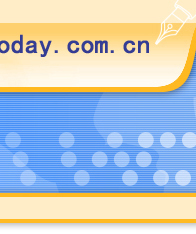小成本的胜利
文/陈四
“以前看中国电影是因为喜欢其中东方的人物和风景,但在看《图雅的婚事》时,我被它的情节所吸引,而没有意识到这是一部中国电影。”一位德国影评人的评论,让《图雅的婚事》的导演王全安深有感触,这说明观众已不再是为影片的中国特色而打动,而是电影内部元素开始起作用,和观众有了真正的交流。
有质感的动人影片
《图雅的婚事》在第57届柏林电影节上,击败了其他入围的21部影片,获得了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三次获得金熊奖,上一次获奖已经是14年前。《图雅的婚事》是一部投资500万元人民币的低成本的艺术电影,整部影片除了女主角是专业演员外,全部是非职业演员。柏林电影节的评委施南生说,“7位评委在看完《图雅的婚事》当天,就经提出,这就是今年的‘金熊’。在最后的投票环节完全没有竞争对手,惟一的争论在于,是否要给女主演余南奖项。”
与《图雅的婚事》不同的是,2006年中国几部投资过亿元(人民币)的大片,在众多国际电影节,特别是奥斯卡上铩羽而归。这些大片都是鸿篇巨制的历史剧,却缺乏人物和情节,缺乏感人的力量。这显然不是国际电影节评委,更不是电影观众的需求。导演王全安说:“我从国际电影节的选片人那儿感觉到,他们已经有种要求:‘你们能不能提供有创造性的东西,跟你当下生活的这个躁动、充满活力、热火朝天的中国现实更紧密的东西?’”这一点从《图雅的婚事》和先前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金狮奖的《三峡好人》的获奖上得到验证。《三峡好人》反映了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三峡,带给当地人生活的变化,而《图雅的故事》则从更为个人化的视角反映了飞速发展的经济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冲击。
《图雅的婚事》说的是,在内蒙古日渐干旱的草原上,丈夫巴特尔为了掘水井而双腿残疾,妻子图雅一个人挑起了家庭的重担。长期的劳碌让她的腰椎病变,甚而有下肢瘫痪的危险。为了不再耽误图雅,巴特尔决意离婚,在现实面前,图雅也只能同意。但她坚持提出自己再婚的条件:新丈夫必须和自己一起供养巴特尔。图雅开始了艰难的择夫历程……
女主演余男是影片中惟一的专业演员,她真实地呈现了一位蒙古族平凡女子的不凡人生。王全安执导的全部作品都是由余男主演。影片中的非职业演员不论出场时间短长,几乎所有的出场人物都形象鲜明,自然。
导演王全安说:“我的电影都是关于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原因很简单,这样的电影太少。现实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在目前的中国电影中是缺失的,希望这部电影是一个例外。”
关注女性题材
王全安目前只拍摄过三部作品,都是女性题材,他认为“女性比较感性,对事物和关系的反应往往较切中问题实质,女性也较敏感,我对女性充满敬意。”
42岁的王全安小时候曾经希望以绘画为终生的职业,12岁时却阴差阳错地离开校园到一个歌舞团当舞蹈演员,并从此开始了城乡游历的生活。1985年他突然萌发拍电影的强烈愿望。1987年放弃去法国里昂电影学院学习导演的机会,考进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因为他认为自己更熟悉中国。
王全安曾经在被中国“第六代”导演极力推崇为经典的《北京,你早》中出演一位汽车司机。影评人对他的评价是对角色的把握“精准到位”。毕业后,他回到自己家乡的西安电影制片厂做编剧。他一共写了13部电影剧本,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导演想对电影结构了如指掌,应该像好莱坞导演科波拉那样自己来写剧本。
2000年,王全安拍摄了他的第一部作品《月蚀》。这是一部称为“中国的《维若妮卡的双重生活》(La Double vie de
Véronique)”的充满直觉和多种新的元素的电影,受到电影界的关注,并被多个国际影展邀请参展。《月蚀》让王全安获得了自己可以成为导演的印证,他说当时自己处在“自我表达的阶段,是不考虑一般受众的,觉得电影可以做所有的事情,什么都可以表达,但后来你发现电影适合的还是讲故事。很多时候我们忽略的并不是什么很重大的东西,而是常识。电影要给尽可能多的观众看,这是常识。”
王全安在他的第二部电影《惊蛰》中放弃了电影技巧的展示和学院味,专注于讲好一个故事:农村女孩二妹被父亲许配给村里一户有钱人家。二妹逃婚进城,但对城市和爱情的幻想很快磨灭,二妹也从女孩儿成了女人。她最终回乡嫁了那个男人。在这部影片中,王第一次感受到对拍摄对象的认可,觉得他们和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比,你没有任何可以惭愧的。他发现,电影的内涵应该根植在好看、让人愉悦的故事里,这样更善意,更有关照。
《图雅的的婚事》的外景拍摄地离王全安母亲出生的地方不远。他说:“我一直喜欢那个地方的蒙古族牧民,喜欢他们的生活方式和音乐。当我听说那里的草场严重沙漠化,当地政府强令当地的蒙古牧民搬离牧区时,就决定在那一切消失之前,拍摄一部电影来记录这一切。而图雅这个独特的婚姻故事,也是出自当地一个真是的事件。”
王全安说:“我希望把这部电影拍得美丽而充满力量,电影的主要拍摄场地选在最后一家还没有搬走的蒙古牧民家里,演员也基本都选择当地的蒙古牧民。电影拍完的时候,电影中的那些房屋和那些人也就消失了,他们再也不是骑在马背上骄傲的蒙古人了,而变成了一些散落在城郊农田里的农民或城市角落卖水果的小贩,一些和我们差不多的人。这叫人悲伤,但一想到那些曾经美丽的人,他们的欢喜悲伤都被记录在这部叫《图雅的婚事》的电影,内心就平静安宁了许多。这个时候我就非常庆幸自己是一位电影导演,对电影业充满敬意和感激。”
拍艺术电影是很愉悦的事
王全安当导演是想表达自己对环境和身边人的看法,并且非常享受拍片经历。他认为,很多导演拍了很多大制作,但是没有拍过让自己愉快的电影,他担心随着电影越拍越多,自己也会丧失掉一些东西,所以他选择了拍艺术片的路子。他对中国艺术片的处境持乐观的态度,他说:“在中国看艺术电影的人比过去成熟了,这让我感到非常惊讶。艺术电影最重要的是它要有交流的对象,现在这种交流其实是非常成熟的。”
从拍摄《惊蛰》开始,王全安的剧组就是一个国际化的团队。他的御用女主演余男是一位能流利讲英语和法语,并与国外导演合作过的演员。他说:“这些人有时能给我提供独特的感受。他们对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的反应更敏锐、更新鲜,对我们过分感情色彩的东西也能保持冷静和旁观,这对我非常有帮助。”《惊蛰》和《图雅的婚事》的摄影师是来自德国的卢茨,他是看过王拍的《月蚀》后开始和王合作的。王全安说:“跟中国的很多摄影师不太相同的一点是,他能更多地关注我们要拍摄的对象,而不仅仅是自己摄影的工作本身。卢茨的气质也是一种松弛的气质,能使电影在整体上、在画面和内容之间获得平衡的效果,他不抢要表达的内容。”
国内有媒体评价王全安的作品主要是冲着国际电影节去的。王说:“要引起世界性的关注,电影节是重要的平台,否则第三世界国家的电影几乎没有机会被发达国家所了解。中国电影参加国外的电影节,不是你想不想去的问题,而是你能不能去,去了以后能不能有所收获的问题。中国电影在国际上的展示,不是多了,而是很不够,这个很重要,一点都不矛盾,完全是一个良性循环。”他认为,中国电影是被国际电影节鼓励、支撑过来的,包括导演本身拍片的方向。不过,他也承认目前一些中国电影为参加电影节而有太多运作的痕迹,就有点索然无味了。
现在简单说中国电影形成商业片和艺术片这个格局,而且彼此有抵触,王全安认为,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在大环境里这两种电影都需要存在。而且,中国电影的类型都还太单一,它应该容纳多种事物并存,呈现多元素,有更多不同的想像力。
目前,王全安正在筹拍的作品是获得中国文学最高奖的作品《白鹿原》,迄今总印数已经超过100万册。这是一部“通过家族兴衰的历史,表现民族、家庭和个人命运,展现上个世纪前50年社会变迁的历史长卷”。由于其漫长的时间跨度,复杂的叙述结构和人物谱系,出版14年来,仍没能拍成影视作品。据说,执导这部影片是因为他善于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