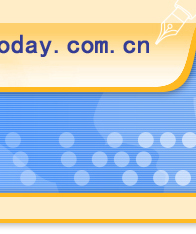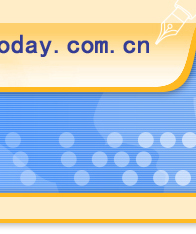铿锵玫瑰在海地绽放
文/刘 洁
在海地紧张艰苦的战斗生活中,我们8名女队员与男队员们一样,经受住了各种严峻的考验。
女队员主要负责队部指挥中心的工作。24小时轮流值班相当枯燥,由于长期值夜班,所有的女队员都出现生理周期紊乱的现象,身体都出现了问题。而且,除了正常的队部工作外,我们女队员还主动请缨,参与了防暴队几乎所有的外勤工作,与男队员一起背负着沉重的武器装备,承受着装甲车里难耐的高温,冒着随时被袭击的危险,还要克服身体和生理上的不适。有时一天的外勤连续长达14个小时,其间为了不上厕所,我们只能尽量少喝水甚至不喝水,生活的艰苦和环境的危险是生长在和平年代的我们难以想象的。
第一次出外勤是刚到海地不到半个月,当时正值海地局势恶化,一周内连续发生了多起针对联合国人员的袭击事件。我和另一位女队员主动要求第一批去,虽然在其他姐妹们面前表现得很轻松,但是一直干内勤工作的我们心里真的没底。为了不影响同伴休息,那天早晨很早我就蹑手蹑脚地走出了宿舍,可当巡逻的车队经过营区门口时,我惊讶地发现另外几个姐妹早已等候在那里,她们并不清楚我们在哪辆车里,向每一辆出行的车辆挥手送行。透过装甲车巴掌大小的窗户,看到她们找寻的目光和掩饰不住担忧的神情!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从那时起,我们就形成了这样一个自发地为出勤的姐妹送行和迎接的习惯,那发自内心的担忧和问候,传递着亲人般浓浓的深情和牵挂。
海地大选最紧张的时期,女队员负责计票中心的站岗执勤,这里是各国要人前往计票中心的必经之路。2月13日的骚乱就发生在距离我们哨所不足五十米的营区外的迎宾大道上,废旧车辆燃烧散发出的滚滚浓烟淹没了计票中心的上空,当时执行任务的是只有23岁的法语翻译张沛,那天她身体不适,但还是坚持站完那班岗。没有勤务的三名女队员也不约而同地来到了哨位。在那最紧张、最危险的时刻,大家没有语言交流,但彼此会送去一个默契的眼神和宽慰的微笑,正是这浓浓的情谊支撑着我们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
执行勤务,危险时时就在我们身边。国家监狱平暴让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恐惧,感受到作为一名警察原来和危险离的那么近。5月14日,国家监狱发生暴动,防暴队领导紧急部署,刚刚值完夜班准备休息的队员们又迅速赶到现场。作为翻译的我,陪同政委来到距离闹事犯人不足20米的监狱最内层近距离观察,从观察点到我们大部队集合的位置之间,要经过一条五十米的小路,这段路使我们完全暴露在囚犯的视线里,他们将手头能扔的石头、铁锁一股脑的向我们砸来,背后还不时传来枪声。因为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当时很紧张,看着落在身边的石头,动作也是麻木的。正当我专心翻译时,突然,一名男队员把我拽了一个趔趄,与此同时一块铁锁就砸在我刚才站的位置。事后,回想起那个场面都觉得有些后怕。
我们这样笑对生活中的一个个困难:营区的厕所面积不到一平方米,全封闭式,待在里面就像是在一个大闷罐里,汗流不止,臭气熏人,我们就戏称上厕所为“洗桑拿”;一日三餐不见绿色蔬菜,土豆洋葱天天当家,我们称之为“增白大餐”;一天到晚40多度的高温,衣服湿透是家常便饭,我们称之为“瘦身总动员”;营区周围枪声不断,时常会有子弹落到营区房顶上,我们就会说“又放鞭炮了”。
虽然面对的是紧张繁忙的勤务工作和艰苦的生活,我们依然乐观开朗、积极向上,如举办文艺晚会,邀请了几百名联海团和海地政府官员参加,八名女队员表演的民族舞蹈尤其受大家的欢迎。联海团的外国官员也表演了精彩的节目,他们的参与使我们的营地变成了一个国际大舞台,我们也向各国友人展示了中国警察多才多艺的另一面。
八位女队员都是第一次离开家到这么远的地方,执行这种危险的任务,每个人的心情都是复杂的。
选择了维和也就选择了要负担起对家庭、对亲人的感情欠债。来自烟台的曲晓云,孩子才三岁,她把孩子的照片贴在床头,每天睡觉前都会看上一小会儿,说上几句话。其实,孩子也想妈妈,有一次她和孩子在网上聊天,突然间孩子哭着冲她大声喊:“妈妈,你怎么还不回来啊,妈妈,你不要我了吗?”当时曲晓云的眼泪一下子涌出眼眶,怎么也止不住。是啊,为了让海地的孩子们也有一个欢乐的童年、一个幸福的家园,我们只能忍痛割舍对亲人的思念。我想等孩子长大以后一定会理解自己的妈妈,也一定会为妈妈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