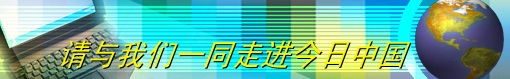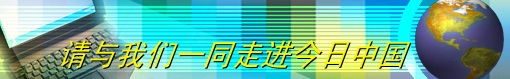史久平静地说着他做志愿者的经历:“我做的事情都特别琐碎,没法跟人家濮存昕比。但能为这些艾滋病患者做点事儿,我特别塌实。听到我帮助过的艾滋病患者说‘史老师是好人’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很高兴。”
与艾滋病人打交道的人
本刊记者
张 娟
时节已进入深秋,太阳依旧暖暖地照着。下午一点三十分,位于北京佑安医院最南端的“爱心家园”门前,几个着病号服的人围坐在树下的石桌上打牌。“史老师来啦!”有人发现了远处走来的一个老人,于是大家纷纷站起来与他热络地打着招呼,“你们中午也不睡会儿觉?”史老师也热情地回应着,“我们不困。”被称作史老师的是67岁的史久,与他打招呼的病人是正在住院治疗的艾滋病患者。
“史老师是我们爱心家园的志愿者。”艾滋病感染科护士长福燕告诉记者。成立于1998年11月26日的“爱心家园”,是中国第一家关爱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的非政府组织(NGO),目前爱心家园里像史老师这样的志愿者在册人数达2000人。“史老师是我们这里的第一批志愿者,也是年龄最大的志愿者”,福燕介绍说,这些志愿者身份各异,学生、工人、职员、老师、医务人员,主体是医学院校的学生。学生流动性较强,再加上对志愿者的管理完全是松散型的,像史老师这样能一直坚持下来的志愿者人数并不是很多。
跟艾滋病人打交道挺不容易的
北京大学志愿服务与中国福利研究中心丁元竹教授说,史老师这样的志愿者被称作“民间志愿者”,目前这样的志愿者在中国大约有20万人。“民间志愿者的志愿程度很高,并且很理性,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从1999年1月成为志愿者起,史老师在“爱心家园”服务已5年多了,其间他从单位退休了,但志愿者的身份一直延续了下来。
“退休前我是首都医科大学的老师,是学校红十字会的副会长,最初做志愿者是从工作角度考虑得多,退休后就是完全自愿了。”讲起5年多志愿者的经历,史老师说:不容易,太不容易了!老人说,与艾滋病人打交道,最初真的是很难,因为这是一个太特殊的群体,在承受着身体痛苦、生活重压的同时,还遭受社会的歧视,他们就封闭自已进行“自我保护”。
史老师说,相比起来现在好多了,前几年人们对艾滋病缺乏了解,在很多人心里,只要洁身自好,就不会得艾滋病。所以理所当然地将艾滋病与道德联系在一起,得这种病的人被涂上道德沦丧的色彩,会像“瘟神”一样,有的被赶出家门,有的被当地人驱赶,举家迁到别地生活,很多患者都有着十分不幸的遭遇。
“不是你一厢情愿想帮人家,他就能接受你的。你想周围突然出现了一群人,说要帮助你,搁谁都得考虑考虑有什么目的。”史老师说,“相比起来,农村来的患者比城里的患者要好接近些,可能相对来说,城里患者压力更大,他只求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他得的是艾滋病。”直到现在,史老师说有认识好几年的北京患者见了他会笑着点点头,你不会知道他的职业、他的家庭及他的一切,但看到的不再是一张漠然的脸。
史老师回忆起最初做志愿者的情景,当时佑安医院的艾滋病房在医院的一角,只有六间平房。最初志愿者们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想得先见到病人才能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帮助。就问护士长:“我们可以看望病人吗?”护士长征求病人的意见后告诉史老师“病人没有这方面的需求”。福燕说更确切地讲,是患者心中的那扇门紧闭着,艾滋病患者遭受过太多的打击,他们渴望人们的理解,但又没有安全感,怕又受到新的伤害。对于这个敏感的群体,史老师说他们所能做的首先是尊重,志愿者通过医护人员向病人送花、送杂志,让艾滋病患者感到病房外并不都是歧视他们的人,有人理解他们的不幸遭遇,真的是想帮助他们,而且没有任何目的,一次又一次后,患者一点点地消除了顾虑,接纳了史老师和他的学生,1999年的中秋节,首医红十字会带着月饼,与艾滋病患者在病房里一起过了一个“团圆节”。史老师和福燕都清楚地记得一个情景:一个名叫刘蓓蓓的学生志愿者,第一次陪艾滋病患者在院子里散步时,激动地哭了,不停地说“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我做的事情都很琐碎
“一提起志愿者,人们都跟高尚、值得尊敬这样的词语联系在一起,我觉得自己跟高尚没什么关系,我做的事情都很琐碎,甚至不值得一提。就像是一种习惯,一件事干得时间长了,就放不下了,现在退休了,为自己找点事干,给这些艾滋病患者做点事儿,我特别塌实。”
作为志愿者,史老师说他做的都是些不值一提的小事:陪患者下棋、打扑克、聊天,帮病人买火车票、送站,为病人募集衣物,协助医护人员陪病人逛天安门、植物园。史老师说有时自己干的一些事让人听了觉得可笑,比如说一个南方来的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住院后情绪一直很低落,一次聊天时跟史老师说到他喜欢打麻将。“我当时还在学校,就去找学生宿舍的管理员,他们那里有没收来的麻将,我借了来找人陪这个病人一起打,打麻将时他有说有笑,人开朗了很多,说一打起牌了就把病给忘了,慢慢地也积极配合治疗了。”
福燕说爱心家园对志愿者的工作方式没有严格的要求,一切都缘于病人的需要,只要病人需要,哪怕再小的事,也要尽力做好。要让他们知道社会上有很多很多的人都在关心着他们。
史老师是爱心家园“随叫随到”的志愿者,“史老师帮了我们不少的忙,” 福燕说忙不开的时候,她们就叫史老师过来,包括有时给新来的志愿者做些简单的培训,史老师做得都很认真。史老师则说自己的家住得离医院很近,比别人多了些便利。
遇到经济上特别困难的患者,史老师还会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我退休工资不多,能帮点是点吧,”现在史老师在资助一个患艾滋病的小男孩上学,男孩的妈妈在生他的时候因输血感染了艾滋病,今年7月已经去世,孩子也被染上了,但自己还不知道。史老师对孩子的前途很担心,“孩子早晚有一天要知道的,家里又那么穷,怎么办呢?”史老师说也只能是尽力而为了。
人打交道时间长了,就有感情了,史老师说艾滋病患者更是这样,当他确定你是真正在关心他的时候,他会十分信任你。史老师手里有一个通讯录,是出院的病人留给他的,前两天有一个山西的病人打电话告诉他,要出一本书,想让史老师给看看,说就信他。史老师说他现在还可以做“心理咨询”,患者会把家里的烦心事告诉他,他会诚心诚意地去帮着“支招”;而患者有什么高兴的事告诉他,他也由衷地为他们高兴。史老师感慨说最难受的事儿是说不准什么时候,会听到哪个患者又“走了”。
他们最喜欢那张“握手”的照片
有关艾滋病的宣传在中国可以说是有些年头了,尽管大多数人当被问及有关艾滋病的传播方式时,都能较为准确地说出它的三个途径:血液、母婴和性接触,但真正当我们面对它的时候,还是显得局促不安。史老师问我以前采访是否到过艾滋病房?我说是第一次,并且老实地告诉他“有点发怵”,他宽厚地笑笑说这是正常的。
史老师说在跟患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很多患者来自偏僻的地方,信息很闭塞。他就着手做一项工作:收集报刊。凡是刊有中央及各地政府出台的关于防治艾滋病政策的信息,他都复印很多份,送给住院的患者。“我就是想让患者了解国家和政府正在为他们做些什么,为他们提供了什么优惠政策,让他们知道社会没有放弃他们,增强他们战胜疾病的信心,并消除因一些地方政府、干部的不当做法而使他们产生怨恨。”
史老师从他随身带着的布口袋中取出他带给一个新入院病人的“资料集”,记者看到有“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首批51个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公布”“河南省委书记李克强走进艾滋村”……史老师特地拿出一张2003年12月2日的北京青年报,头版刊有温家宝总理于“世界艾滋病日”在地坛医院看望艾滋病患者时,与他们握手的大幅照片,“那天几乎所有的大报都登了这张照片,我到学校里把能搜集到的报纸都找来了,还买了很多份报纸送给患者。”史老师说他告诉病人们:总理都跟艾滋病患者握手,总理都不歧视你们,你们一定要好好治病。他们很喜欢那张照片,后来这张报纸史老师又复印了很多次,因为不断有新入院的病人,来了后会找他“要那张握手的照片”。
采访中,福燕告诉记者,由于艾滋病患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艾滋病宣传防治志愿者中有很多人是“地下工作者”,这里有许多原因,但人们对艾滋病认知程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与史老师差不多同期到“爱心家园”的志愿者是位工人,他有理发的手艺,几年来他随叫随到为艾滋病患者理发,一直瞒着家人。后来他谈女朋友了,认为得对人家负责,就把做志愿者的事告诉了对方,结果吹了,临了还送他一句话:“你真有毛病。”史老师说自己不是地下工作者,“我老伴是教师,儿子大学毕业,全家人都能接受。”史老师说他退休时曾倡议同事做志愿者,但没得到回应,他没觉得有什么失落,毕竟“做志愿者就是自愿的事情”。